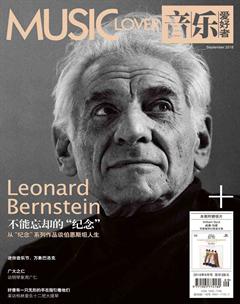廣大之仁
周廣仁,鋼琴家,中央音樂學院終身教授,1928年12月出生于德國漢諾威,1951年在第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中榮獲鋼琴比賽三等獎,是中國鋼琴家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第一人。1980年,周廣仁接受美國愛德加·斯諾基金會的邀請,前往美國堪薩斯城的密蘇里大學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交流,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走出國門的鋼琴家,也是中國首位向國外系統地介紹中國鋼琴作品的音樂家。

周廣仁曾擔任美國范·克萊本國際鋼琴比賽、英國利茲國際鋼琴比賽等重大鋼琴賽事的評委。1994年,在她的策劃和主持下,具有國際規格的首屆中國國際鋼琴比賽成功舉辦,引領中國鋼琴家進入國際樂壇。她創建音樂學校,舉辦音樂講座,指導中國鋼琴的教學工作,培養和提攜了眾多鋼琴家和鋼琴教育工作者。她將畢生心血獻給中國鋼琴事業,是普及和推動中國鋼琴音樂發展的最大功勞者之一。2009年,周廣仁榮獲第七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成就獎”。
周先生是中國鋼琴界的一面旗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普及中國鋼琴教育,她自己花錢為想學鋼琴但沒有條件的學生買了很多臺鋼琴,幫助了中國各地的很多琴童。在采訪過程中,周先生說的最頻繁的兩個詞是“感動”和“感恩”,她被積極向上、努力工作的人感動,她被別人對她的關心感動,她感恩自己兒時的所有鋼琴老師,她說正是他們為她指明了音樂學習的方向,指引她日后的教學事業。周先生對待專業極其認真、苛刻,她說她喜歡做與音樂相關的所有事情。如今,她每天仍堅持練琴,給學生上課。在眾多鋼琴音樂節和鋼琴比賽現場,她可以連坐幾天聽各位鋼琴家和孩子們的演奏。她說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學習,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周先生胸襟寬廣,總是為他人著想,用自己強大的內心包容和幫助所有人,我想這都與她從小的家庭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良好的家庭教育,培養了嚴謹認真的做事態度。她一生遭遇了很多坎坷;“文革”時期喪夫,獨自撫養一對兒女成長;1982年,搬鋼琴時她的三根手指被砸斷,在承受極大的痛苦和恢復訓練一年后,她重返舞臺,在北京大學禮堂舉辦了音樂會;1986年,由于過度疲勞,她的右耳突然致聾。對于鋼琴家來說,這些坎坷都是致命的打擊,然而她依然樂觀開朗,豁達地面對人生。堅定的信念、始終不渝的熱情、永不妥協的精神和對藝術的執著伴隨著她的一生。周先生才華橫溢、認真謙虛,一輩子追求平和與愛,每一次與周先生的接觸都令我深深地感動,被她的人品和師德所折服……

● -史青岳 ○ -周廣仁
● 周先生,您好。作為中國鋼琴家,您為中國鋼琴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您出生在一個大家族里,您的家族環境和教育對您的人生有什么影響?
○ 我的祖父是搞實業的,他特別喜歡幫助人,經常做積德行善的事。他告訴我們要“踏踏實實地做一個有用的好人,認認真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我的祖母對我的影響更為深刻,她的性格剛毅堅忍,我能平靜地看待生活、積極地對待困難和挫折,都與祖母對我的影響分不開。
我的父親為人寬容、人緣極好,他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工程系,后又前往德國漢諾威攻讀機械工程博士學位。我的母親是一位聰明智慧、大方開通的賢妻良母,她善良美麗,從小讀古文、背唐詩,頗有文化氣息。母親隨父親去了德國,學會了德國家庭主婦的全套本領,包括待人接物的禮節和習慣。她可以用標準的德語說和寫,會游泳、會跳交際舞,還會一點鋼琴。我從母親那里學到了許多優秀品質,特別是她的賢良、謙虛忍讓和樂于助人的精神,都讓我受益匪淺。
● 您出生在德國,回國后也在上海的“德國學校”學習,您覺得德國教育對您的影響是什么?
○ 我的祖父是上海金融界人物,他的事業發展使他經常與德國洋行有生意來往。祖父贊揚德國人整齊劃一、嚴肅認真、謹慎厚重的品格。這種“德國情節”使我父親赴德國留學深造,我也因此而出生在德國,五歲回國后又進入上海的德國學校——威廉皇帝學校讀書。德國教育特別注重勞動,我的父親對兒女要求非常嚴格,他強調“自己的事自己做,而且必須做好”。最重要的是德國教育培養了我們極度守時的習慣,這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
● 您的音樂啟蒙是在什么時候?
○ 我的啟蒙音樂課是在“德國學校”,學校的音樂老師非常好,我也特別喜歡音樂課。當時我報名學習吹笛子,學會了識譜和演唱一些兒童歌曲。我十歲時,父親準備讓大姐學習鋼琴,因為我對鋼琴太熱愛了,所以希望父親也能讓我學。在我的爭取下,父親才給我租了一臺鋼琴讓我學習。我的鋼琴啟蒙老師是錢琪先生,她屬于中國第一代鋼琴家。錢琪先生對每一節課都有非常細致的計劃,她給我做標準的示范,讓我知道該如何彈,應該注意哪些問題,這些都激發了我幼年對鋼琴的興趣。
● 之后您在上海私立音專跟隨丁善德先生學習鋼琴,請您講講丁善德先生對您的影響。
○ 丁善德先生是中國第一代鋼琴家,是中國舉辦鋼琴獨奏音樂會的第一人。我是上海私立音專的第一批學生,在丁先生班上學了近四年,在這期間我接觸了大量的鋼琴文獻,參加學校每年舉辦的音樂會,這使我對學習鋼琴的興趣更加濃厚。丁先生心胸寬廣,我親眼目睹了他把音樂館改辦為私立音樂專科學校的整個奮斗過程,我從他身上感受到“教育救國”的精神力量,這是一種以身作則的榜樣作用。丁先生的為人和做事風格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是一位偉大的“導師”,為我打開了音樂大門。他對音樂的忠誠是我終身學習的楷模,我從心底里佩服他,這大概就是教育傳承的作用。后來丁先生去法國留學,學校因此就解散了。
● 那您后來又隨哪些老師學習鋼琴?
○ 丁先生出國后,我就想跟隨意大利名師梅·帕契先生學琴。梅·帕契的水平非常高,學費也很貴,當時是五美金一節課。我的想法遭到了父親的強烈反對,他當初同意我學琴,完全是為了培養和提高我的教養和素質。他雖然是一位音樂愛好者,但他覺得靠音樂吃飯沒前途,將來無法養活自己,音樂不能作為職業。他希望我發揮語言優勢,將來從事外交職業。為了打消我學鋼琴專業的念頭,父親對我說,從今往后,不再給我提供學費。


當時楊嘉仁先生正好從美國留學回來,他畢業于美國密歇根大學的音樂教育系,從事了幾十年的鋼琴教學,對中國鋼琴教育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跟隨楊先生學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他有很多現代化的教育觀點,他鼓勵我教學,說在教學過程中我的鋼琴演奏水平也會得到提高。楊先生極為重視兒童鋼琴學習的興趣培養,想方設法讓孩子們高興練琴,對彈琴不產生厭倦和逆反心理。他注意教材的前后安排,強調循序漸進,非常重視基本功的訓練。在給孩子布置作業時,他把作業的難點和可能出現的問題都告訴學生,從而讓學生知道如何練習,如何有針對性地解決具體問題,這些兒童鋼琴教學的科學方法讓我在鋼琴教學中獲益匪淺。所以,為了掙得與梅·帕契先生學習的學費,在楊嘉仁先生的鼓勵下,我決定開始教學,靠教琴的收入來繼續學習鋼琴。我從十六歲就開始了教學生涯,教二十個孩子學琴,每天白天教琴,晚上練琴。

梅·帕契晚年離開上海工部局樂隊,靠教琴為生,我跟他學習只有一年,上了四十四節課,后來他就去世了。梅·帕契非常重視基本功訓練,他給我留的作業非常多,系統的練習曲占了很大比重。他強調慢練和熟能生巧,總會給我提出各種問題,再一一為我講解。他的上課形式是“一對多”,把水平相似的學生集中起來,大家輪著彈,他給一個人指出問題時,其他學生也能聽到,相當于一個人可以聽三四個人的課,避免出現相同的錯誤,這種上課方式效率非常高。梅·帕契先生對我的影響是終身的,跟他學習以后,我的技術有了很大提高,手指功夫、彈奏方法和閱讀識譜能力明顯提高,對音樂表現有了新的認識和感受。
梅·帕契先生去世后,我跟隨當時從歐洲逃難到上海的奧地利猶太音樂家馬庫斯先生學習。馬庫斯先生非常重視培養我的音樂修養,他認為學那么多練習曲是浪費時間,建議我多彈樂曲。他把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作品都讓我熟悉和理解,從古典音樂作品學到現代音樂作品,擴大了我的藝術視野和藝術認知水平。他鼓勵我彈奏室內樂,說這是提高藝術修養的重要途徑,這一點對我的藝術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庫斯與在上海的外國音樂家組成了室內樂團,每周都舉辦音樂會,馬庫斯離開上海時,他推薦我頂替他參加演出。與這些高水平的音樂家合作,對我來說是艱巨的考驗,但讓我的伴奏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讓我知道伴奏對于鋼琴學習的重要性。
馬庫斯離開上海后,我隨李斯特的再傳弟子貝拉·貝拉伊學習鋼琴。認識貝拉·貝拉伊純屬巧合,有一天,我聽到有人在琴行里彈琴,就隨著鋼琴聲找到了他。當時貝拉·貝拉伊已雙目失明,但他擁有扎實的功底,可以極為清晰地分析出我彈奏的任何問題。他對雙音和八度的訓練很有見地,讓我天天練習李斯特所有的八度片段,在他的指導下,我的八度演奏卓有成效。一年以后,在貝拉·貝拉伊離開中國前,為了表達對老師的感謝,我與另外兩位同學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舉行了“協奏曲音樂會”,演奏了李斯特和柴科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觀眾大部分是外國人。那場音樂會非常轟動,演出結束后,我攙著貝拉上臺和觀眾見面,他非常激動地對我說:“我教了一輩子鋼琴,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你們這樣讓我如此感動的學生!”
貝拉·貝拉伊離開中國后,我又跟隨德國猶太音樂家威登堡學習鋼琴。他是一個大天才,柏林音樂學院的院長,已經載入具有經典意義的音樂百科全書之中了。威登堡是以鋼琴和小提琴雙專業畢業的,當年,為了擺脫德國法西斯的迫害,他四處流亡,最后落腳在中國上海,培養了許多中國小提琴家。他居住在猶太人聚集的虹口區,那時候已經九十歲了,卻還得到學生家里上課。威登堡是一個有修養、有學問,但沒有祖國和家庭的音樂家,他始終堅持對音樂的信仰與執著,我向他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學習貝多芬奏鳴曲。我非常同情他,把他的學生都集中在我家里,這樣他就不用跑來跑去上課。每次學習結束后,我都讓他在我家吃飯,然后再讓人力車的師傅把他送回家。我向威登堡學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就非常凄慘地去世了。
之后,我就處于沒有老師的階段。直到1955年,我在中央樂團擔任鋼琴獨奏員期間,到中央音樂學院進修,跟隨蘇聯鋼琴專家塔圖良學習。塔圖良認為我演奏樂曲時表達得很完整,音樂形象生動,基礎也很扎實。他在教學中非常精煉,話很少,但會經常給我做示范,并且能夠很精準地指出我的問題。通過向塔圖良的學習,我的鋼琴演奏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 您是我國最早進行兒童鋼琴普及教育的鋼琴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您先后創辦了星海青少年鋼琴學校和樂友鋼琴學校。您當時創辦這些學校的初衷是什么?您認為創辦一所優質學校最核心的是什么?


○ 第一是為了普及音樂教育,讓孩子們既學習文化,也有機會學習鋼琴,從多方面發展他們的音樂天賦。第二是我在國外講學、辦音樂會期間,外國人沒想到中國人也會彈琴,這個對我觸動很深,我想中國人怎么就不會彈琴?但是我再想,我們的老百姓并沒有古典音樂的基礎,那時候北京音樂廳開音樂會也沒有觀眾,我就想觀眾是需要我們自己培養的,所以我就決定馬上辦學,我一個人會彈琴是不夠的,我要讓更多的人來彈琴。辦學的好壞與否,教師是關鍵,于是我親自邀請了一批經驗豐富的老師來任教,孩子的啟蒙教育,必須由優秀的教師來完成。
●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學琴狀態怎么樣?學校最后達到您所期望的效果了嗎?
○ 當時學琴很“熱”,北京還沒有搞普及的鋼琴學校,所以這所學校受到了社會的歡迎,培養了一些比較有才能的孩子,后來都考上了音樂學院。不過,我也看到了家長們的艱辛,他們帶孩子從外地來北京學習,非常不容易。他們沒有錢買鋼琴,孩子沒有琴彈是不行的,我就自己資助這些學生,前后給他們買了數十臺鋼琴。我還收到過兩三次地方家長的來信,說他們的孩子特別想學鋼琴,但是地方學校沒有鋼琴,我就真的給他們寄鋼琴去了。我只要有一點錢,就給這些孩子買鋼琴。我覺得這不是偉大,是我真心希望這些熱愛音樂的孩子有能力學下去,因為我小時候想學鋼琴,父親是不支持我的。
鋼琴學校經過幾年的創辦,我覺得已經達到了普及鋼琴教育的目的,就關閉了學校。之后我就利用寒暑假和各種節假日,深入到地方和普通學校舉辦鋼琴知識講座,進行鋼琴啟蒙和音樂啟蒙教育。現在全國的琴童非常多,教學規范就顯得特別重要。我覺得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培養好老師,讓孩子們走正道,教給孩子正確的演奏方法和音樂知識。
● 您怎么評價現在的音樂教育?您認為理想的音樂教育為孩子帶來的是什么?
○ 培養孩子學一門藝術類的東西,對他的一生是有好處的,他會通過音樂得到很多樂趣和精神上的溫暖。現在有一個誤區,好像我們總想通過學一樣東西而得到些什么。我們從小學鋼琴,就是為了懂音樂、會彈琴,學音樂不要功利,不是為了得第一名,也不是為了得什么獎。原來為了激發大家學音樂的興趣,我會舉辦一些比賽,但是現在我對這些比賽不那么熱心了,因為隨著音樂教育的普及和關注程度的提高,功利的傾向性也越來越強,現在變成一種“買賣”,感覺一定要從中得到什么好處,這是不健康的現象。不要把獲獎看得太重,是否得獎并不重要,更多的是享受音樂和藝術,感知音樂的美,為追求美而學習。
● 您普及鋼琴教育,促進中外音樂交流,將畢生的心血都獻給了中國鋼琴事業。如今您已九十歲了,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終身教授,您還在給學生上課。是什么精神讓您如此奮進拼搏?您覺得什么樣的人生是有意義的?


○ 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實在太喜歡鋼琴,凡是與鋼琴有關的活動,我都太希望去參加,這對自己也是一種享受。一個人的一生不是自己策劃的,一半是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選擇,另一半是歷史把你推到那個位置,我的運氣算好的。實事求是地講,我不是天才,我只能承認我是努力的好學生,我學習很認真,學什么都有興趣,而且要學就學好。我是個樂觀的人,我們的鋼琴事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能夠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已經非常好了。
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只能發揮一定的歷史作用,只要在各自的歷史崗位上盡心竭力,就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我給自己的定位是過渡階段的人物,最應當發揮的作用是承前啟后。我希望通過我的作用,使中國的音樂事業,特別是鋼琴事業發展起來。這些活動對普及和提高鋼琴藝術都很重要,所以只要條件允許,我就一定會堅持下去,希望為中國的鋼琴事業多做點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