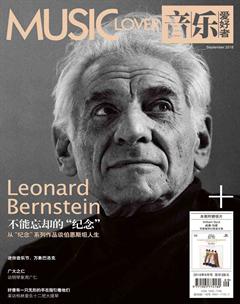一場大學音樂會帶來的“小確幸”
Néstor Castiglione
說起洛杉磯,除了好萊塢和西區(Westside),多數未曾來過這里的人想到的第一個地方應該就是洛杉磯市中心了。這座有著自我意識的復興城市,正是洛杉磯愛樂樂團和當代藝術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的所在地,在過去的十年中也一直發揮著其不斷增長的文化吸引力。



某一個周日下午,在輕軌南行線紀念公園站臺上聚集的人群似乎說明了這一點。他們與那些在北行線站臺上等車的零星人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于少數北行的乘客來說,他們的目的地也許是終點站阿祖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簡稱APU)和西勒斯大學(Citrus College)。當他們走下火車時,可能會好奇地環顧周圍的環境,砂礫和灌木叢包圍著一條混凝土道路,第一次來的訪客也許不會發現這是一條通向大學停車場的蜿蜒小徑。近距離處是連綿的圣蓋博山脈,斑駁的綠色依然透露著月初那場降雨所帶來的短暫的喘息之機。
對于初來的游客來說,從站臺漫步到停車場,有著一種微小而愉悅的探索感。繞著樓梯走到底層,可以看到通向克萊蒙(Claremont)的火車大橋橫跨了街道,沿著街道直走,最終會到達西勒斯大學。同樣的探索感也來自那天下午,在該校的霍爾表演藝術中心(Haugh Performing Arts Center)聽到的一場令人振奮的演出,那是由阿祖薩太平洋大學交響樂團在其指揮羅塞爾(Christopher Russell)的組織下完成的。西蒙斯(John E. Simons)帶領的阿祖薩太平洋大學的Masterworks合唱團加入了管弦樂隊,共同演繹了德沃夏克的《感恩贊》(Te Deum)。


耳熟能詳的曲子與陌生的旋律交融在一起,卻依舊讓人覺得親切。貝多芬鮮為人知的歌劇《菲岱里奧》(Fidelio)中的回聲穿插在《國王斯蒂芬》(King Stephen)序曲中。德沃夏克閃光的《第八交響曲》在他的《感恩贊》中有力地響起,給嘈雜的波西米亞式的喜悅巧妙地蒙上了一層憂傷。值得一提的是,布萊希(Angela Maria Blasi)和羅威(Ben Lowe)都是極其優秀的獨唱家。
在那天下午的音樂會中,只有阿沃·帕特(Arvo P?rt)的《第三交響曲》是一首人們完全不熟悉的作品。
受到其朋友和同事曼蘇利安(Tigran Mansurian)和施尼特凱(Alfred Schnittke)的影響,帕特放棄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蘇聯前衛藝術所采用的十二音技法,而是另辟蹊徑,從宗教和中古音樂中尋找靈感。結果,一本迷幻的樂譜俘獲了轉型時期的作曲家,使其創作風格逐漸走向了神圣簡約主義,從而形成的代表作有《鏡中鏡》(Spiegel im Spiegel)、《本杰明·布里頓紀念碑》(Cantus In Memoriam Benjamin Britten)、《兄弟》(Fratres)等,但這些仍然只是讓他走向和確立這一創作風格的過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的穆索爾斯基和肖斯塔科維奇的創作精義也出現在了《第三交響曲》的樂譜中,并使其深深附著在了交響管弦樂色彩罕見的擴展段落,也是復調二聲部對位段落中。那繪聲繪色的定音鼓獨奏,毫無疑問地彌合了第二和第三樂章,同時也是最后兩個樂章的派生物,正如肖斯塔科維奇《第一交響曲》終樂章結束前的定音鼓獨奏段落。在現場,演奏家杜克(Erin Duke)用了驚心動魄的力量詮釋了這段定音鼓獨奏段落。
盡管如此,于我而言,當天最大的發現還是阿祖薩太平洋大學交響樂團和他們的Masterworks合唱團。他們不僅排演了這些對公眾來說晦澀而又極具挑戰的樂譜,更令人贊賞的是羅塞爾和西蒙斯所帶領的各自的團隊將他們自己的風格和信仰也融入到了演出之中。或許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可以從主流交響樂團重復表演的編排相同的老舊曲目中受益良多,相反,更多的人也許會把阿祖薩太平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銘記于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