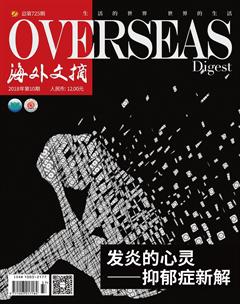說不通的現代人
淺野裕見子
在職場和生活中,人們經常遇到難以溝通的情況,曲解和疏漏也因此產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現代人語言表達和理解能力低下?是教育中忽略了實踐能力的培養,還是在社交網絡發達的今天,人們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漸漸減少?
只會說“糟了”的現代人
“每當我懇切客氣地對職場后輩和下屬提出建議,他們總是一邊聽一邊點頭,之后卻一點改正都沒有,我的話被完全忽視了。”一位四十幾歲的大學教師這樣抱怨著。本刊在網站主頁進行了問卷調查“為什么和那家伙說不通”,參與調查者只有60人左右,但答案集中出現的問題值得一書。
“在工作單位,同事(包含上司和下屬)無法正確理解我說的話,我和他們難以溝通。”有這種經歷的人占到調查總人數的72.4%。嚴重“說不通”的事例在人們的生活中頻繁出現。
一位兒科醫生說:“有時我只是闡述個人意見,對方卻當成命令去執行,這讓我感到困惑。”一位公司職員說:“因為常常不被理解,我擔心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夠完善,卻沒想到‘這人總是不把話說清楚的評價傳開了。”許多人都會感嘆共事的人語言能力低下。
文章開頭提到的大學教師說:“很多學生只會千篇一律的表達方式,無法通過語言表達細膩的感受。被什么事情感動的時候也只會說‘我打起了精神。”某位醫生則表示:“現在的人們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只會說‘糟了糟了。”抱有這些不滿的人大多已成為了管理層,年齡在40歲左右。
筆者原以為年齡較大的人才會因為代溝與下屬溝通不暢,然而年輕人對此也深有體會。某位30歲的臨床醫學檢驗技師說:“我和同事年齡相差不到5歲,雖然對方入職的時間比我晚,但也有幾年的工作經驗了。我和她卻難以溝通,談話會浪費很多時間。”工作相關的專業談話沒什么問題,問題在于日常會話。“前幾天我說‘心直口快‘簡明扼要這些詞,她都聽不懂,我感到很震驚。”他們的辦公室有一本共享筆記,用于記錄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而這位職場后輩表示如果不將情景再現,她就看不懂筆記。“比如系統錯誤的應對步驟,如果不把畫面一個個調出來查看,她就無法理解筆記內容,明明她本人也在用這個系統,難道是從來沒遇到過錯誤嗎?又或許是即使遇到了,她也直接無視了。”對工作方面的錯誤理解放任不管,會導致危險的后果,她說:“想到這一點,我客氣地試圖為她講解,她卻打斷我的話,拒絕了我:‘不用,我懂的。”
我們的問卷調查中出現了很多類似的控訴。比如,某集團職員說:“有的人既不看工作手冊里的步驟講解,也不讀器械說明書,教了幾次還說‘頭一次知道要這樣操作,講解當中只會說‘要點是什么呢‘只教我具體做法就好。”某公司員工抱怨:“明明自己做的是宣傳工作,每次公司調查卻都提出‘要把文章總結成只看標題就能明白內容‘希望減少稿件數量等要求。”某兒科醫生指出:“很多孩子看書的時候總是看差行,可以看出根本原因是他們過于急躁地想弄懂文字的主旨。”
社交網絡普及的后果
有人提出,容易誤解對方話語含義的原因,或許在于本來就沒有用心去理解,而這其實是互聯網或者說社交網絡普及的后果。“不管在網上搜索什么問題,都能立刻找到答案,人變得不會思考了。”“許多人依賴于手機和社交網絡,缺乏閱讀長文章獲得結論的專注力。”一位大學老師說,現在學校里有一種“只要自己懂就可以”的風氣。進行論文指導時,她每年都對學生提出“不要用口語表達,要用書面語寫論文”,可是大部分學生只會寫口語的語句。
在社交網絡盛行的世界里,人們害怕惹事或遭遇攻擊,于是價值觀相近的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即便如此,只是出現一點小摩擦,也有人會反應過大,認為“自己被苛責了”。
一位來自東京的公司職員說:“我的上司平日給人的印象是一位非常有領導才能的人物,可一旦成為他的下屬,就會感到他難以相處。他發揮領導才能的方向也明顯不對勁,把我們的團隊引向不明的方向,不知道在他的領導下我們的未來會如何,我感到很不安。”她從事保險公司的辦公室事務工作。公司以促進信息共享、縮短業務時長為目的,將數目龐大的文件以及辦公流程數字化了。為了測算數字化的效果和進度,辦公室要核算用紙的數量。她說:“我的上司卻把這項任務的目的誤解成環保,說讓我們保持職場環境的整潔,把桌子收拾干凈等等。”
上司隨時隨地的理解錯誤讓她煩躁。“上級會議談到了‘要注意職場騷擾問題。結果他好像只聽進去了一句‘不是只有上級對下級才有職場騷擾……”于是當天團隊全員就收到了來自上司的郵件:“我們團隊內部時常出現下級對上級的職場騷擾,大家要注意!”他提交的文件總是寫著個人記錄的信息,白天也無視輪休時間隨意外出,“自由”過了頭。“有時我會委婉地向上司請求業務支持,可很快就會弄得自己心情糟糕。到底怎么說才能讓上司不發怒并理解我的意思呢。我已經把能說的說盡了,非常疲憊。”
“現代人即使不與其他人來往密切也能生活,所以變得不能理解其他人的困惑了。”來自靜岡縣的公司支援堤啟暢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我出國的時候對此深有感觸,如果出門買東西或者吃飯,出于問價格等目的,我會拼命利用動作和手勢與外國人交流。可是回國之后,我一整天都可能不和他人講話,購物也可以從網上解決。”
他分析,當人們與他人溝通減少,感知、判斷其他人困惑原因的能力就會下降。
六成人選擇放棄溝通
當與他人“說不通”的時候,你會怎么做?17.2%的受訪者回答“從一開始就會放棄”,41.4%的人表示“如果說幾次對方還是不能理解就放棄”。也就是說有六成人選擇放棄。
另一方面,也有近一半人感到不安,擔心“自己會不會也是聽不懂他人真實語義的家伙”。
某位自由職業人士說:“我常常不能在當時理解他人的挖苦或煩惱,事后才注意到。”一位40歲的公司職員則擔心地說:“和他人談話的時候,有時對方會表現得很煩躁,莫非是我理解能力差造成的嗎?”
問卷調查中,也有不少來自教育界的聲音。在所有參與調查者當中,有五分之一是老師或教育機構工作者。一位今年帶小學畢業班的男老師對學生“實踐不足”的現狀感到擔憂。“升入高年級以后,明顯有些孩子在休息時間也不出去玩。首都圈區域自然資源雖然不算豐富,但配備花壇的操場還是有的,也有昆蟲。可是孩子們卻‘看不到這些東西。這樣下去,不管怎樣上課、讀書、學習文科和理科知識、了解社會,也無法擁有實際體會。全年生活在空調房里的孩子連‘手凍僵了的感覺都無法理解。”
學校雖然在校外活動中增加了許多體驗性學習項目,但成果如何還需要打個問號。他說:“現在的孩子們很少和老爺爺老奶奶接觸,也很少聽到關于戰爭、貧窮等內容,幾乎沒有忍受饑餓的經歷。在學校吃飯剩了飯菜,也毫不在意地說‘回家再吃就好了,如果去補習班回家比較晚,也可以去便利店買食品。在他們的生活里,不論缺少什么都能找到替代品。”
讀不懂教科書的學生
這些不單純是年輕一代的特征,還顯露出更加深刻的問題。學者新井紀子曾出版《被電腦奪走的工作》一書,她在最近的著作《人工智能與讀不懂教科書的孩子》當中提出了令人驚愕的事實:“許多日本的中學生無法正確理解教科書里的文章。”只注重知識量堆積的教育最終導致學生“連問題的真正含義也無法理解”,就像不論輸入多少數據依然會產生感覺上的微妙差異、不能完全匹配的人工智能。這一事實為人類敲響了警鐘,這樣下去未來的教育只能量產出工作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才。
與他人交流的減少和生活感的淡薄,最終導致人們理解力和閱讀能力低下。如果持續欠缺這些能力,在必須與人工智能共生的未來世界,人該如何生存呢?這引發了人們的思索。
[譯自日本《AERA》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