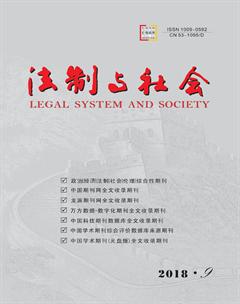未婚女性生育權探析
摘 要 隨著女性從婚姻中獨立出來,社會上一些未婚女性渴望擁有屬于自己的孩子的訴求卻因沒有合法配偶而受到限制。本文通過對相關法律進行整理和分析,發現法律雖沒有對生育權的主體作出明確規定,但未婚女性依法應享有生育權,期待法律考慮這類群體的生育需求,推動法律的規范性與科學性,更好的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權。
關鍵詞 未婚女性 生育權 主體 公平
作者簡介:金喚喚,重慶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117
生育行為的延續是人類社會繁衍生息的關鍵,對于個人來說,享有生育自由,自主決定繁衍后代,是不應被附帶條件的普適性權利,而且只有在為社會利益的情況下才能限制生育行為。 在現有法律框架內,未婚女性想要生育孩子,只能通過收養的方式實現,但隨著避孕方式的公開化與多樣化,符合收養條件的孩子越來越有限,有些收養人可能要等上很久,對于被收養人來說,由于他們對陌生環境的敏感與陌生人的隔閡,情緒會有很大的波動,不利于身心的健康發展。而且,收養雖然能夠解決未婚女性擁有孩子的愿望,但養親并不等同于血親,不能生育自己的骨肉至親,確實是作為女性一生的憾事。通過法律的整理和分析,筆者認為,一些省份剝奪未婚女性生育權,違反了生育權的平等性與私人化。相反《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并不違憲,也沒有違反上位法,因為生育權并非婚姻存續期間的夫妻專享,未婚女性的生育權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應當通過一定的途徑保障該類群體生育權的實現。
一、地方關于未婚女性生育權的立法規定
現代婚姻觀念影響著人民對婚姻與家庭的看法,正如卡塔林娜·托馬瑟夫斯基指出:“國際人權標準當初所設想的在婚姻和家庭之間的聯系已經被廢除。婚姻已不再是建立家庭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婚姻和父母身份之間的聯系的廢除還使得人們提出了對作為個人權利,而不是夫妻共同權利的生育權的要求。”
隨著單身、同居方式的泛化,必須以婚姻為前提的生育方式受到不婚者尤其是不婚女性的質疑,在新的時代,應當給生育權賦予新的內涵。
各省對未達到法定婚齡生育子女和已達到法定婚齡而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子女的法律責任有如下規定:除了重慶、河南、安徽、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吉林、黑龍江、江西、陜西、青海這些省份沒有明確規定未婚生育子女的法律責任外,在未達到法定婚齡生育子女的省份中,山東省規定征收3倍社會撫養費,浙江征收1.5倍至2.5倍,遼寧省按照3倍至4倍的標準征收;與前面的省份相比,福建省征收的相對少一些、按照60%至100%的比例征收,云南省規定男女雙方分別處2 000元罰款。某種程度上,這些未達到法定婚齡的生育者,大多過早輟學、心智還不成熟,而且本身的生存技能較差,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因此應該得到社會的救助、扶持和關懷,而不是在其承擔撫養子女義務的同時,還加重他們的社會責任,違背現代社會人權保障和給付行政理念的要求。
在已達法定婚齡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子女的法律責任方面,山東、遼寧和浙江三個省份都采用限期補辦的方式,未補辦的征收社會撫養費;廣東省是采用分別罰款1 000元;海南省規定未區分是否達到法定婚齡,統一規定未履行結婚登記手續生育子女的,按10%至20%征收社會撫養費;江蘇省采用非婚生育的說法,按照基本標準的0.5倍至2倍繳納社會撫養費,此做法明顯違背社會撫養費征收的初衷:一方面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規定辦理結婚登記是生育孩子的必經程序,婚姻自由是我國婚姻法倡導的基本原則,計生部門以辦理婚姻登記為前提,明顯違背了我國《婚姻法》的婚姻自由原則;另一方面,相對人沒有超計劃生育,其子女不存在多占用社會資源的可能。計生部門要求相對人以辦理婚姻登記為前提,無非是為了以后人口管理方便。這本身在現實操作張力下的“便宜之舉”,此舉是行政機關的自我授權,在沒有得到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是缺乏相關法律基礎的。
社會撫養費征收是以多生育子女而多占用社會資源為依據,征費的目的是為了補償社會因超計劃外生育而增加公共投入和促進社會公平,但是未婚者并未引起社會公共投入的增加,征收社會撫養費也就沒有法律和事實依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區別僅僅是其婚姻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這顯然不是此法律的調整范圍。對未婚生育的行為應該用道德規范,只要沒有超生,就不應征繳社會撫養費,否則就涉嫌侵犯公民個人財產和人格歧視。
二、未婚女性享有生育權的法律依據
法治國家強調任何政策的出臺都應當符合憲法及上位法的規定,要做到“援法而言”,以法律規范作為探討問題的出發點。 從《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出發,它是我國第一個把未婚女性作為享有生育權主體的規定,但它強調該類主體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達到法定婚齡;第二,生育后不再結婚;第三,必須采用合法的方式生育,該規定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彰顯了法律的人文主義關懷,但因該規定被認為超越上位法對于“夫妻”作為生育權主體規定,而被認為“違憲”,而且,該規定可能會帶來一些關于繼承權、撫養權、贍養權的法律爭端,及該類主體再生育后若又想結婚問題該如何處理的難題和一些學者的質疑。 但是,根據收養法對收養人的限制條件中,沒有要求收養人必須有配偶,那么如果未婚女性如果有能夠保障子女健康成長,就應當享有其生育的自由。 而且,其上位法并沒有把未婚女性排除在生育自由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和第49條只是強調了國家計劃生育的初衷和目的,以及夫妻雙方應當履行計劃生育義務,從中并不能得出“只有夫妻才能享有生育權”的結論,而且憲法作為規范國家權力、保障公民基本人權的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概括性的法律,很難判定某一具體法律或者措施違憲。尤其第47條第2款規定的“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只能得出夫妻雙方應當遵守相關計劃生育法律的規定行使生育權,當然,其他生育主體也應當遵照其規定,不得濫用其生育權。如果以此把其他不婚但想生育的主體擋載生育訴求的門外,明顯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初衷,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而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51條規定的“婦女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規定的“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以及相應的法律責任章節中,也只是規定不遵守計劃生育的公民應當繳納社會撫養費,也就是說法律并沒有限制行使生育權必須以合法成立的婚姻關系為前提。把生育權歸屬于人格權而不是身份權范疇,除配偶身份外,未婚主體也應當享有生育權,未經法律明確規定以及法定程序批準不得剝奪公民的生育權,更能夠體現法律趨向于保障和服務于人的主體地位和權利的平等性。
所以,一些省份對未婚女性生育者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做法,顯然是誤解了我國法律中享有生育權主體的概念。從社會發展的標志來看,從單純強調“婚姻生育”這一多數人的權利再到充分尊重“婚外生育”這一少數人權利的過程,也正是我國法治進步的體現和要求。
三、保障未婚女性生育權的建議
1.具體分析未婚女性生育子女的原因,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措施。對于未婚女性生育的規定過于苛刻與嚴厲,造成未婚女性生育權受到過度限制,建議完善相關規定,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要求所有未婚生育者都要繳納社會撫養費,加重他們的財產負擔。建議在立法上應當明確未婚者生育的權利,但同時要考慮其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能力、我國的生育政策等,以引導其自由而負責人地行使生育權。 具體來說,對于未達法定婚齡生育孩子的女性,尤其是未滿十八周歲的女性,出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禁止其在未達法定婚齡前生育孩子,但不能只是通過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方式加以制止。應當具體分析其生育子女的原因,如果是因為未達法定婚齡而無法領取結婚證,只要是未超生,就不應當繳納社會撫養費,因為他們可能本來就是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面對要繳納不菲的社會撫養費的現實,會增加他們的經歷負擔和心理負擔;對于其他原因生育孩子的未成年女性,要依據實際情況,對其進行幫助或疏導,此類人群,可能由于過早踏入社會,在于戀人或其他異性相處時,不懂得避孕方式,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下,便成為了準媽媽或媽媽,此種情況下社會應當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和幫助;而對于已達法定婚齡,不愿結婚而又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只要其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關于超生的規定,不以法律禁止或違背公序良俗的方式行使生育權,同時能夠保障其子女的權益和幸福,都應當尊重其生育意愿。
2.設立未婚媽媽關愛中心等普惠性的援助機構或組織。是否在有配偶的家庭中成長不是子女的健康成長決定性因素,在完整家庭下成長的孩子受到傷害或其他不利于成長的因素的報道也不在少數。相反,單身家庭只要能夠為孩子提供穩定和諧的家庭環境,孩子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關愛與保護,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而且女性由于天然的母性情懷,在沒有婚姻的家庭下,反而會更懂得如何去給孩子營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在眾多離婚案件中,一些女性寧愿放棄財產也要爭取到子女的撫養權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那些認為賦予未婚女性生育權會導致子女身心發育不全,或受到傷害的擔憂是沒有合理根據的。所以,雖然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長,是國家和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社會不能因為賦予未婚女性生育權存在法律和社會風險,而剝奪該類人權的生育權。而且,國家對未成年的保護措施相對全面,如果其子女受到來自其母親的傷害或潛在傷害,未成年保護組織及社區都會有一定救助措施,鑒于不婚但有生育想法的女性數量還不是特別多,未成年保護組織或者其他相關協調結構可以對這類家庭進行動態追蹤,這些數據也可以成為放開生育權主體提供有力的依據。或者可以以政府主導、社工組織參與的方式設立未婚媽媽關愛中心,幫助未婚的女性生育者解決在撫養孩子過程中,出現的難題,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該類兒童的保護力度,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兒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 但要盡量避免直接給予其物質資助,不然可能會導致一些不法分子受到金錢誘惑,在沒有生育意愿和撫養能力的情況下生育孩子,也會給子女的健康和成長帶來更多的潛在威脅。
3.給予女性未婚生育者生育保險待遇。一些省份規定取消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人員的福利待遇,比如分娩的住院費、醫藥費自理,不享受生育保險待遇和產假期間的工資待遇等,這就使得未婚女性生育者除了要支付社會撫養費外,還要支出額外的費用,這會增大其撫養子女的經濟負擔。而且社會保險屬于社會保障體系,是國家和社會對社會成員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制度, 生育保險是國家對生育職工的經濟、物質幫助,其宗旨是保障他們因為生育而暫時無法工作的經濟來源,若以符合《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條例》為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前提條件,將未婚生育者排除在外,則不合符社會公平的要求,也無法實現社會保障的初衷。
注釋:
國家計生委外事司.人口與發展國際文獻匯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5.
卡塔林娜·托馬瑟夫期基著.畢小青譯.人口政策中的人權問題(第一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95.
張翔.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憲法空間.中國憲政網.2018-07-15.
徐玉梅、劉憲亮.關于獨身女性生育權的法律問題思考.中國醫學倫學.2003(1).31-32.
邵燕芬、金晶.非正常婚姻形式下的生育權探討.研究生法學.2002(4).25-31.
許莉.供精人工受精生育的若干法律問題.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99(4).31-36.
任順女.試論我國未婚女性生育權的完善.法制與社會.2008(18).85.
陳玉生.未婚媽媽關愛中心設立研究.社會福利(理論版).2015(5).17-22.
鄭秉文、春雷.社會保障分析導論.法律出版社.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