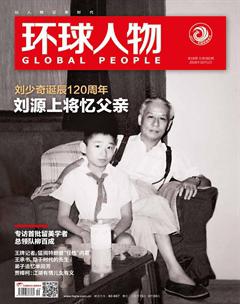林毅夫:1988年是我的分水嶺
尹潔
之前他信仰西方經濟學,之后他開始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問題
1988年是林毅夫的分水嶺。
無論哪個領域的翹楚,在其一生中,大抵總要經歷幾次里程碑式的轉折。就像經濟學家林毅夫改過兩次名字,每一次都在他的人生節點上。
第一次,他把本名林正義改為林正誼。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林毅夫還是一個“狂熱的國家主義者”,為蔣介石政權失去聯合國席位而怒不可遏,從人人艷羨的臺灣大學退學,轉到軍校當兵。第二次,他把林正誼改為林毅夫。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他從金門游到大陸,幾經輾轉,成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碩士研究生。但在林毅夫自己看來,對他的思想和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節點并非上面兩個,而是更晚一些的1988年。
1988年是林毅夫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歸國的第二年,是他躊躇滿志、決心將西方經濟理論付諸中國實際的一年,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深刻了解何為“國情”的一年。
在此之前,林毅夫將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師夷長技”上。這是自鴉片戰爭10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斷探求的道路。出國時,林毅夫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他所就讀的芝加哥大學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最高殿堂,林毅夫特地帶去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里以自勉。1987年回國時,林毅夫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到世界最先進的理論,足以改造中國經濟,現實卻給了他狠狠一擊。
1988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率,按芝加哥大學的理論,林毅夫認為應該提高銀行利率,增加投資成本,讓人們更愿意儲蓄而不是投資和消費,社會總需求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
然而,中國政府當時采取的是行政手段,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減少需求,看起來是一種“不理性、愚笨”的方式,卻引發了林毅夫的深刻思考:“從1978年到1987年,中國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是9.9%。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那為什么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
經過仔細了解,林毅夫才知道是因為大型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密集的行業里,如果把利率提高,大型國企就會有嚴重的虧損,政府只能給予財政補貼,導致財政赤字增加,于是就要增發貨幣,結果還是通貨膨脹。
林毅夫這才意識到,西方用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脹的目的,就是讓那些經營不善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提高經濟效率、恢復市場均衡。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采取的措施當然也不一樣。
1988年對林毅夫來講是一個分水嶺,他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根據國情來研究中國問題的人。他告誡自己必須把現有理論拋開,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后的限制條件是什么,決策者的目標是什么,然后考慮采取怎樣的措施。
齊白石有句名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百年來,世界上多少人、多少政府、多少民族都在“學”與“似”之間徘徊,從跟隨到引領者寥寥,從引領到開創者幾無先例。然而所謂大國之魄力,必然敢在滿目從眾者中堅定自己的信念與意志,借鑒而非照搬,直到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
走過5000年而香火不滅的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是“獨一無二”的。面對這種特殊性,作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嫡傳弟子的林毅夫,最終沒有選擇該學派的自由市場理論,尤其是在中國國企改革方面。
按西方理論,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國有制度,因此一些經濟學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則認為,產權是否私有與企業自身能力并無必然關系,私有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市場是否透明有效。因此,他一直強調在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在他看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干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資深副行長,當時世界上仍有大約14億人餓著肚子入睡,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貧困狀況觸目驚心。如何縮小它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林毅夫在世行思考最多的問題,他在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發表演講說:“我認為貧窮并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命運。”
部分非洲國家的經濟現狀與中國上世紀80年代初期非常接近:社會相對穩定,勞動力豐富、成本低,政府也相對有效率,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很高。這些國家要擺脫貧困,可以借鑒中國發展的經驗。
2011年8月,時任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接受林毅夫的建議,親自來華舉辦招商活動。兩個月后,廣東一家企業在埃塞俄比亞設立代表處,兩條生產線很快建立起來,機器、設備、主要原材料從中國進口,而600名工人都是當地的。2012年10月,工廠開始贏利,年底已經成為埃塞俄比亞最大出口企業。以今日“一帶一路”的眼光來看,林毅夫此舉是一次基于國情而有的前瞻性舉動。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是能預判發展趨勢的。
在外界看來,對于中國和中國經濟,林毅夫一直是堅定的樂觀派,他自己卻說:“我不是樂觀派,而是客觀派,但大家都悲觀,客觀就變成樂觀了。”在他眼中,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被感情所左右的文字表述,而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歷史必然,這正是他40年前游過海峽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