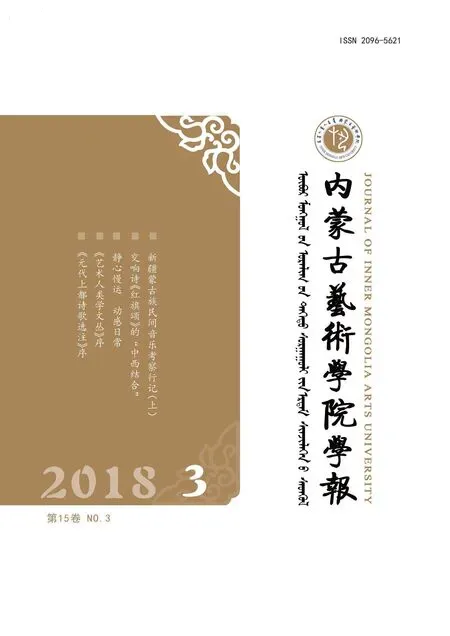交響詩《紅旗頌》的“中西結合”
——對作品主題、配器方式以及體裁和音樂結構的分析
李查寧畢丹
(1.2.內蒙古藝術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引 言
交響詩《紅旗頌》是我國著名作曲家呂其明先生于1965年創作的作品。樂曲主要描繪了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上,全國人民目睹天安門廣場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時的振奮人心的場景。同時,也展現了所有中華兒女為之感動,為之歡騰的面貌,謳歌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無數先烈為了祖國的革命事業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表達了炎黃子孫對祖國繁榮富強的美好前景的希望。同年5月,這部作品首演于“上海之春”音樂節,自此開始,其雄渾激蕩、大氣磅礴且細膩柔美、感人至深的旋律和音響,便回響在人們的耳畔,流淌于人們的內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紅旗頌》仍然經久不衰,時常上演于國內外重大的音樂場合,它也被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評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可以說,《紅旗頌》勾勒出了每一位中華兒女心中的那幅關于五星紅旗的圖畫,也奏響了每一位中華兒女心中的熱愛和歌頌我們偉大祖國的旋律,更是激勵著中華兒女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宏偉目標去拼搏奮斗。
《紅旗頌》之所以被人們歡迎并廣為流傳,與作曲家呂其明先生的精妙創作是分不開的。這部優秀的交響樂作品在涉及音樂創作的許多方面上都體現出非常值得研究與學習的技術特色。然而,筆者認為,在使該作品能夠成為經典的眾多因素中,最為重要的則是作曲家在創作過程中對西方藝術音樂寫作技術進行個性化靈活運用的同時,又融入了于宏觀及微觀角度將中國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的寫作思維和旋律音調所進行的技術化與藝術化的處理。這種體現于作品中間的創作理念和寫作技術的共性與個性的并存,也可以被理解為“中西結合”的創作思維,它們理應是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應是這部作品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筆者試圖通過從充分體現上述特征的作品的主題、配器方式、以及體裁和音樂結構等角度對樂曲進行分析,并結合作曲家的個人經歷以及作品的創作背景,來了解作曲家在宏觀創作理念和具體寫作技術方面對“中西結合”思維的實際把握及應用的情況,以初步認識和掌握蘊含于該作品中的涉及以上方面的創作理念與寫作技術的內涵。
一、主題的“中西結合”
可以說,《紅旗頌》所獲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樂曲開篇的那段深入人心的歌頌紅旗的主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紅旗主題”的產生,便成就了這部人們心目中的經典作品。的確,這部作品的主題,是中國現當代交響音樂作品范圍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片段之一,時至今日,無論是專業領域還是聽眾,仍將其視為上乘之作,并廣為傳誦(見譜例1)。
譜例1
眾所周知,“紅旗主題”中的旋律悠揚大氣,洋溢著熱烈的情感且極富感染力,這其中必然體現了呂其明先生出眾的創作才華。但是,該主題也不是靈光一現的產物,在創作思維和技術層面上,其音高材料本身及其所反映出來的具體的展開方式則帶有著明顯的“中西結合”特點,這來自于作曲家精彩的手筆。
可以看出,“紅旗主題”是一個四句式的樂段,前三句均為四小節,第四句有所擴充,為八小節,這樣的較為方整的結構具備西方藝術音樂作品的曲式特征,而其中音高材料的陳述方式則始終體現著典型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特點。就調式來看,雖然主題中的音高在半音關系上可以被納入自然大調的范圍,但在實際上,音高材料在進行的過程中則反映出中國傳統七聲調式(清樂音階)的音高關系——主題中所包含的所有“B”音都沒有出現直接進行至“C”音的現象,而是上行三度進行至“D”音或下行二度進行至“A”音,這顯然不符合自然大調中的導音進行到主音的音級進行的規律。因此,這里的“B”音就明顯代表著“變宮”音的意義。可見,單從這一方面,就可以初步論證“紅旗主題”的旋律中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本質及其所帶有的“中西結合”特征。
從整體上全面地觀察主題,就能夠更為清楚地發現其中所具有的民族化特點。主題的音高材料在進行的過程中都基本體現了以三音列為單位的、在純四度范圍內的大二度與小三度(或反之)相結合的陳述方式(在帶有“清角”和“變宮”兩個偏音的樂句片段中,若將其忽略不記,亦能呈現出上述的三音列進行的狀態),這便是屬于中國民族調式范疇的音高材料的典型進行狀態。[1](52-53)同時,從每個樂句或樂節的結尾音來看,它們包含了同宮系統下的各個旋律音,并結束于徵音上,也就是說,“紅旗主題”通過歷經“商”“羽”“角”“宮”四個音的逐次停頓之后,最終則確立了徵調式來作為其調式基礎,而徵調式也是中國民族民間音樂領域內的漢族地區最為常用的調式。[1](54)此外,主題中的樂句首音與前一樂句的尾音相同(從第二樂句開始,而第四樂句則不是十分嚴格),這也體現了我國民間音樂中的一種較為常見的旋律發展方法——即“魚咬尾”或“頂真格”——所包含的特點,著名的民間音樂《春江花月夜》就是展現這種旋律發展手法的典型作品。[2](27)
由此可見,不論是基于中國民族調式的三音列進行,還是徴調式的核心地位,以及“魚咬尾”(“頂真格”)式的旋律發展狀態,都明顯反映了“紅旗主題”所具備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典型特征。這樣的主題,在西方藝術音樂中的樂段結構中,仍然得到了自然地展現,其旋律收放自如,又不失整體感,且完美地詮釋并表達了其所象征的意義和作曲家的思想感情。總而言之,“紅旗主題”充分地反映了“中西結合”這種創作思維,也是具體表現這種創作思維的優秀范例。
對于作曲家來說,創作此類既體現著西方傳統音樂的寫作技術內涵,又不失純正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風格的主題,自然是一條高水準的要求——在全面且充分地掌握創作技術的同時,還應具備深厚的民族民間音樂底蘊,而呂其明先生就是一位符合這種標準的優秀作曲家。
呂其明先生1930年生于安徽省無為縣,他的父親呂惠生先生是當地著名的教育家,抗戰爆發后,又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40年,呂惠生先生將他10歲的長子送到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抗敵劇團”。從此以后,年少的呂其明便開始受到了音樂的熏陶與啟蒙教育。
1942年夏,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先生來到淮南抗日根據地并為“抗敵劇團”的團員們教授了三個月的音樂理論與作曲知識,也使熱愛音樂的呂其明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音樂教育。可以說,賀綠汀先生是呂其明在音樂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師,他鼓勵呂其明學習音樂,激發了呂其明創作音樂的熱情。此后,呂其明便開始了他的作曲生涯,不論是在解放以前的部隊生活中,還是在解放以后任職于北京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和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生活中,他都以充分的熱情積極地進行著音樂創作。1956年,呂其明應邀為著名導演趙明先生的影片《鐵道游擊隊》作曲,他潛心研究原著,還進行了大量的采訪和采風的工作,并挖掘自己多年來對山東民間音樂的積累,最終創作出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雖然在不到30歲時,呂其明已成為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并擔任著上影樂團的團長。但是,勤奮好學的呂其明仍感到自己在專業知識上的缺乏,因此,從1959年開始,他又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學習了5年作曲和2年指揮。雖然未完成10年的學習計劃,但是,這段系統學習的光陰,也成為了呂其明先生的藝術創作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經歷。
可以看出,對于呂其鳴先生來說,從早期對音樂的感性接觸及認識,到后來進入音樂學院進行專業的學習,就是一段感知音樂的“中西結合”的過程——在抗敵劇團的實踐以及對電影音樂的創作,使作曲家具備了理解民族民間音樂內涵和運用其音樂元素的能力,而在音樂學院的學習也為其打下了創作技術的基礎,全面提高了音樂創作的水平。因此,這段難得的人生經歷,就是解釋作曲家能夠在創作中靈活地運用“中西結合”思維的原因的根據。
從和聲上來看,“紅旗主題”則進一步反映出“中西結合”的創作思維,主題的和聲基本是以三度疊置的和弦為主,這在引子中就已經有所展現——位于樂曲開始處并由小號奏出的分解三和弦顯然來自《義勇軍進行曲》,而以其作為引子的動機,在一定程度上也預示了作品的和聲風格(見譜例2)。
運用和弦來配置和聲,明顯是經過學習西方藝術音樂寫作技術之后的結果。然而,從主題中的全部和弦的走向上來看,其運行方式也并未完全遵循功能和聲的連接原則。具體來說,這些和弦基本上都是伴隨著旋律而出現的,呈現出一種“旋律加伴奏”的狀態。因此,在“紅旗主題”的段落中,旋律對于和聲的選擇是處于支配地位的,而和弦功能的作用則被有所淡化。可見,這樣的音樂風格在宏觀上直接體現了“中西結合”的創作思維。
對于呂其鳴先生來說,設計出這樣的和聲風格也是絕非偶然的。由于主題的旋律本身就包含著多種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特點,所以,若機械地將其納入功能和聲體系,所產生出來的音響和音樂形象必然會十分生硬且不貼切。由此可見,“紅旗主題”段落中的和聲應是作曲家的精心創作,而就聽覺感受上來說,這個片段的和聲效果舒展自然,張馳有度,涉及到每一個旋律音的和弦都恰到好處,為音樂的抒情性和描繪性都增添了濃重的色彩。
譜例2
在“紅旗主題”結構內部的和聲細節上,還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現象,即數次呈現出上四度關系的和聲連接狀態,它們在主題進行的過程中非常有效地不斷增加著音樂的張力,其原位的低音進行在引子中,也就是在樂曲的第一小節就已經被展現了出來(見譜例3)。顯而易見,這種和弦連接在音程關系上與西方功能和聲體系的屬和弦——主和弦的解決是一致的。但是,介于之前所提及的在“中西結合”思維下的“旋律加伴奏”的和聲風格,所以,這并不意味著上述四度關系的和弦連接能夠將其與功能和聲中的離調狀態等同起來。實際上,這種四度關系也可以在中國民間說唱音樂中找到充分的依據。例如,“同宮換主”或“換宮換主”的轉調方式,就與變換調式或調性的上四度和弦進行相似。[3](80-81)可見,運用西方化的和弦,并將它們以中國式的音樂發展原則聯系起來,對于技法純熟,又深諳民族音樂文化的呂其明先生來說也許并不生疏,而這樣的創作方式也正是“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具體表現。
譜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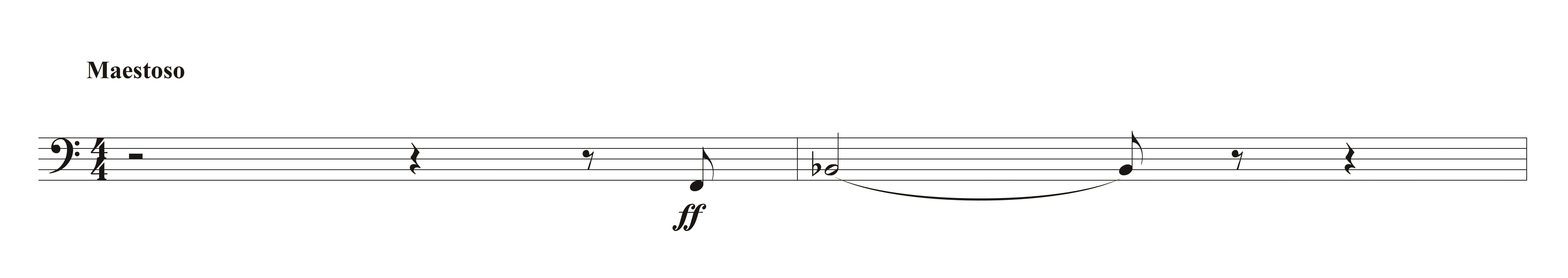
此外,主題中所出現的bVI級和弦,也為旋律在情感性和音響的豐富性上都增加了極大的表現力。而且,從主題的整體上來看,該和弦位于第三樂句中,這就在音樂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轉折”的效應,使得音樂更為跌宕起伏,也更為激動人心。因此,盡管該和弦在“紅旗主題”中僅有一次呈現,但其作用和地位仍然不可忽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運用該和弦也與作曲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音樂作品的整體風格有關,然而,就“紅旗主題”而言,呂其明先生對其處理的方式是十分妥當的,使其依照一種源于中國風格的創作思維而呈現出來,并發揮了與在西方調性音樂中同樣的作用。
二、對配器方式的分析
作為一部成熟的交響音樂作品,《紅旗頌》以其時而鏗鏘、時而淡雅、時而恢宏、時而精巧的樂隊音響而令人難以忘懷。因此,這些豐富的音響必然值得分析與推敲,蘊含于其中的樂隊寫作技術也必然值得研究與借鑒,同時,它們也充分體現著呂其明先生的創作功力,而這樣卓越的創作成果幾乎完全得益于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多年的潛心學習。可見,完成一部成功的交響樂作品,既需要非凡的創作靈感,更需要深厚的技術功底。
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的時間里,呂其明先生非常地努力,他十分珍惜這寶貴的學習機會,盡管要兼顧工作,但他并未減少學習的時間,而是放棄休息,以完成學習的任務,他日復一日地堅持著。就這樣,在他的藝術生涯中,又增添了五年的作曲專業學習和二年指揮專業學習的寶貴經歷。在此后的歲月里,呂其明先生始終對學習的時光難以忘懷,對老師和同學們心存感激。他曾表示過,如果沒有這段在專業院校的學習生活,他是不可能寫出交響音樂的。可見,這若干年的學習,為呂其明先生日后創作《紅旗頌》奠定了扎實的技術基礎。
由于是隸屬西方管弦樂種類,因此,作品基本體現的還是呂其明先生對于西方管弦樂創作技法的運用。然而,其中也不乏作曲家的個性化創作,更為重要的是,“中西結合”創作思維仍然蘊含于作品中,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作品的樂隊編制是較為典型的雙管樂隊配置,但使用了三支小號,并加入了短笛、鋼琴和豎琴以及部分打擊樂器。在全曲的不同段落中,配器的方式也顯示出明顯的對比。在“紅旗主題”的引子中,衍生于《義勇軍進行曲》的音高材料首先由小號奏出,其反映著帶有如同號角般或宣言式性質的音樂內涵,也揭示了“紅旗主題”的大致形象特征,同時,這一音高材料也貫穿于主題中,用于間補或者連接等部分,然而,其每一次的出現都始終位于銅管聲部,可見,這顯然來自于作曲家的有意安排——描繪這樣一種音樂形象,銅管樂器能將其表現的最為貼切。
在第一個段落中,“紅旗主題”完整地出現了兩次,首先是由弦樂組以兩個八度的形式單獨奏出,隨后,則將木管樂器與其重疊并再次演奏主題,而為主題伴奏的和聲主要是由木管組和銅管組來承擔的(主題在第二次呈示的過程中,則由銅管組單獨演奏和聲)。可以看出,以弦樂組來演奏“紅旗主題”是非常合適的,有利于演繹主題的抒情性及幅度較大的舒展性,而且,兩個平行八度的形態也將主題寬廣大氣的特征體現得更為明顯。此外,利用混合音色來第二次詮釋主題也反映出作曲家在創作中的匠心獨具,很顯然,這對于加重主題的音響色彩,加大情感的表達深度都能起到有力地推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紅旗主題”段落中,呂其明先生對于鋼琴的寫作也花費了濃重的筆墨,可以看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俄羅斯作曲家的音樂創作的影響,如柴科夫斯基的《bB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中就包含了與之相似的片段。然而,就“紅旗主題”段落而言,鋼琴所發揮的作用卻是不可替代的——在主題的第一次呈示過程中以柱式和聲的形態出現,非常有效地強化了樂隊的音響,使得音樂剛勁有力,也為其增添了堅毅的個性;伴隨著主題的第二次出現,鋼琴的織體則換成了分解和弦式的琶音,它們所帶來的流動效果有力地加強了對情感的渲染力度,也使得音樂更加地激情洋溢。
雖然,從呂其明先生對鋼琴的巧妙編配上能夠找到借鑒的因素,但是,其中還是體現出了明顯的個性化創作的特點,而且,在樂隊寫作過程中使用鋼琴也是同時期國內音樂創作的整體趨勢。因此,這種在當時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配器方法就可以被看作是對“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具體運用。
在位于紅旗主題之后的抒情段落中,音響的厚度和力度明顯有所降低和淡化,旋律首先由獨奏雙簧管奏出,伴奏的角色則由弦樂組擔任,與此同時,豎琴開始演奏分解和弦式的琶音。可見,上述三者的音響效果,與之前的段落呈現出明顯的對比,更為柔和悠揚。隨后,圓號與兩組弦樂同度演奏旋律,其他的弦樂器與大管聲部則演奏對位線條和低音,長笛與單簧管聲部以及加弱音器的三支小號基本以平行三和弦的形式分別演奏引子中的音高材料(之前所提及的宣言式的主題),而豎琴的織體仍然與之前一致。同樣的旋律在第三次出現時則有所展開,首先由兩組小提琴以平行八度的方式演奏,并加入了與之相應的位于中提琴和大提琴聲部的呈卡農式模仿狀態的音高材料,這時長笛和單簧管則在它們的中音區演奏用于對位的音樂材料,大管聲部仍與貝司聲部演奏低音。隨著音樂的進一步展開,木管樂器則再次演奏著旋律(或為獨奏,或為不同樂器共同演奏,或與弦樂器構成混合音色),整個片段中的銅管樂器的分量呈現出逐漸加重的狀態——先是演奏和聲,隨后逐漸活躍并開始演奏引子中的音高材料,并以卡農式模仿和加大音量的方式將其推向高潮,并將音樂過渡至下一個段落。
就配器的方式而言,抒情段落中所體現的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旋律聲部的音色由單一逐步轉向復雜,由稀薄逐步轉向濃郁。由此可見,在主題旋律最后一次出現時取消帶有軟化樂隊音響作用的豎琴顯然也是作曲家有意地設計,這使得音樂能夠更為自然地與之后的強段落構成銜接。
作品的快板段落中的節奏最為緊湊且富有動力感,形成這樣的音響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于樂隊所演奏的織體。可以看到,由八分音符三連音構成的等時值音高材料幾乎完全貫穿于整段中,無論是位于弦樂組還是木管組,它們都是以跳弓或跳音的方式被演奏出來的。銅管組在此時也得到了大量的應用,旋律、伴奏及低音等因素都得到了該樂器組的充分演繹。鋼琴與不同樂器組的分別重疊,以及打擊樂器的加入,更是有效地加強了音響的力度,也為樂隊的整體音色增添了一定的硬音質的特性。總而言之,這一系列的配器手法使得該段的音樂明顯具有著進行曲的特征,且形象也十分鮮明,與前后的段落形成了顯著地對比,因而有效地實現了作曲家的構思(而對主題材料的節奏所運用的緊收方式,也明顯反映出作曲家對于該段的創作立意)。
與之前所提及的段落相似的是,呂其明先生對于主題在有所重復的情況下所采取的配器方式,仍是用單一音色與混合音色進行對比。這種在創作技法方面的有機統一,也必然會使音樂從局部至整體都將具有一定的邏輯性。
由于樂曲的最后一個段落包含著對首段再現的性質,且都是對“紅旗主題”原形的完整演繹。因此,在分析的過程中,可將二者加以對照。縱觀兩段音樂,對比最為明顯的就是配器的方式:首先,與之前相比,再現段落中的主題直接運用弦樂加木管的混合音色來演奏,而取消了與單一音色的對比,而且,在尾聲中,對伴奏織體的表現仍是以這種混合音色為主,使音響更為復雜;其次,銅管樂器的使用密度更大,并在織體中增添了更多源于引子的音高材料的、具有流動性特點的音型,增加了音響的強度和動態效果;此外,對打擊樂器的使用也更加頻繁,使得音響更具深度。顯然,這個段落在樂隊音響方面具有了更為廣泛的包容性,隨之形成的音樂形象也更具內涵,使之前所表達的思想與情感都得到了進一步地升華,因此,單從配器的變化上來看,就已經能夠明確該段落屬于動力再現的類型。
從作品所涉及的調性中也可以領會到呂其明先生基于配器方面的考慮,樂曲中的幾個主要段落所涉及的調性都是非常易于樂隊把握的。例如,在銅管組所占比重較大,速度又較快的段落里,作曲家選擇了bB大調,這顯然是出于對銅管樂器的考慮,使其更加容易發揮。而建立于C大調和D大調的音高材料對于樂隊的演奏來說,也是十分便捷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紅旗頌》在配器上的成功之處,就樂隊寫作技巧而言,這部作品也完全可以作為中國當代管弦樂創作的優秀范例。然而,樂曲除了體現出對西方創作技法的熟練運用之外,其中所蘊含的“中西結合”創作思維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作曲家對鋼琴的重視,將單一音色與混合音色進行對比的處理方式,在抒情段落中對獨奏樂器的選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內管弦樂作品的普遍風格。因此,《紅旗頌》的創作,必然不是呂其明先生對于西方藝術音樂創作的單純模仿,而是靈活運用“中西結合”創作思維之后所產生的成果。
三、體裁與音樂結構的“中西結合”
交響詩是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音樂的典型體裁,由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茲·李斯特首創。其主要的特征是單樂章結構,內部包含著速度與性格相異的幾個音樂片段,并通過戲劇性的沖突發展而融合為一個整體,另外,其內部結構也帶有奏鳴性,即傳統奏鳴曲式所包含的呈示、展開及再現的三部性特點,但是,在調性的設計上卻是較為自由的。李斯特創作交響詩所運用的主要手法則是應用單主題貫穿發展的模式。可以看出,選擇這種體裁來創作《紅旗頌》,也應是呂其明先生經過深思熟慮之后的結果。
對于呂其明先生來說,《紅旗頌》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委約創作”。1965年2月,在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的一次審議第六屆“上海之春”音樂節初選曲目的會議上,包括賀綠汀、丁善德、孟波、黃貽鈞、瞿維、鐘望陽等音樂家一致推薦年齡最小的黨組成員呂其明來創作一首頌歌般的作品來獻給黨和人民。而“紅旗頌”這個題目,就是由老一輩著名指揮家黃貽鈞先生擬定的。
這次“委約”寄托著前輩們的關懷、信任與期望,也激發了年輕的作曲家心中的為祖國做奉獻、為黨和人民做奉獻的創作欲望。擔負著光榮的任務,懷著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對革命先烈的敬仰與緬懷,經過數日的思索,呂其鳴先生最終設定了作品的體裁,并努力將自己的所有感情都融入到音樂的創作中,僅用了非常短的時間,他便將《紅旗頌》的初稿創作完成了。
顯而易見,《紅旗頌》首先體現出呂其明先生對西方藝術音樂創作理念的遵循——以西方浪漫主義風格的交響詩體裁來限定作品。然而,《紅旗頌》在具體的寫作個性上也是較為突出的,明顯地反映了作曲家個人的創作風格。與西方典型的交響詩不同的是,《紅旗頌》并未包含強烈的戲劇沖突,主題材料基本都是被較為平穩地敘述出來,沒有得到戲劇性的發展,即使是中間所出現的進行曲式的變奏段落,其主題材料也屬于呈示性的陳述方式。因此,西方音樂的固定體裁得到了作曲家自由化地處理,則完全是“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充分體現。
實際上,這樣的處理方法也是非常符合作品的創作意圖的。筆者認為,《紅旗頌》在思想性上并不是十分復雜,它像一首頌歌,基本上是單純地表達著作曲家對偉大祖國的熱愛。盡管音樂時而激情澎湃,時而甜美悠揚,但在總體情緒上都是非常樂觀的,整部作品中沒有出現明顯的對立因素。在調性方面,該作品也沒有像西方典型的交響詩那樣,出現奏鳴曲式般的調性對置。樂曲中所出現的調性變化基本上是屬于色彩性的,大致都是以模進式的換調為主,如引子為bB大調,“紅旗主題”的第一次陳述為C大調,第二次則進入D大調。總而言之,《紅旗頌》的寫作既遵循了源于西方的創作理念——選擇西方藝術音樂范疇內的傳統的管弦樂體裁;又彰顯出作曲家本人的創作個性——淡化了音樂材料的戲劇性展開以及調性的具有奏鳴曲式特點的對置。
以音樂結構為出發點縱觀全曲,首先能夠較為直接地發現作品所具有的再現特征。也就是說,在樂曲中,“紅旗主題”段落出現在引子之后,并且在樂曲臨近結束時又進行了再現式的陳述,其次,在樂曲的中間,還出現了一個非常抒情的段落以及一個進行曲式的段落。此外,后三個段落之間都明顯存在著連接。可見,整部作品的內部結構的界限是比較清晰的,全曲基本包含了上述的四個主要段落、三個連接的片段、以及由源自《義勇軍進行曲》的音高材料所構成的較為簡短的引子和尾聲。
之前所提及的樂曲的四個主要段落中的音高材料是比較統一的,盡管中間的抒情段落和進行曲風格的段落在音樂形象上的個性十分突出,其相互之間的、或與其他段落之間的對比也比較明顯,但如果仔細推敲其中的音高材料之后便能夠看出,抒情段落中的音高材料就是源于“紅旗主題”(見譜例4)的,而其后的進行曲風格的段落中的音高材料則是和“紅旗主題”幾乎完全一致。
譜例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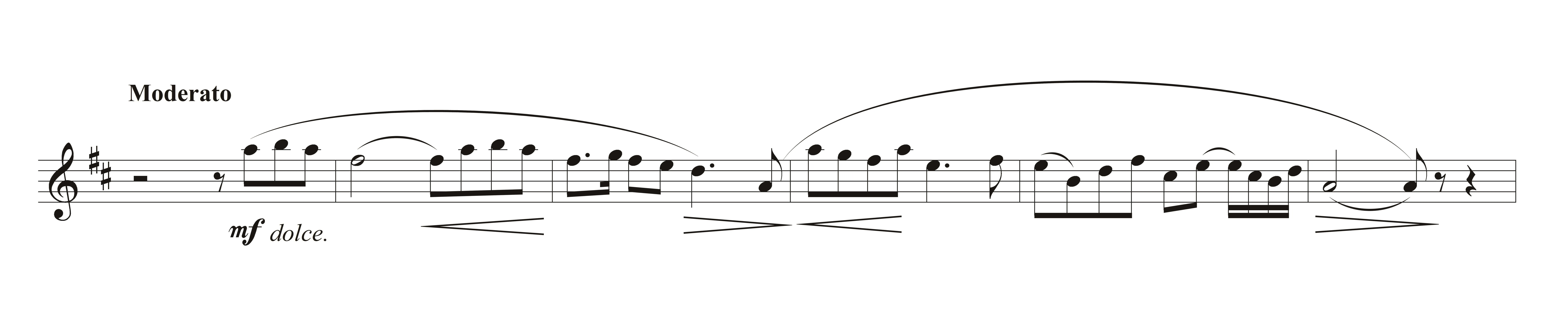
雖然從音樂的力度和風格上,抒情段落與它前后的段落相比較,都具有著較大的差異。但是,從例4中可以看出,這個第一次由雙簧管演奏出來的抒情主題,應是來自于“紅旗主題”的第四句,這個抒情主題的兩個樂節的結尾音與“紅旗主題”第四句的兩個樂節的結尾音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宮音和徵音)。該主題的第一個樂節的音高材料可以看做是從“紅旗主題”的第四句中截取下來的,唯一不同的只是先重復了一次原樂句的第一個動機,而第二個樂節與“紅旗主題”相比,二者的旋律骨干音也是完全相同的,只是略加變化,這可以看作是一種變奏式的發展。經過不同樂器組的幾次反復演奏之后,單簧管聲部奏出了一個新主題,它與之前的主題也較為近似,應是衍生于其中的。由此可見,這個抒情段落,與之前的“紅旗主題”是有著密切聯系的,兩者間存在著主題與變奏的關系——抒情段落的音樂主題采用了“紅旗主題”的最后一個樂句,并對其進行了變奏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變化發展。
之后的進行曲風格的段落則更是簡單明了,實際上,這個段落就是對“紅旗主題”的性格變奏,與“紅旗主題”相比,該段落增添了貫穿始終的、由等時值八分音符構成的三連音音型,而主題材料則在節奏上進行了緊縮,這些新的因素也使該段落在氣息上更加短促,節奏上更為緊湊,更富動力性,因而具有了一種嶄新的、進行曲般的音樂風格。
以往有些分析曾認為《紅旗頌》的音樂結構是復三部曲式或是三部性的結構,就是將抒情段落劃分為連接段,將“進行曲”段落劃分為中段或插部,或展開部。對此,筆者認為是有待商榷的。首先,抒情段落在音高材料和調性方面,總體上都是比較穩定的,沒有出現較多的變化,音高材料的陳述更趨向于呈示性,整個段落的調性也沒有出現過多的轉換,只出現了一次“清角為宮”式的轉調。其次,在這個段落與下一個段落之間雖然有連接,但在連接片段中并沒有出現向下一個段落明顯過渡的因素,其后的段落的出現是較為直接的。可以說,這個抒情段落中沒有體現出明顯的連接段所具備的功能特點,它在整首樂曲中則是相對獨立的。
筆者認為,全曲的第三個段落也不具有插部或展開段的特點,整個段落與前一段相同,在音高材料的陳述上是呈示性的,在調性上也較為穩定。因此,這個段落并不帶有典型的插部或展開段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整體的角度來縱觀全曲的四個段落,就能夠發現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著四樂章交響套曲的特征。例如,中間的抒情段落和“進行曲”段落類似于交響曲的第二、三樂章,而“紅旗主題”段落的首次呈示和位于全曲末尾的再現則意味著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和末樂章。可見,作曲家在對音樂結構的設計上有意地結合了來自于交響套曲的創作思維,并且效果顯著。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由于作品中間的兩個段落是以不同的方式對“紅旗主題”所進行的變奏,使樂曲帶有了主題加變奏的性質,而最后一個段落則是對“紅旗主題”的動力再現,這又增添了再現曲式的特點,整部作品還反映著交響套曲的特征。因此,《紅旗頌》的音樂結構,不應該定義為任何一種固定的曲式類型。一方面,其音樂結構并沒有完全禁錮于某一類曲式的框架內,這是作曲家創作個性的反映;另一方面,明顯的再現特征與交響套曲的結構性質則反映出作曲家對西方作曲技法的借鑒。因此,可以認為這部作品是將屬于西方藝術音樂典型創作技術范疇的再現因素與交響套曲因素,加之源自中國民間音樂的“寫意”風格的、較為自由的音樂發展方式來創作而成的,這充分地反映出作曲家對“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深刻理解,并已獨具匠心地將其巧妙運用于音樂創作的過程中。
結 論
通過對《紅旗頌》的主題、配器方式及體裁與音樂結構的觀察與分析,以及對蘊含于其中的“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探究。可以看出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方面:第一,作品的主題在音樂結構上可歸納為西方藝術音樂范疇內的樂段形式,但其中旋律的音高材料的展開狀態則是完全依據著源自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發展規律。如C大調中的“B”音的偏音性質、純四度范圍內的二度和三度相結合的進行方式、“魚咬尾”(“頂真格”)似的樂句間的關系,在調式上,也完全遵循著中國民族調式的音高關系,并突出具有典型漢民族音樂風格的徴調式在主題中的地位,在和聲方面,以使用代表西方音樂風格的(三度疊置的)和弦為主,但對于和弦間的功能關系則有所淡化,而是服從于旋律的走向,呈現出“旋律加伴奏”的狀態,并且,對音樂發展起到有效推動作用的、主題中所出現的數次類似于西方功能和聲的屬和弦——主和弦解決式的呈上四度關系的和弦連接,則是由中國民間說唱音樂中的“同宮換主”或“換宮換主”等轉調方式來支配的,同時,對富于和聲張力的bVI級和弦的應用,則是作曲家所處時期的音樂創作的總體風格趨勢的體現;第二,樂曲的配器雖然基本借鑒了作曲家所系統學習的西方管弦樂寫作技術,但在其中仍能夠看出其對樂隊寫作技術的個性化處理方式以及“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具體表現——以單一音色和混合音色相對比的方式來表達音樂發展以及情感渲染的深化,以銅管組的使用密度的變化來增加或削弱音響的強度,以連續不斷的等時值音符式的織體來形成音樂的律動感并營造出進行曲般的節奏氛圍,以音響厚度及音色濃度的加深來體現動力再現的效果,同時,對鋼琴的使用應是受到了柴科夫斯基作品的影響,然而,鋼琴音色在《紅旗頌》中的出現是恰到好處的,例如,柱式和聲適時地增加了音響的硬度,而分解和弦式的琶音也加強了音樂的動力,并使音樂激情洋溢,與之相對應的,對豎琴的應用則使得音響得到軟化,使抒情段落的音響效果更加柔美,此外,作品中的幾個主要調性則非常有利于樂器演奏的便捷,可見,這應來自于作曲家的精心設計;第三,呂其明先生雖然選擇了交響詩這種西方藝術音樂領域中的重要且典型的體裁來進行創作,但是,與西方傳統的交響詩相比,《紅旗頌》則淡化了音高材料、調性等方面的戲劇沖突,這也是作曲家創作個性的彰顯,更是“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體現,另外,在《紅旗頌》的音樂結構中所蘊含的變奏因素、再現因素與四樂章交響套曲的結構性質,以及所體現的未遵循某種固定曲式原則的較為自由的結構特點,仍可以被看作是“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作用及影響。
總而言之,《紅旗頌》的音樂既反映出對各種寫作技法的廣泛運用,又體現出作曲家突出的個性化的創作風格特點;既具有著明顯的西方藝術音樂作品的交響化及器樂化的性質,又保持著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韻味,而正是這些因素,則是這部作品獲得成功并成為經典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至此,筆者認為,《紅旗頌》對于當代音樂的創作而言,也是一個優秀的范例。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中西結合”創作思維的巧妙運用,以及對創作共性與個性的結合度的把握,都為當今的音樂創作提供了眾多可參考的經驗以及可借鑒的技術手段。從專業角度來說,這也正是這部作品的最高價值及解讀、分析與研究這部作品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