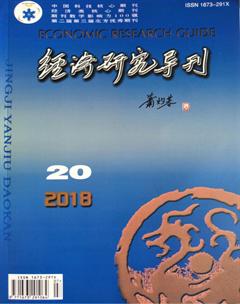鄉村旅游視域下“游客家園感”概念初步建構
閆春平 陳海鷹
摘 要:將“家園感”這一美學概念引入旅游研究中,以相關理論為依據,結合海口市龍鱗村的案例,在鄉村旅游語境下,探尋游客家園感的形成背景、形成機制及本質屬性,從而對“游客家園感”這一概念進行初步建構。“游客家園感”可初步定義為,一種在現代性結構化社會背景下,游客對自身生活現狀反思的情感產物和心理訴求,同時通過與鄉村旅游情境的互動體驗,衍變出的具有實有性、親和性、本土性、深沉性以及延續性的主觀感受。研究成果有助于進一步豐富“家園感”的概念內涵,并為實踐中的鄉村旅游產品創新、服務升級等提供借鑒依據。
關鍵詞:鄉村旅游;游客家園感;形成機制;本質屬性;龍鱗村
中圖分類號:F590.7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8)20-0128-03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聯結鄉村和旅游的紐帶,鄉村旅游強調休閑、回歸山野及淳樸的鄉風民俗文化體驗。保存相對原始與完整的鄉村之境,可喚起人們對自然的熱愛和尊重;而鄉村事物作為地方文化的載體,可引發人內心深處的鄉土情結以及對心理歸宿和精神家園的回歸,迎合了都市人“回歸自然、回歸淳樸、釋放真我”的價值需求。與此同時,鄉村旅游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大中城市周邊鄉村地域傳統農業生產功能逐漸減弱引起的經濟貢獻退化、鄉村經濟新生動力不足等問題,為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帶動鄉村居民脫貧致富、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等提供重要途徑。但在現實中,旅游產品鄉土性缺乏、同質化嚴重、鄉村原生意境破碎等,依然是目前鄉村旅游在深化游客體驗感、提升游客滿意度和忠誠度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基于此,本文從游客“追憶鄉土,回歸家園”的旅游訴求切入,對于可激發游客鄉村旅游需求的“家園感”這一概念的本質屬性,以及鄉村旅游場域中“游客家園感”的形成機制等問題進行理論層面的探析,以此回答“鄉村旅游中的‘游客家園感是什么?”“‘游客家園感的價值意義何在?”等問題,并為鄉村旅游實踐中“游客家園感”的塑造及強化提供合理依據。
二、文獻回顧
“家園感”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人們對人類所處生存環境的現實反思。陳望衡認為,環境美的根本性質為“家園感”,指出“家園感”本質上是對這塊土地的親和感、依戀感和歸屬感[1];之后,其又創造性地將環境美的“家園感”衍化為環境美的功能——“樂居”[2]。王琳闡釋了環境美學視角下“家園感”的理論前提及其特性,指出對于著眼于人類總體環境的“家園感”應更多地取哲理的維度,而著眼于某些人們具體環境的“家園感”應更多地取生活的維度[3]。依此思路,本文將“家園感”的兩個著眼點歸結為慣常生活環境中的“主人”(本土居民)以及短期或長期外移至此環境中的“客人”(非本土的大眾群體)。這一解讀可從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得以驗證。例如,張檸從本土居民的視角對農民的家園感進行反思,認為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漂泊生涯中,他們都會心生不適[4]。此外,程磊從“游子”(非本土的大眾群體)角度,通過對羈旅行役詩中家園感呈現的意象形態進行研究,提出家園意識始終牽引著游子行旅的精神指向,家園感產生于生命歷程的切身體味中,常需借助特定的情境意象而加以呈現,并將行旅之人在山水之間得到安頓生命的補償,進而達成人與自然的親和,提升到一種“寥廓深邃的宇宙意識”的層面[5]。
作為整體概念,“家園”強調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喚起鄉民的主人翁意識和歸屬感,是一種富有情感的生活空間、環境優美的宜居之地,也是游子心中的美好向往與夢想[6]。張文祥認為,桂林山水最美的是它的詩境家園。劉玲等將鄉村旅游者追尋的鄉土情結內容劃分為物質情結、家園情結、文化情結、人際情結四個維度,各維度正向驅動旅游情感動機的形成[7]。黃潔提出,鄉土情結是人類從心理上否定了逃離自然的行為后所產生的尋求心靈歸宿的特殊情結,具體表現在中國人身上就是“土地情結”和“家情結”[8]。本文認為,這種鄉土情結內連于心并以“鄉愁”外顯于形,在某種意義上,與“懷舊”有著極大的共通性,與“家園感”也有著共同的語義。國外學者羅蘭·羅伯森指出,現代性所帶來的變遷本身也招致對世俗的世界秩序的懷舊,以及對家園世界的某種前瞻或鄉愁[9]。熊劍峰等認為,懷舊就是向往過上一種“簡單和溫暖的生活”,指出懷舊旅游是游客渴望通過旅游重溫傳統意義“家”的體驗,確認自我身份、尋求生存的意義和生命的歸屬[10]。此外,陶玉霞從歷史演進和意識建構角度闡釋現代鄉村旅游的原根性訴求,將回歸鄉土的實質歸結為“在尋找家園中獲得身份認同與信仰重建,讓生命重新扎根于厚重的土地,讓靈魂回家,溫習久違的淡泊與寧靜”[11]。
綜觀現有文獻,雖然有關鄉村旅游的研究成果頗豐,有關鄉村旅游者情感訴求的理論和研究方法體系也漸趨完善,但著眼于對鄉村旅游者內在情感訴求和體驗,特別是解析其情感訴求形成機制等的研究尚不多見。同時,將“家園感”這一美學概念引入到鄉村旅游研究中并對“游客家園感”的本質屬性及其形成機理進行解析的研究更為鮮見。因此,本文嘗試在既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海口市龍鱗村的案例實踐,對鄉村旅游視域下“游客家園感”這一概念及其形成機制進行理論建構,以期在鄉村旅游語境下進一步豐富“家園感”的概念內涵,并為著眼于“游客家園感”構建的鄉村旅游產品開發和服務創新等實踐活動提供有益參照。
三、游客家園感概念建構
(一)游客家園感形成背景
印第安人民諺中有一句描述:“我們走得太快,該停下來等等自己的靈魂了。”這句民諺同樣適用于中國社會。在現代化發展語境下,鄉土空間的消失、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導致的傳統農耕方式、民俗文化等的遺失,不僅帶來鄉村寂靜下的鄉土破碎,還造成游離在城市的人群對鄉愁的情感詮釋愈發模糊,加上“生于斯,長于斯”,而未能“活于斯”的缺憾,致使這一群體的鄉土情結越來越強烈。此外,現代性所引發的環境危機、個人生活歷程的時空斷裂、文化價值觀,生存意義的缺失以及人際關系的疏離,把人們帶入到“本體的安全和存在性的焦慮”[10]。這樣的生存危機狀態中。經過對現代生活的審視和對自身靈魂的觀照,“家園感失落”成為大多數現代都市人的心理通病。“家”情結促使人們渴望通過到與“故土”有相似特征、有同源性地域文化的鄉村旅游場域中重溫傳統意義“家園”的體驗,再尋家園安頓的踏實感與回歸鄉土的親和感。某種意義上,游客的鄉村旅游需求是基于對現代性生存發展的理性訴求與對生命質態的感性體驗之間的沖突,而衍生的對現代性結構化生活的反抗與對個人原根性價值的彌合。從反思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角度審視,當較低層次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時,個人心靈方面的一些更高層次的需求也可能會占主導地位[12],而游客這一渴求回歸和體驗“家園”的“逆序需求”。本文認為,可解釋為在現代化社會環境中,理性層面上自我實現的需求與感性層面上社交需求和安全需求間的矛盾所引發的集體無意識的“需求失序”和“矛盾交織”。對此,只有通過生活場域的變換(鄉村旅游等),方可使人暫時從這種內在的心理紊亂中逃逸。
(二)游客家園感形成機制
勒溫提出在個體行為表征背后,存在著決定行為的內在動力——心理場(或稱為生活空間(life space),包括人和環境,即行為主體所處的整個主觀環境,也就是個體的心理經驗的總和[13]。在勒溫場論的基礎上并結合格式塔心理學,謝彥君等指出,旅游場作為旅游者行為反應的當下情境,是一個以地理環境(即旅游景觀的空間場域)為基礎的物理場和以心理環境(主觀心理情感)為基礎的心理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物場[14]。在這一語境下,作為一種符號,鄉村景觀(rural landscape)存儲著某一特定地域群體的共同文化和象征意義,其構成了解讀鄉土文化、意識形態、話語權力的充滿符號和象征意義的文本[15];傳統的鄉村是哺育生命、滋蘗文化、承載人類本源性生產生活的根性空間,隨著鄉村進入人們的審美視野,代表著鄉村詩意棲居的田園理想,鄉村意象成長為一種極具人性與溫情的家園性召喚結構[11],能夠激發游客前往鄉村參與相關旅游體驗活動的欲望,也能賦予鄉村以深層的旅游功能意義。例如,海口市龍鱗村作為海南鄉村旅游十大名村之一,除了原生的自然景觀和傳統習俗保護較為完整外,村民在長期聚集而居中形成的“民風淳樸、夜不閉戶、夜不拾遺、和睦互助”的鄉土情境保留至今,為有鄉愁懷舊情結的游客群體提供了空間體驗、情感互動的特殊場域。
由下圖1可知,在旅游活動開始之前,受“鄉土記憶”中傳統家園帶給游客的居家安全感、穩定感和溫暖感以及市場宣傳引導等主要因素的影響,游客初步形成了對個人情感期望中“家園感”的認知,這一長期積累的情感,成為游客做出鄉村旅游出游決策的根本性動機,驅使游客參與到鄉村旅游場域中的體驗活動。同時,由于旅游體驗作為一種主要由個體賦予其意義的主觀心理過程,對物理環境和心理環境都有著極大的依賴[16],游客經由鄉村氛圍情境和行為情境及旅游場的交互作用之后才能實際獲得“家園感”這一情感體驗。在與旅游場的空間互動過程中,通過與有形的鄉村景觀、村民生產生活實物以及其他物化層面上文化符號的身體接觸,游客最初的家園感便在此行為情境中得以自然流露,繼而通過互動,與這一物理場形成心理共鳴,達到物與我兩相忘,沉浸在“歸家”的真切和實有感里,形成對其所在鄉村旅游目的地“家園感”的認同。同時,游客對鄉村氛圍情境的體驗需求,可以在靜態的感知以及動態的主客交往過程中得以滿足。鄉村原真的鄉土氣息,村民自發營造的日常生活勞作的鄉土氛圍,讓游客的“家園感”在此種氛圍渲染中得以升華,之前日漸模糊、殘缺的“家園記憶”,會變得更清晰具體。同時,在自我建構的“家園感”所在的真實場景中,氛圍情境表征的熟悉感,會促發游客本能地與當地村民建立話語上的情感聯系,在“鄉音”中尋找“似曾相識”的親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除了感性層面上的鄉愁慰藉,游客還會通過主客互動,理性判斷自身的異化程度,來確認個人的本土感和本土性身份。如此,在與所處旅游場的互動中,通過感性的“家園感”實際體驗和理性地對自身生活的深刻反思,游客會形成對鄉村旅游場域實有鄉土價值的判斷,達成對“家園感”的心理認定,進而產生歸屬感和地方鄉土依戀。此外,對比最初的個人期望,通過具體的鄉村旅游情境體驗,游客會重構更符合自己心境的“家園感”。
(三)游客家園感的本質屬性
“游客家園感”的產生是個體在現代性結構化社會背景下,對自身生活現狀進行反思的產物。“家園感”本身具有的實在性、消費型和享受性[3]與鄉村游客追求本真性、真實性的愉悅體驗訴求相契合,鄉村本有的“家園感”能滿足游客對“家園”深度體驗的訴求。同時,在與鄉村旅游場的互動過程中,游客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形成鄉土自然相融、文化迷醉、情感流連的特有心境,賦予“家園感”以實有性、親和性、本土性、深沉性以及延續性的本質特征。此外,在與鄉土場域互動體驗之后,經過個人重構的“游客家園感”,從功能屬性上來看,又促使游客產生對鄉村的歸屬感和依賴感,從而建立游客自身對地方的忠誠度,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旅游目的地客源的持續輸入,為所對應的細分客源市場的穩定提供了保障。例如,通過對龍鱗村的實地調研訪談得知,來此旅居的游客在體驗“吃農家飯、住農家屋、看農家景、學農家活、享農家樂”等鄉村旅游活動時,其內在的家園感在主客日常互動過程中得以強化,逐漸建立與客房主人之間的深厚情誼及對龍鱗村的地方依戀,之后往往會以“探親訪友”的出游動機頻繁到此游玩。
四、結論
本文將“家園感”這一美學概念引入到旅游學研究中,結合海口市龍鱗村的案例情況,在鄉村旅游語境下,嘗試對“游客家園感”的形成背景、形成機制以及本質屬性做出理論解析,從而對“游客家園感”概念進行建構。本質上,游客家園感是一種在現代性結構化社會背景下,游客對自身生活現狀反思的情感產物和心理訴求,并通過與鄉村旅游情境的互動體驗,衍變出的具有實有性、親和性、本土性、深沉性以及延續性的主觀感受。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進一步豐富“家園感”的概念內涵,并為實踐中的鄉村旅游產品創新、服務升級等提供借鑒依據。但現實中,游客社會異化感越強烈,其對旅游經歷中的“本真性”就越追求[12],游客自身不同的異化程度會導致其對鄉村情境旅游體驗訴求的差異,而不同鄉村旅游目的地的鄉土性強弱又決定著游客能否在鄉村氛圍情境和行為情境中獲得“家園感”。僅將渴求回歸和深度體驗“家園”的游客置于龍鱗村這一特殊的鄉村旅游場域來探討“游客家園感”的內涵及形成機理,是本研究可能存在的一個不足。游客自身異化程度、旅游場域鄉土性強度差異,對“游客家園感”情感建構的影響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陳望衡.環境美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 陳望衡.環境美學的當代使命[J].學術月刊,2010,(7).
[3] 王琳.也談環境美的根本性質——家園感[J].美與時代(下),2010,(12).
[4] 張檸.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M].上海:上海東方出版社,2005.
[5] 程磊.羈旅山水與家園體驗——論羈旅行役詩中家園感呈現的意象形態研究之一[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31(1).
[6] 明慶忠,劉宏芳.鄉村旅游:美麗家園的重塑與再造[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8(4).
[7] 劉玲,舒伯陽,王朝舉.鄉土情結對旅游情感動機的驅動機制研究[J].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6).
[8] 黃潔.從“鄉土情結”角度談鄉村旅游開發[J].思想戰線,2003,(5).
[9] 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M].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熊劍峰,王峰,明慶忠.懷舊旅游解析[J].旅游科學,2012,26(5).
[11] 陶玉霞.鄉村旅游需求機制與訴求異化實證研究[J].旅游學刊,2015,30(7).
[12] 王寧,劉丹萍,馬凌,等.旅游社會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13] 章士榮.心理學哲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14] 謝彥君,徐英.旅游場中的互動儀式:旅游體驗情感能量的動力學分析[J].旅游科學,2016,30(1).
[15] 董培海,李偉.旅游、現代性與懷舊——旅游社會學的理論探索[J].旅游學刊,2013,28(4).
[16] 謝彥君.旅游體驗的情境模型:旅游場[J].財經問題研究,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