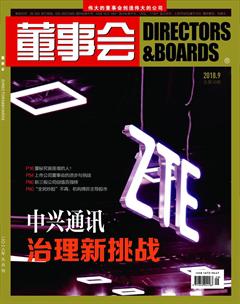聲音
創業如何成功?
哈佛商學院的一項研究發現,75%的創業公司最終倒閉,經營超過5年的不到50%。可能公司產品很出色但資金不夠,可能公司愿景很好但技術欠缺,也可能是公司戰略與規模存在問題。Surkus CEO Stephen George認為企業存續發展應該汲取四條經驗與教訓。
一是領導層愿景必須一致。領導層的任務是制定事關公司發展軌跡的決策,如果他們都不能統一意見,公司很難發展。公司的愿景可以在發展中改變,但領導層必須目標一致。
二是戰略性的建設團隊。要為達成目標不斷吸收新鮮血液,當需要調整公司結構時,必須在戰略計劃中設計這一步驟。
三是服務與技術息息相關。服務是解決用戶需求的產品,但技術是支撐這一產品的唯一要素。服務的擴展與對用戶的吸引都需要強大的技術基礎。
四是不要被眼界所限制。面向市場的產品與服務多樣化對于創業成功至關重要。
“買方壟斷”抑制工資上漲
一些大型巨頭企業的力量或許是當前工資不再上升的關鍵。失業率已經連續17年處于低位,公司利潤飛漲,可是美國勞動者們的工資卻沒有上升。排除通貨膨脹、平均支出增加等因素,幾乎是零增長。經濟學家們曾經對這一現象展開爭論并將其命名為“工資之謎”。
近期,在一場重要的全球性經濟政治會議上,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的觀點引起了關注:勞動者工資議價能力很低,因為每個行業都存在著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一小撮巨頭——這種少數企業的外部影響叫做“買方壟斷”。克魯格估算,這種影響每年削減了1%到1.5%的工資增幅。這看起來不多,但如果持續20年的1.5%增幅大概能讓工資漲1/3。由于勞動者們的可選擇雇主變少,他們的工資議價能力就會削弱。同時,隨著雇主企業數量減少,他們能夠更容易地達成“工資同盟”,無論是通過明確的幕后交易還是微妙的共識。
汽車的未來更像機器人
蔚來汽車(Nio U.S.)的CEO Padmasree Warrior表示,全社會正步入行業創新階段的“后應用時代”。Nio制造生產的已經不再是汽車,更像是一種看起來像汽車,實際上是一個搭載有大量傳感器、各式拍攝設備的機器人。這種機器人同時需要配備各種軟件,自主分析駕駛途中的障礙。
目前的汽車與未來的汽車已經存在根本區別:早期汽車工業時代的創新主要在機械方面,過去30余年則主要是電子、電氣系統,而到“汽車3.0”,數字化與軟件系統將成為汽車革新的方向。
隨著AI在自動駕駛汽車中的應用,汽車能主動預測用戶喜好并自行前往目的地。同時AI還能提供自主監控與維護功能,定時檢查剎車系統與輪胎狀態。汽車將成為一種服務的載體而非僅僅是一件沒有生命產品,它以后甚至能為用戶提供送貨上門的服務。
企業數字化轉型陣痛五大病因
為什么企業在面臨數字化轉型時表現有好有壞?在基于數據制定決策、推動探索以及積極開展試驗方面,只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能較為高效地建立數字化文化。Capgemini Consulting高級副總裁Didier Bonnet認為,究其原因大致有五個。
首先是預期不切實際。部分企業可能在轉型過程中盲目樂觀,難以真正適應技術領域的百花齊放。決策群起初更多對技術而非企業轉型更感興趣,但現實表明二者至少同樣重要。
其次是人才鴻溝。企業在人才與能力方面的差距,因為轉型可能會進一步拉大。
再者是溝通不暢。領導團隊與技術團隊之間存在孤島效應,二者需要有效的溝通和交流。
此外是數字文化欠缺。員工多數不愿意參與到數字計劃中,他們很難將在數字化轉型中所做出的努力轉化為對前端產品的有意義嘗試。
最后是競爭壓力提高。用戶對數字化的期望持續提高,新的標準與要求對企業造成巨大壓力。
Didier Bonnet認為,技術的進步遠早于組織轉型,如果放任這種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可能嚴重阻礙企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