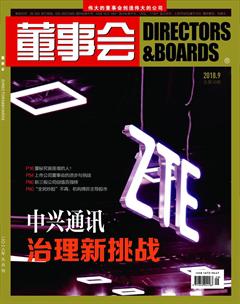長生生物警示中國公司治理
馬連福 秦鶴
依賴經營者的個人權威、社會關系所形成的粗放的治理體系,雖然使現在的經營活動如臂使指,但其產生的負面效應在未來的發展中終將難以控制。因此,企業必須“兩手共抓”,即一手抓經營管理,一手抓公司治理
2018年7月15日,國家藥監局發布長生生物的全資子公司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記錄造假的通告;18日,長春長生因生產的疫苗檢驗結果“效價測定”項不符合規定,被罰沒344余萬元;24日,長生生物董事長高俊芳等15名涉案人員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拘。8月6日,國務院調查組公布,長春長生從2014年4月起,在生產狂犬病疫苗過程中嚴重違反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和國家藥品標準的有關規定,其有的批次混入過期原液、不如實填寫日期和批號、部分批次向后標示生產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8月16日召開會議,聽取關于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調查及有關問責情況的匯報。會議強調,疫苗關系人民群眾健康,關系公共衛生安全和國家安全;這起問題疫苗案件是一起疫苗生產者逐利枉法、違反國家藥品標準和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編造虛假生產檢驗記錄、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失職失察、個別工作人員瀆職的嚴重違規違法生產疫苗的重大案件,情節嚴重,性質惡劣,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長生生物作為背負重要企業社會責任、涉及社會公眾生命安全的生物企業,借殼上市不過三年,緣何驚爆“黑天鵝”?在國企改革和后續經營中漠視公司治理風險、進而形成治理失控,是長生生物爆發丑聞的重要原因。
監督不力,變身家族控股
2001年,長春長生的前身長生實業的第一大股東長春高新,將長生實業20.68%的股份轉讓給長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簡稱“長生所”)。1個月后,長生所將其持有的長生實業30%的股份以1932萬元轉讓于韓剛君。至此,長生實業第一次出現個人持股,且韓剛君成為第二大股東。
2003年,長春高新拒絕福爾生物3元/股的報價,擬以2.4元/股的價格向長春長生董事長兼總經理高俊芳轉讓長春長生34.68%的股權。由于“高價不賣低價賣”,且高俊芳彼時身兼長春高新副董事長,輿論對這次轉讓涉嫌自買自賣、低價侵吞國有資產的質疑不絕于耳。雖然備受爭議,高俊芳在“按照有關規定回避表決”后,最終于2004年4月以2.7元每股,斥資3375萬元獲得長春長生25%的股權。至此,韓剛君、高俊芳分列長春長生第一、第二大股東。在此次股權轉讓中,長春高新的內部監督力量反應平淡,兩名獨立董事出具了“本次交易公平、合理”的意見。
2007年,韓剛君將所持有的長春長生30%的股份轉讓于深圳豪言,后者由高俊芳、張帥實際控制。2008年,21位自然人分持了原本持股數排名第三至第五名合計42.93%的股份,2010年進行了眼花繚亂、幾無收益的倒手,深圳豪言將30%的股份無償轉讓給高俊芳、張洺豪母子后隨即注銷:至此,長春長生成為家族控股,2015年借殼上市。
高俊芳等內部人通過“合法”的方式低價取得國家優良資產的背后,根源在于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所有者缺位問題。國企真正所有者的分散和缺位滋生了監督的“搭便車”問題:監督供給不足、不力, 監督力量在履行監督職能、保護股東利益時存在立場模糊的情況。所有者缺位致使長春長生在股權轉讓的過程中監督機制流于形式、監督主體權責不清、監督效果令人失望。
治理失控,企業風險激增
長生生物的實際經營存在極大的內控風險。內部董事比例較高。董事會缺乏必要獨立性,難以對管理層形成有效監督。高俊芳兼任董事長、總經理和財務總監三職,權力極大。作為董事長,高俊芳兼任財務總監在法律中雖無明文規定禁止,但對上市公司而言,兼任顯然難以保證公司治理結構、信息披露和財務內控機制的有效運作;作為總經理,高俊芳在近年來大幅降低研發費用、公司研發支出遠低于行業龍頭企業平均水平的同時,通過激增至人均2300余萬元的銷售費用變相鼓勵商業賄賂行為,致使法律訴訟成為長生生物訴訟信息中的突出部分,運營風險大幅提升;作為財務總監,高俊芳將長生生物大量資金投資于銀行理財產品,流動資金沒有有效利用。以上決策實例,令人質疑高俊芳兼任數職的勤勉程度和合理性。
長生生物種種異于常理,體現的是內部人控制。高俊芳自1994年擔任長生實業總經理,至2018年的24年一直位居“一把手”,并接連引入丈夫、兒子及其他親屬進入公司擔任董事、高管等職務,最為明顯的是高俊芳之夫張友奎、之子張洺豪。張友奎從長生所人事處離職進入公司任副總經理,主要負責銷售工作,2016年后不再擔任董事;張洺豪在長生生物任副董事長、副總經理,負責工程項目。資料顯示高、張二人的親眷也在長生生物中擔任職位,如張友奎之妹張敏擔任董事,張友奎與高俊芳的外甥女楊曼麗擔任長春長生市場銷售部經理。
另外,高俊芳在長生所工作時期的許多同事,長期在長生生物任重要職位。疫苗事件爆發后,張洺豪接受采訪時稱自己對長生生物的經營并不了解,并直指長生生物董事、副總經理、質量總監張晶對疫苗事件負有責任,而后者在1996年前一直擔任長生所職員。如張晶一般活躍在長生生物的“長生所同事”還有數人,分布在長春長生的董事、監事、高管之中。如在2008年至2014年任職長春長生董事的張嘉銘,在2000年退休前任長生所所長;現任長春長生監事的李鳳芝,曾任長生所建筑服務公司黨支部書記;現任長春長生副總經理、研究所所長的鞠長軍曾任長生所職員。可見,自1992年國企改制開始,參與改制并分享利益的長生所員工是“高氏家族”背后的另一重要內部人力量。
此外,據年報顯示,高俊芳在2000年、2001年的年薪分別為5.98萬元、8.4萬元,其2004年何來3375萬元巨資收購長春長生25%的股權迄今為止并無透明、準確的信息披露。高俊芳在回應媒體時稱收購資金是找“親戚朋友”借的,“自己出200萬”,“到期如果還不上的話,就自動轉讓股權”。未被信息披露的內部人復雜社會關系也最終成為長生生物公司治理失控、風險激增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長生生物的公司治理風險隨著內部管理人員權力的累積而不斷增加,最終嬗變為一場引發全社會關注的輿論風暴。239億市值的長生生物在短短十數年“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巨大警示
2018年7月26日起,“長生生物”股票簡稱變更為“ST長生”。7月27日,證監會發布《關于修改〈關于改革完善并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見〉的決定》,指出,上市公司構成欺詐發行、重大信息披露違法或者其他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全、生產安全和公眾健康安全等領域的重大違法行為的,證券交易所應當嚴格依法作出暫停、終止公司股票上市;對有關重大違法公司,特別是嚴重危害市場秩序,嚴重侵害群眾利益,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堅決依法實施強制退市。據此,長生生物將面臨被強制退市和股東訴訟的巨大風險。長生生物案例,給中國的公司治理帶來巨大警示。
一是及時優化公司治理,遏制粗放式生長。在企業初創期,大量企業依賴經營者及其團隊的熟人網絡與社會關系,迎合時代特殊需求,快速實現了業務增長和資本積累。然而,經營者也應意識到,依賴經營者的個人權威、社會關系所形成的粗放的治理體系,雖然使現在的經營活動如臂使指,但其產生的負面效應在未來的發展中終將難以控制。因此,企業必須“兩手共抓”,即一手抓經營管理,一手抓公司治理。其中,不斷優化公司治理機制,建立公司治理風險和預警防范體系,將束之高閣的內部監管力量解綁,是公司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是加強信息披露管理,重視利益相關者權益。長生生物案例顯示,不透明的信息披露、不公開的公司決策是滋生公司內部人道德風險乃至法律風險,最終導致公司治理失效的背景之一。因此,公司應首先制定更為規范嚴格的信息公開和披露制度,保證信息披露的及時、準確和完整。同時,加強自愿性信息披露,方便廣大投資者、媒體公眾進行常態化監督,直面社會質疑,將危機的種子鏟除在萌芽階段。
三是強化外部監管力量,防范“一放就亂”。公司治理風險表象的根本原因是改制中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難以撼動內部人在公司盤根錯節的權力體系。長生生物2004年私有化以來,幾次股權轉讓均游走于公司治理風險的紅線。盡管公眾的質疑形成一定壓力,但是直至本次疫苗事件案發前,長生生物并未就治理機制問題做出過整改措施。這進一步凸顯僅僅依靠市場的監督機制,并不能保證負有重要社會責任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服從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需要。因此,對于涉及提供人民基本健康需求產品的企業,有關監管部門要放下“一管就死”的憂慮,合理強化監管,適時針對內控問題突出、公司治理薄弱的公司進行重點管理和穿透性監督。
四是完善國企監督改革體系,避免重蹈覆轍。在長生生物的改革過程中,體現了內部人控制是國有企業資產流失的一大內因,股權轉讓是國企改革中的“事故高發區”。國企所具有的獨特社會責任,決定國企監督機制建設需要考慮社會價值的最大公約數。企業應通過恰當的制度安排整合現有多元監督體系,形成國企監督共同體,緩解所有者缺位問題。在實際監督中,不僅關注財務與市場指標層面,也要關注與高層管理者利益相關的行為指標。由此在新一輪混改中懲前毖后,避免錯誤的再次出現。
長生疫苗事件為企業、社會帶來深刻影響的同時,反映出一些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低下、風險不小。公司經營者應該意識到,構建完備的公司治理體系、及時應對公司治理風險不僅是制度的要求,也是企業弄潮商海、基業長青、個人優秀的保障:這將對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帶來積極影響。
作者供職于南開大學商學院/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
獲得71772094,18JJD630002項目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