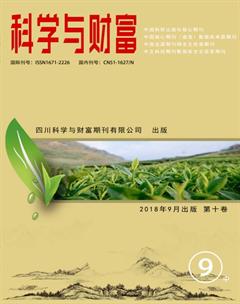市場經濟下人口流動對城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影響
畢文章
摘要:在我國多民族居住的城市,依然存在部分民族居住較為聚居的情況。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下,在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各族人民或快或慢的地理空間流動和社會流動持續發生,各民族聚居的格局會逐漸打破,各民族混居的情況逐漸增加。屆時,以階層分化為主要的居住格局形成,民族居住隔離的狀況將會逐漸打破。
導言:
我國城市中,多民族居住的狀況主要存在于邊疆多民族聚居區。新疆,西藏,內蒙等地所在的城市尤為典型。但是歷史上形成的居住格局主要還是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況。在當前新的歷史格局下,尤其是邊疆地區存在少數分裂主義的思想和活動。追根溯源,這與各民族之間缺乏相互交往交流有關系,而欲達成這種目標,需要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中盡可能形成一種雜劇的形式。也就是創造一種多民族混居的居住形式,使得一個小區內有各個不同民族的群體居住,左鄰右舍是各個民族的存在,從而創造出一個各民族便于交流的條件。這種客觀條件的建立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基礎,雖然依然存在語言交流的問題,但這都可以逐漸克服。這幾年中央政府也提到過建立多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這種提出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對于新疆的調研和考察也印證了以上的理論和政策。
一、城市空間居住格局的形成主導力量是市場
我國城市居住空間格局的形成演化是市場、政府、社會等多種因素對歷史因素和自然背景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市場經濟下,市場因素是其發展演化的基本力量,政府因素則是其主要的干預力量。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基于供需關系的價格決定了資源的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社區的建設主體從政府轉變為房地產開發企業,需求主體從單位轉變為居民個體,土地的級差效應、住房市場的價格機制和供求關系等都開始主導居住空間的演化,家庭經濟收入差異逐漸導致居住空間的分異(劉學良,2010:37)。
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分化必然引發社會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的轉變。前者是同質性社會,以強烈的集體意識為紐帶;后者是異質性社會,以社會分工形成人們的相互依賴。社會結構是社會團結的基礎,特定的社會結構形態與社會團結模式之問存在對應關系,社會團結的構建必須從社會結構的塑造開始(涂爾干,2000)。涂爾干將社會團結分為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前者是同質性社會,以強烈的集體意識為紐帶;后者是異質性社會,以社會分工形成人們的相互依賴。
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居住格局取代傳統民族聚居
據此,包亞明(2015)將我國民族民族團結分為機械民族團結和有機民族團結。他不贊同我國有人堅持的機械民族團結的老思路,這些思路認為為了民族團結,就應該讓同一民族的在一起。他認為在多民族國家里,各民族的異質性使得相互之間有天然的區隔,需要有意識地建構有機民族團結的共同基礎。互嵌式社區的建立就是通過結構重組推進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從而培養成一種相互依賴的社會結構類型。如果缺乏合理的多民族社會結構,可能導致民族認同對國家認同的挑戰,前蘇聯就是前車之鑒。
在這樣的有機民族團結的社會里,民族身份可能不是人們考慮交往及居住的重點。在如今社會流動的時代,也沒有那個民族能夠持續地長久地在一起了,他們四處流動,尋找更好的發展空間。以職業、興趣愛好、教育程度、品味等區隔為基礎的共同點代替了民族或者某種先天的身份而成為了人們凝聚在一起的新式的有機團結的紐帶。
由此,選擇社區居住可以有很多標準,如樓房的價格;環境的綠化程度;空氣質量;物業管理水平;上班的遠近;交通是否便利;居民素質等等。這個時候,不需要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哪個民族做鄰居都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了。
芝加哥學派或人類生態學的觀點:族群居住隔離是群體間社會地位差異的一個方面,他將隨著社會流動而趨于消失。當移民群體抵達美國一個城市后,他們傾向于住在與其他族群相對隔離的地段內,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移民社區開始在居住上分散開來。(阿維利,2010:269)
而且這種分散有規律性。一般來說,較之社會地位較低的族群,較高低位的族群一般居住更為分散。(阿維利,2010:270)人們更愿意選擇與自己所在族群社會地位相似的族群做鄰居,而不見的考慮單個個體的社會地位。(阿維利,2010:272-273)
三、新疆民族居住格局的未來
馬戎(2012:91-92)研究了1982-2005年新疆維吾爾族和漢族在全疆各地的流動,發現維吾爾族集中的和田、喀什、阿克蘇、吐魯番四地維吾爾總人口下降,漢族在烏魯木齊、石河子、昌吉等地人口減少,說明兩個民族出現了“均衡化”的地理分布,表明原來相對封閉的農村社區年輕人開始在外尋找新的學習和就業機會,這對于族際交往有積極意義。
歷史也說明了這種趨勢。舉例說明,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和漢族的居住格局民國時期就已經基本定型,維吾爾大多居住在二道橋等城南之地,漢族則在城內。宗教信仰、經濟貿易的內部性,政府政策等共同形成了這種格局。改革開放以后,人口流動增加,民族社區封閉性被打破,維吾爾人比例下降(劉正江,2012)。
而且,不同民族居住格局也會呈現變動狀態。烏魯木齊天山區漢族與維、回、哈族之間存在隔離現象,北部漢族人口集聚區分異度大于南部少數民族集聚區,但演變趨勢為北部趨緩,南部加劇(李松,張凌云,2012)。
從本人在新疆的觀察看來,新疆無論南北疆的城市,都形成了新區和老區。老區的民族聚居情況比較嚴重,而新區民族混居情況較多。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形勢下,老區的民族聚居情況逐漸發生變化,多民族混居情況有所增加。另外,在政府的老城改造項目下,政府也在積極推動混合的居住模式,從而為老城的多民族混居提供了外部支持。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以來,政府的作為在為新疆的多民族混居提供了較好的條件,比如建設高速公路,鐵路,等等。這樣內地人就可以較為便捷地來到新疆開展各種經濟活動。另外,政府對于新疆安全的保障也促進了內地人到新疆的移民。可以預測,這些方面使得新疆的各個民族的混居格局在逐漸地形成,即使存在某些個別的小聚居,但也不會是廣泛的存在。這一切,為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條件。
結論:
總而言之,不論是什么民族,只要在一定的環境下,主要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為了追逐自我的利益,必然會產生各種形式的人口流動。現在人們已經形成了共識:無論身在何處,只要有一個謀生的工作,在哪里定居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說,安身立命最重要,身居何處無所謂。從而,和誰做鄰居也是不重要的事情了。基于此,各個民族在市場的驅使下,在其無形的手推動下,會逐漸形成混居的狀態。各民族的個體或家庭,選擇居所不是看本民族的人多不多,而是考慮是否安全,是否適合自己的收入,身份地位等等。所以,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給各民族提供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氛圍。
參考文獻:
[1]劉學良,2010,歐美混合居住的效應研究及對我國的啟示,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埃米爾·涂爾干,2000,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2頁。
[3]包亞明,2015,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報,7月11日。
[4]阿維利,2010,居住中的族群隔離:變遷的模式;馬戎,西方民族社會學經典讀本——種族與族群關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馬戎,2012,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發展與族際交往,第91-92頁。
[6]劉正江,2012,清至民國時期烏魯木齊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年第2期。
[7]李松,張凌云,2012,民族混居區居住格局演化與分異研究——以烏魯木齊市天山區為例,社會學,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