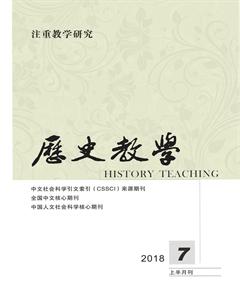絲綢與“絲綢之路”
關鍵詞 絲綢之路,絲綢,考古,中外交流
中圖分類號 G6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0457-6241(2018)13-0009-04
漢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繼位,兩年后即公元前139年派張騫出使西域,可見漢帝國的頭等大事是解除匈奴的威脅。如果上一節以“領略大漢雄風”為主題,本節課接敘張騫的鑿空之旅,學生很快就能進入歷史情境。張騫出使西域只是第一次將中原與天山南北地區連為一體,今天所說的經過中亞通往歐洲的“絲綢之路”,大約在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的50多年后才逐步形成。公元前60年,漢宣帝在位時設置西域都護,從此時起,通往中亞的兩條道路貫通。東漢的班超任西域都護30年,據《后漢書·西域傳》記載,這時“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也就是說,徹底戰勝匈奴,完全控制西域后商路才得以興盛。
漢代運往西方的商品沒有瓷器,主要是蠶絲、絲織品、漆器和鐵器。那么,這節課就必須介紹絲綢。
一、將絲綢與“絲綢之路”放在一節課
在內容標準中,應該將絲綢與“絲綢之路”合并為一個內容要點。絲綢曾經是中國在世界上的物質代表,是中國古代文明發達的標志之一,同四大發明一樣重要。成人通史習慣于在手工業的發展中介紹絲綢,初中課程不必分門別類。瓷器也是古代中國的物質代表,但瓷器開始熱銷海外是在唐宋。尤其是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活躍,中國瓷器大量出口,在這個點上再說瓷器。這樣設計既合理又節省課時,適合兒童學習。
制定課程標準應當借鑒外國成功的經驗。美國的國家歷史課程標準是比較成功的,似乎它在1994年頒布以來還沒有廢除或修訂。它的教育理念是先進的,我們基本已經套用過來。它的歷史思維能力目標體系梯度明顯、分解明晰,而我們還缺乏研究。它的內容標準采用“由近及遠”的原則,低幼年級從家庭、社區的歷史開始學習,然后再了解學生所在州或地區的歷史,再進入殖民地時期,了解有關那段歷史的紀念日、建筑物、雕塑,等等;而且還設計了多個主題和多種模式,供教師選擇。它對美國國家歷史的每個階段設計了不同層次的標準,整合了政治史、制度史和社會史,從能力目標的角度提出學習要求,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而我們的內容標準還缺乏中學歷史課程的個性,內容標準沒有層次,也缺乏研究。美國的歷史很短,歷史課程可以不慌不忙地帶領學生進入國家歷史。我們的歷史太長,初中課程要用兩個學年時間學完中國歷史,要學的內容多而學習的時間少。因此,建立適合兒童學習的歷史課程體系,是一項很難的工作。
二、絲綢與“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
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詞,現在也看不到兩千多年前的“路”。那么,絲綢之路從何說起?又是怎樣確認這條路線曾經存在呢?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又稱“河間”)及印度的絲綢貿易路線,稱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將其譯成“Silk Road”,中文譯為“絲路”“絲綢之路”。這是第一次出現“絲綢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國學者阿爾巴特·赫爾曼(A. Herrmann)在《中國和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又作了進一步闡述,并將絲綢之路延伸至敘利亞。老外起的名字我們在100年后才普遍使用,此前只有齊思和與郭沫若的著作中使用了“絲路”的名稱。1978年的中學歷史教學大綱第一次出現“絲綢之路”,而這年英國出版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已經有了絲綢之路的地圖,并附有絲綢之路的解說詞。
西方學者為什么將橫貫歐亞大陸古商路,取名為絲綢之路呢?因為西方最早通過絲綢才知道東方有個“絲國”,在他們的文獻中稱中國稱為“賽里斯國”(Seres,拉丁語),稱中國人認為“賽里斯人”。他們沒有記載絲綢是怎樣出現在歐洲市場的,他們沒見過蠶,不知道絲是怎樣產生的。他們那兒有蜘蛛,于是他們想象,蠶像蜘蛛一樣也是有爪的甲蟲,能吐絲。有位叫馬賽里奴斯的希臘人,他筆下的中國是:四周環山,其中平原,氣候溫和,森林甚多,林中有毛,梳理出之,成精細絲線,半似羊毛纖維,半似膠質之絲,將此纖維紡織成絲,可以制衣。①在古代世界,只有我們的祖先掌握了養蠶和絲綢生產技術。蠶絲是由絲纖維和絲膠構成的,其中絲纖維占70%以上,絲膠占25%左右。沒有去除絲膠的叫“生絲”,用沸水或堿性溶液除去絲膠的叫“熟絲”。絲纖維的長度可達800至1000米,而且韌性大、彈性好。蠶絲的細度、長度、韌性和彈性主要取決于養蠶技術,如飼料的選擇和加工,細致的呵護。因為出了蠶蛾的破繭和殘絲需要紡拈成紗,而紡拈不能保證絲的均勻,絲線的光澤、韌性、彈性也很差,因此保持繭子不出蠶蛾是養蠶的關鍵。考古學家夏鼐認為,我國在殷商時代產生了養蠶和絲織技術,有出土文物為證,甲骨文中也有絲字。他認為,說新石器時代已出現養蠶業的根據不足。西周至春秋時代,養蠶成為普遍的家庭副業。《詩經》《尚書》等文獻都記述了蠶、桑、蠶絲和絲織品。戰國時期的絲綢物已有羅、綺、錦、繡等不同技術的產品,“錦繡”一詞在那時已經出現并常常連用,成為美麗的象征。漢代絲綢織物更加豐富多彩,著名的“素紗禪衣”,據說現代技術還無法復制。唐代絲織品的產量和品種更多,上層社會普遍穿著絲綢衣料。漢唐的強盛及其開放政策是絲綢之路繁榮的必要條件。
古代的絲綢之路不可能保留至今。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聯合西域各國共同夾擊匈奴,《漢書》只記了他的行跡和西域的一些古國,并未記載商貿,也沒有確切描述商路。古代歐洲人、中亞人知道絲綢和中國,至于絲綢之路,他們也沒有記錄。對這條古代國際商路的確認是近代的事,主要依靠考古發現。考古發掘了一個又一個“點”,將這些“點”連接起來,絲綢之路的幾條“線”路清晰地呈現出來。考古學是西方近代產生的新學科,考古首先確認的點是樓蘭古國。20世紀初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首次發現樓蘭,而后,美、英、日本及我國學者接踵而來。樓蘭遺址的發現印證了《史記》《漢書》有關樓蘭的記載。張騫出使西域路經樓蘭,在漢、唐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樓蘭成為中西貿易的中轉站、交易市場和交通樞紐。樓蘭的發現是一個“點”,后來在新疆的且末、于田、和田、葉城、喀什,考古陸續發現的“點”,連接了絲綢之路的南線;在庫爾勒、輪臺、庫車、拜城、阿克蘇,考古陸續發現的“點”,連接了絲綢之路的中線;在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伊寧,考古陸續發現的“點”,連接了絲綢之路的北線。在中亞地區也發現了許多“點”,連接了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外的線路。
考古不僅證明了絲綢之路,而且還印證了漢唐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有效管轄,及漢文化在西域的廣泛影響。新疆發現的漢、唐的城址很多,城址既是國家政治的平臺,也是連接絲路保證商旅安全的設施。如在輪臺縣發現西漢時期的西域都護府城址,車庫縣發現唐朝安西都護府城址,高昌故城則是幾代王朝的治所。這些城址很多是按內地形制建造的。在昌吉州發現的北庭故城,分內外城,略呈長方形;早期的樓蘭古城受中亞影響是圓形城,后來受內地影響,城為方形。烽燧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遺產,由敦煌至庫爾勒沿線筑有漢代烽燧,是保護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在城址及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漢字文書、漢文官印。如在樓蘭遺址發現了大量漢文簡牘、魏晉木簡文書;在且末縣漢晉時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漢文紙文書;在昌吉州吉木薩爾縣的古城規中出土了唐代銅質官印“蒲類州之印”;在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司禾府印”等。在新疆的漢唐遺址與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漢文典籍。如羅布泊西漢烽燧遺址中出土的《論語·公冶長》篇簡,羅布泊海頭遺址發現《戰國策》殘卷,尼雅遺址發現《倉頡篇》殘文。此外還出土有《毛詩》《鄭玄注論語》《孝經》《唐律疏義》《針經》等古籍抄本。在貴族墓葬中發現很多織錦上有漢字。如尼雅遺址墓地發現的漢晉時期織錦上有“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大明光”“安樂如意長壽無極”“萬世如意”“世毋極錦”“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等文字;在羅布泊地區孤臺墓地發現織錦殘片上有“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明光”“望四海貴富壽為國慶”等文字。絲綢是漢王朝饋贈他們的重要禮品,他們生前享用,死后隨葬。①
考古在城址及墓葬中發現了很多中外古錢幣,漢唐的錢幣最多,還有中亞波斯薩珊王朝、貴霜帝國的錢幣。但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出土的駱駝俑,牽駱駝、坐駱駝的人,均為胡發卷曲的“胡人”,沒有發現一例漢人牽駝俑,在西安、洛陽和寧夏的固原等地還發現了不少粟特人的墓葬。這說明來往于絲綢之路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不是漢人。粟特是古地區名稱,位置在今伊朗、阿富汗北部,現屬于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境內,是與我國新疆同緯度的地區。粟特人有自己的語言文字,他們是中國與歐洲商貿的中間商。張騫出使西域到達的大宛國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西部的費爾干盆地,距長安已有一萬兩千里,再到地中海西岸,這中間有一長段荒涼的山地和沙漠邊緣地帶,可以想象,粟特人也是蠻辛苦的。因此往來于絲綢之路,近處一次要兩三年,遠處要八九年,一年至多十余批,少時五六批。一批多則數百人,少則百余人。②由此可以判斷,運到歐洲的絲綢價格必然昂貴,而且數量有限。
通過絲綢之路,內地的鑄鐵和鑿井技術傳到西域,現在新疆的坎兒井就是絲綢之路開通后出現的。經過這條路中國的絲織品、漆器、鐵器、玉器外傳,從西方傳入的有西瓜、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豆以及胡琴、良馬,等等。東漢蔡倫發明的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出現在西域、波斯等地。印度的佛教也借助這條通道傳入我國的中原地區。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合西域各國共同夾擊匈奴,西域地區的酋長們也渴望擺脫匈奴的統治,建立軍事聯盟是雙方的需求。以政治目的開啟的這條通道,后來卻以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而聞名于世。也就是說,當年的商貿和文化交流只是這條路的“副產品”。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證明西漢王朝開辟絲綢之路的目的不是為了貿易。但是,打通中國與西方的通道開啟了歐亞商貿與文化的聯系,使歐洲人開始了解中國,也使中國人開闊了眼界。
三、對教學效果的估計
初中歷史課程應該具有適合兒童的特點。從絲綢之路談及絲綢和養蠶業,展現古代中國的物質文明及其對西方的影響,比那些說我們比歐洲早多少多少年更生動、更有說服力。民族自信心應該通過歷史細節自然而然地形成,不需要說教。絲綢之路興盛之時,往往是在中原王朝穩定、繁榮時期;中國處于盛世時代是絲綢之路暢通、繁忙的基礎。因為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強大不僅保障了商路的安全,而且可以提供豐富的商品;反之絲綢之路必然衰落。這個道理初中學生能懂。從考古角度認識絲綢之路,既滲透了重證據意識,同時從根本上了解了歷史書寫的由來。以前只講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條商路,不交代怎么知道的,讓學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假如化學課只告訴學生氧氣助燃而不做實驗,化學老師肯定說不行。學生的興趣也在于觀察到氧氣助燃的現象,才領會氧氣的特性。歷史也是同樣道理,教學不應停留在結論層面,從考古發現認知絲綢之路,然后再分析商路暢通的歷史條件,這是教學之道。考古發現不必詳細介紹,如果作業是讓學生通過網絡尋找考古證據,就更理想了。很多文章說美國教育的作業就是這種模式,需要學生去再發現,這樣的作業更費時費力,但學生有興趣去完成而不成為負擔。至于要求學生想象商旅的艱辛,先要弄清楚是什么人行走在絲綢之路上,感悟“胡人”行商辛苦,不是瞎操心嗎?
將絲綢與絲綢之路合并在一節課,“既經濟又實惠”,何樂而不為呢?
【作者簡介】老任,本刊顧問。
【責任編輯:李婷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