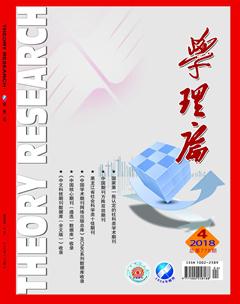“軟硬兼施”的權力運作——村干部的策略選擇
馬藝菊
摘 要:以太原市王村為案例研究地點,運用田野調查法和個案拓展法,針對在政府主導下的城中村拆遷改造的過程,分析了在城中村拆遷改造中,村干部為了順利完成征地任務,采取不同的策略性行為。展現了村干部與被拆遷村民的互動,雙方各自具有的策略空間,最終村干部以“軟硬兼施”的辦法完成拆遷任務,即以正式權力運用為主,非正式權力以及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用為輔,在適當的時候做出調整、妥協和讓步。
關鍵詞:城中村拆遷;村干部;權力運作;軟硬兼施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4-0082-03
中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中,城市在快速的發展,城市周邊大量的村莊被吞入城市,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城中村”。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特殊的地域現象,是在特定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政策背景下形成的非完全城市化的產物[1]。城中村的發展讓城市中的土地形成了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并存的局面,同時由于國家長期的二元社會制度結構帶來了城鄉征地成本存在巨大差異,與城市土地相比,農村土地特別是靠近城市地區的農村土地“價格低,地段好,收益高”,所以當面對解決土地供求壓力、落實城市發展用地問題時,政府的目光自然而然落到了城中村。于是以“推進城市化進程、盤活城中村存量土地資產和促進城中村村民的全面發展”為目的的拆遷改造工程轟轟烈烈地在城市展開。
而將過去的城郊農村并入城市版圖,這必然涉及征地拆遷。由于土地和房屋的不可移動性,加之征地拆遷涉及的事情繁雜、利益巨大,使得征地拆遷成了“天下第一難事”[2]。在農村地區進行征地拆遷過程中,村干部的行為能夠對這一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他們作為鄉村治理的直接實施者,貫徹落實政策的關鍵點,連接村民和政府的紐帶,如何順利完成城中村拆遷改造,維持村莊秩序,進行利益整合,對村干部群體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我國“鄉村政治”的研究中,費孝通在研究傳統鄉土中國的權力結構時,就區分了村莊中同意權力、橫暴權力和教化權力等三種基本的權力類型[3]。黃宗智以長江三角洲和華北農村為分析對象,提出了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態、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結構對于鄉村權力結構類型的影響[4]。新中國成立初期,村莊權力體現出較為鮮明的國家權力的邏輯。申端峰認為國家權力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深入村莊,構建起了村莊的“制度型權力”,對村民具有強大的支配能力[5]。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村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轉型時期,隨著國家權力從農村社會的部分撤退,村落社區自治權的迅速成長,造成了村莊層面上空前復雜的權力互動,造成了一系列權力關系的重新型塑。國家在農村的權力弱化,村組權力運轉的邏輯除了遵循國家的邏輯之外,還有各種地方性的邏輯,接近于杜贊奇所說的“權力的文化網絡”[6]。孫立平等人認為,在國家權力衰退的背景下,基層官員對正式權力之外的本土性資源的借用,強化了國家在農村的權力。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并不以權力的正式規則為基礎,而是借用民間社會中的本土性資源,比如,人情、面子、常理等[7]。
本文選擇山西省太原市王村作為案例研究地點,通過對王村城中村拆遷改造過程中村干部與政府、村民之間互動的分析,試圖探討的問題是:在以政府為主導的大力推進城中村征地拆遷改造的背景下,村莊權力的運行機制,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通過正式權力、非正式權力的運作,平衡安撫多方利益主體,維系發生劇烈變動的村莊秩序,在具體的互動中如何運用策略以達到拆遷改造的目標。
一、案例研究
本文案例研究地點是太原市王村,王村位于太原市區中西部,距離市區12.5公里。王村占地面積1 500畝,絕大部分土地為生態園山地、林地,全村總戶數126戶,人口507人,60歲以上老人48人。村中有王、張、郝三大姓。近年來,市政府推進城市化,在城鄉統籌過程中,以修建外環高速公路為契機,對高速公路規劃道區的城中村進行整村拆除改造。經區政府申請,市政府批準,王村被列入2013年城中村整體改造名錄。2013年5月,王村正式啟動城中村拆遷改造,歷時兩個月,完成整村拆除。之后進行招商引資,引進開發商入村建設,但由于多方因素影響,截至2016年底,王村尚未完成全部的村民回遷安置工作,安置樓建設正在進行中,計劃于2019年全部完成回遷。
在2016年間,筆者于王村城中村進行田野調查,對城中村拆遷改造工作進行了調研,收集了與王村有關的歷史人文資料,城中村改造相關文件等等一手資料,并與村干部以及村民進行了多次訪談,尤其對城中村拆遷過程進行了深度訪談,試圖理解城中村征地拆遷背后的邏輯。
二、“軟硬兼施”:正式權力與非正式權力的運行
村莊權力可以劃分為正式權力和非正式權力。正式權力是指存在于正式的政治組織當中、由法定的制度規范賦予并以法定方式實施和表現的政治權力;而非正式權力則主要是指非正式組織中,由非正式組織成員在法定的權力體制外賦予其領導人并在具體的行為過程中予以接受和服從的政治權力[8]。正式權力對應著各種正規政策、制度的施行,非正式權力則往往指正式權力和非正式權力主體運用本土社會的關系資源所實行的非制度化的行為策略與方式。本文中非正式權力是針對正式權力而言的,與正式權力的文本性、科層化、強制性不同,非正式權力更具策略性、靈活性、多元性。
在政府宣布列入城中村計劃后,宣傳動員拆遷工作正式開始,王村的村干部們開始了進行說服村民們的工作,就是通常所說的“做工作”,通過版面、標語、宣傳單、入戶宣講等形式向村民開展宣傳動員工作——即通過權力的正式行使宣講政策。一般村干部會在村民會議上給村民講拆遷改造的勢在必行,讓村民認識到城中村改造將會給村子帶來的機遇和發展,以及對拆遷補償改造方案進行講說和解釋,在村民們了解了基本的拆遷補償政策之后,村民對拆遷的態度開始分化,本文將城中村拆遷改造中村干部的策略分為了三個階段進行分析,分別是前期:團結響應者,中期:安撫觀望者,后期:解決“釘子戶”。本文試圖論述村干部是怎么樣通過權力的正式以及運用權力的非正式途徑完成任務,由“軟”及“硬”,軟硬兼施。
(一)前期,團結響應者:關系、人情、面子
村主任WZ以及村委改造組深知在拆遷開始村民們的“輿論”以及“風向”的重要性。如何通過團結響應支持者來“造勢”,讓村民們看到城中村拆遷改造是“大勢所趨”,不可抗拒的,從心理上瓦解他們試圖抵抗的防線,是村干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報名拆遷的初期,村民們大多人心惶惶,觀望者跟風者眾多。所以村干部要做到的便是極力溝通各方,團結“自己人”,了解和控制村內的輿論導向,穩定人心,保證在初期報名拆遷和簽訂協議的順利進行。
黨員和村民代表是村干部的首要團結對象,黨員和村民代表由于經常參加村里的相關會議,他們的身份比較重要,具有一定的表決權,而且和村委的關系較為熟悉,比較容易溝通,好說話,尤其是黨員身份的特殊性,村干部多會給他“曉以大義”,“你(身為)個黨員,怎么覺悟還不高了”,以帶頭表率、圍繞大局等話語來進行勸說,給他們施以一定的輿論壓力,會起到一定的效果。
其次能夠團結的人群,是村干部自身所在的家族,中國農村一直存在“熟人社會”這種特有的人際關系網絡,在王村,W姓為大姓,也就是村主任WZ身處的家族,具有一個關系緊密的網絡圈,WZ作為這個“家族”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村干部適時地運用“人情”“關系”,推動拆遷工作的完成。
最后要團結的人群,是在本次拆遷中能夠獲益的,或者利益沖突小的,如擁有大面積住宅的村民,通過拆遷能夠得到置換的房屋或者是一筆豐厚的賠償款,是響應拆遷的頭號人群。他們本身心思活絡,再加上村委適當地給予他們一些“做通工作”的金錢獎勵等,激勵他們幫助改造組做工作,對不愿意拆遷的村民進行軟化和勸說。對于這部分人群,除了納入城中村改造小組,有一定的“面子”之外,還有一些額外的待遇,是村委的得力幫手。
(二)中期,安撫觀望者:獎勵、幫忙、特殊照顧
城中村拆遷改造的觀望者,他們的心態矛盾又猶豫,他們的心結在于怕輕易拆了之后留下無窮的后遺癥,政府、村干部許諾的高樓大廈何時能夠建起呢?拆遷補償款的多少,能賠多少?能拿到多少?是大多數人關心的問題,還有部分村民在拆遷中有門面房的,利益受損,不愿拆遷,于是觀望者村民的策略是:別人不拆咱就不拆,誰知道早拆了是好是壞。
相對的,村干部采取的策略是“各個擊破”,采取多種“做工作”的方式。身處“熟人社會”,村干部對于村子里各家的情況十分清楚,也十分明白怎么樣“做工作”能夠“做通”。
首先是設置鼓勵政策,如在王村的拆遷政策中,對××日以前簽訂放棄協議的住戶,每戶可在享受原方案補償以外另獎勵十萬元。其中,十萬元的獎勵是面對所有的拆遷戶,但是面對一些“難說”的家庭,這條獎勵政策也有適當的放松,即便拆遷超過了所定的日期,但是只要最終拆了,這個獎勵也并不會取消。村民說到“在規定時間拆了給獎勵,拆不了就扣你,(筆者提問:扣多少?)就是那么一說,一般情況你超個十天八天也沒事,拆了的人都有。”
其次是幫忙解決實際困難,村主任WZ講述他去村民家里做工作,“有困難解決困難,看他怎么回事,該解決的解決,該打壓的打壓,該支持的支持,找個工作啊,活兒啊,能安排都安排了”。通常一些合乎情理的要求都能得以解決,如幫忙找一些難度不大的工作,解決不能及時安置等問題,王村的村委幫忙尋找臨時的安置過渡房,幫忙解決村民用于存放搬遷物品的庫房,對于一些家庭有行動不便的老人,也盡量優先安置。
還有一些村民,由于拆遷中利益受損,情緒較大,拆遷難以推進,村干部在做工作中盡量好話好說,也會適當地給予一些“特殊照顧”,如在說服過程中,答應拆遷戶若簽訂協議,便能給拆遷戶一年7000元額外的“生活補助費”。或者在別的方面做出一些妥協和讓步,以換取他的同意,如在測量房屋面積的時候,適當寬限一點,這樣的行為被干部稱為:懂得變通。當然這種“協商”僅限于當事人和村干部知情。
村干部或承諾或許愿或妥協,總之,拆了再說。通過多次的“做工作”:輪流上門,軟磨硬泡,反復承諾,打消顧慮,施以恩惠,隨著進行拆遷的村民越來越多,觀望的群眾態度也多有軟化,同意拆遷。
這樣,在拆遷工作的前期和中期,村干部通過先來“軟”的,利用本土性資源——“講好話”“拉關系”“給人情”,也就是面子、人情來說服和影響其他村民,采用收買、分享部分利益的策略來拉攏“盟友”,以此緩和自己與村民間的關系,通過非正式的途徑完成任務。正式權力的運作具有剛性的特征,村干部用強制手段容易激化干群之間的矛盾,現時的工作不好做,日后也難以相處,所以能夠運用這種非正式權力,村干部樂見其成。用孫立平的話說,“本土性資源并不總是抗衡國家的一種力量,它有時也可以被國家利用,作為強化國家權力的一種手段”。
(三)后期,弱者的反抗與解決“釘子戶”
“釘子戶”是我國拆遷過程中獨特的社會現象,是權利失衡的結果,屬于農民為爭取拆遷補償的社會抗拒事件,是廣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及鄉村治理中的問題[8]。
釘子戶與政府在力量上是不對等的,拆遷農民維護自身利益的“弱武器”也是有限的。
王村干部在經過與村民漫長的說服、談判、協商、“拉鋸戰”之后,仍有個別村民拒絕拆遷,一戶村民拒絕拆遷的理由是他的宅基地面積小,只有兩分地,但是他有兩個兒子,且都尚未結婚,在王村的風俗中,給未婚的兒子準備婚房是傳統,也是為人父母的責任,而賠償款顯然遠遠不夠解決兩個兒子的婚房問題,于是他提出了要以更高的價格進行賠償才同意拆遷,村干部拒絕了他的要求,雙方僵持不下。還有村民因為擁有地段較好的門面房,一年租金收入能有十來萬,這次拆遷損失不小,心理也充滿了不滿和抗拒。
這部分村民他們或許表面上“同意”拆遷,但實際上不配合拆遷的工作,如故意逃避,拒絕丈量,不配合工作,甚至采取過激行為,6月的一天早上,城中村改造小組的工作人員發現往常在告示欄張貼的王村城中村的拆遷補償方案、規定通知、樓座戶型效果圖等宣傳文件被撕毀。斯科特認為,當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村民們會進行反抗,農民秉持著追求“生存第一”的生存倫理,一旦他們的生存倫理或社會公正感遭遇威脅,他們將會采取行動進行反抗,并稱為“弱者的武器”[9],如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暗中破壞,拖延搬遷等日常抗爭形式。日常抗爭是被拆遷農民在政治結構限制下的有限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