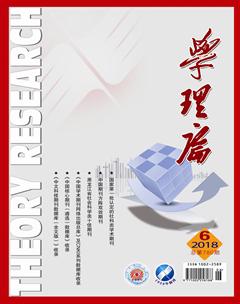探析布洛赫彌賽亞色彩的希望哲學思想
楊曉東
摘 要:布洛赫的希望原理的理論邏輯由彌賽亞主義的末世論、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等思想構成。布洛赫基于傳統猶太文化精神的研究,提出希望之鄉需要人的自我拯救,描繪了人類最終要到達的哲學世界的未來圖景。他的希望哲學從烏托邦哲學發展而來,卻摒棄了烏托邦中空想的成分。從希望哲學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變革關系;由人道主義的烏托邦、具體的烏托邦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來理解具體的希望是基于現實的客觀趨勢,面向未來的唯物主義是布洛赫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定位。
關鍵詞:希望的原理;彌賽亞文化精神;烏托邦精神;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6-0065-03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1885 - 1977)的著作跨越人類學、生理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等多學科研究領域。布洛赫認為在西方哲學史上都有烏托邦精神的痕跡:柏拉圖的理想國愿景是“輕浮和狂熱的抽象的烏托邦”,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建構是“空洞的愿望”,康德倡導的是自由意志的至善,當然這也是布洛赫所批判的,后來漢娜·阿倫特對于人的境況提出了生命至善的論述,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至善原則對于人的重要性。布洛赫提出的概念比較零散又頗具詩意,他的思想是基于烏托邦原型的至善原則,為了更透徹地理解文本,我們以至善原則和彌賽亞主義的烏托邦精神來源進行分析,再從希望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直接聯系等方面進行類比分析,進而來判定布洛赫希望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性質。
一、基于至善原則的希望哲學建構
布洛赫“烏托邦原型”的至善是對康德“自由意志”的至善進行了總體的揚棄,康德認為至善是幸福和德行的綜合體,意志自由產生于尋求幸福的人和遵循道德的人。自由意志至善是最高準則,人們不得不去追求它。“通過意志自由產生至善,這在道德上是先天必然的”,可以說布洛赫是位哲學家也是位感性的詩人,他不側重于經驗的實證知識,而是從內在原則汲取知識,倡導人們從感性世界中尋求自我滿足。《希望的原理》的內容豐富了康德至善原則,使其更加形象化或者說圖像化,唯一的區別是康德認為舍與得,行善與回報在現實世界不可能發生的,只有期待靈魂轉世來完成圓滿的至善。與其相比布洛赫是位立足于現實的唯物主義者,他認為生活中幸福的形態就是點滴的至善,“康德強調宗教的道德倫理功能,康德認為至善只有設想在彼岸世界實現,在現實世界是達不到的。“要想設想在彼岸世界里實現至善,我們不僅需要進一步設定意志自律即自由,而且必須進一步設想靈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希望神學的至善原則是康德理性范圍的宗教建構,同樣布洛赫提出具有烏托邦原型的至善也是出自康德這里,它具有幸福形態,“至善原理不是柏拉圖回憶說這種太古的,它是擁有最幸運驚訝的不變性內容,它的顯現近似的滿足其圖像即更美好生活夢的尖端。”而這并非可驗證的知識,而是做出一種理想的假設圖景。
從發展性質來看,一般認為布洛赫提出的希望哲學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未來是處在一種“尚未”的狀態中,認為人和世界是向前運動的、開放著的一種未完成過程,希望的基本原理是未來以無限多的可能性向人敞開,由此人便對未來(世界的未來和人自身的未來)產生各種“希望”。希望也就是文本中所描述的饑餓,它是人類種種激情中最富于人性的激情。因為現實的人總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充分的人性、真正的人性仍存在于前面,人要不斷地朝前。希望的法則對于人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它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本體論現象,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固有的人類需要。
二、彌賽亞主義的末世論
(一) 彌賽亞色彩下的烏托邦精神
1912年,布洛赫與盧卡奇在海德堡參加了馬克思·韋伯研討班,進行了“認識對象的烏托邦趨勢”的主題構思,這也是1918年《烏托邦的精神》前期雛形。根據《圣經》的說法,信仰、愿望的必要條件是對耶穌基督的信仰體驗。布洛赫沒有做過像《圣經》中關于信仰、愿望的表述。與傳統猶太的彌賽亞思想相比,布洛赫希望哲學更具有科學性和自然歷史性,更多是對革命實踐的因果聯系做了表述。比如布洛赫認為的“拯救”是理想化的自然世界以人為作用對象反饋的結果,當然充要條件是人要懷著“信、望、愛”之心面對自然和人。在此前提之下,希望之鄉就是人被“拯救”的境界。馬克思·韋伯和布洛赫的思想碰撞在于信仰、忍耐和期待對革命實踐起到動力助推的作用。“信仰雖然歸根結底是物質與精神的利益,而不是思想支配人們的行動,各種宗教所設計的理想社會或世界形象能夠像扳道工一樣,決定行為為利益動機推動而沿著他前進的軌道,決定人們希望將要從什么地方得救和為什么得救并且能夠得救這樣一些非常現實的問題。”那么拯救是改變不平等的、固化的存在方式,自我拯救是保持一種向善的動態運動。
(二)布洛赫對傳統猶太文化精神的升華
布洛赫不僅研習了哲學、物理、音樂還對希伯來神秘主義產生興趣,1907年他主要從事拉比宗教主義的研究,布洛赫的思想來源于猶太傳統的文化精神,傳統的文化精神有其自身的展望性和革命性,彌賽亞思想對歐洲現實起了補償和精神解脫,也構成了解放運動的動力因素。第一,彌賽亞即末日救贖者源于希伯來語“受膏者”(Mashiah)最早見于《利未記》“受膏的祭司”這樣任何被賦予神的使命者。“夾雜著烏托邦和災難性層面的重建內容。客觀上形象反映民族宗教衍化過程中現實歷史層面。末日救贖思想是復國重建民族主義層面,普世主義指向烏托邦層面,互為表里,相互依托。”第二,“回歸錫安”與彌賽亞思想。“回歸錫安”這一說法最初在公元6世紀即猶太人第一圣殿被毀約五十年后開始出現。“希伯來圣經記載索羅巴伯、以斯拉及尼希米帶領的民族整合性回歸渴望的錫安運動,并在猶太教中彌賽亞信仰及末日論思想得到宗教力量的詮釋性支持。”除了思想背景外更具有某種烏托邦性質,這也是古代早期環境下宗教在社會意義上文化整合功用的獨特表現。第三,喀巴拉(原意指傳統)與猶太彌賽亞主義。二者最初無直接關聯,二者結合于1492年西班牙大驅逐的陰影籠罩下 ,無論群體和個人命運都是災難性的未被救贖的存在,喀巴拉將其轉向現世和末世的時空范疇。“喀巴拉體系的三個范疇分別是上帝自身的一種自我放逐;拯救‘失落的神光而進行的不懈努力;神性統一不在創造開始的過去,而在修復完成后的末日。”拉比猶太主義在《摩西五經》之后還編撰了《密西那》《塔木德》,其目的在于借宗教行為和宗教組織來鞏固宗教信仰、宗教觀念、宗教情感。“耶和華的詩篇記載舊約第二次編纂是在公元5世紀初。耶和華的詩篇在希伯來原意是贊美詩,其實除了贊美之外還有泣訴、感謝、祈禱、教訓、喜怒哀樂各種情緒的表達,猶太教基本教義:圣潔祈禱十誡(法的形式和結構、法的內容、共同基本倫理的基礎)安息日、家庭、猶太婦女、外邦人”。按照猶太神秘主義的說法,救世主并非專程解救而是賜人以智慧,使人得以解放,思想主導向善,肉體主導向惡,人有需求和情緒的表達,那就應該刻苦禁欲,剔除惡因,才可以得到拯救。而按照布洛赫的說法:性沖動、死亡沖動對于人來講,這是自身的自我(Ich),布洛赫的倫理觀也是基于猶太教教義。布洛赫在批判弗洛伊德、阿德勒精神分析論指出“按照人的個別階級狀況和時代狀況,沖動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因此沖動也是按照人的意向,或作為沖動方向加以把握的”。 “作為世界以及人類的創造者,上帝讓他所創造的萬物都為各自的行為負責。上帝對人類的判刑絕不偏心絕不遺忘絕不勢力絕不受賄”,意思是人要有十誡教義的約束,人的行為要遵從戒律,不違背人的倫理和人性道德的基礎上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是泯滅人性的資本家和慘無人道的侵略者應當反思的。布洛赫從猶太經典和希臘理性主義出發,對希伯來精神進行展開,將彌賽亞思想歷程的探究和希望之鄉的假設分析,都必須服從于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身心解放這一核心。一戰時期西方世界文化危機,物化泛濫,布洛赫認為人類都應該尋求救贖,跟猶太傳統不同,布洛赫尋求的是人的自我拯救而不是神的拯救,旨在喚醒人的烏托邦沖動。布洛赫在這三種主要的傳統彌賽亞文化精神的影響之下,把握馬克思主義與拉比猶太主義的思想聯系,批判揚棄地汲取了文化精神中對理想社會的政治思想變革。共產主義思想和末世論下的信仰相比,“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是無神論,而無神論最初還遠不是共產主義:那種無神論毋寧說還是一種抽象。無神論的博愛最初還只是哲學的、抽象的博愛,而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是現實的和直接追求實效的。”布洛赫在彌賽亞思想的熏陶下也有強烈的猶太復國主義渴望,但他希望的復國是國際人道主義的,他希望和平開放,不摻雜任何地域、勢力、信仰爭端。布洛赫與傳統彌賽亞思想不同之處在于他不承認有神論。與費爾巴哈無神論相比,無神的彌賽亞王國既克服了虛無主義和迷信庸俗,也奠定了宗教末世論。“無非是‘人類生存從個人(信仰主體)中心向實體(信仰對象)中心的轉變和神人之間的同一。轉變同一思想構成了宗教經典和宗教教義的主題思想。”人本真的希望是本體論上的追求,道德、音樂、自然、至善這些生活理想不是抽象的,在烏托邦當下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那么懷有烏托邦夢想的實踐者才能在生活之中發現這些美妙的東西,布洛赫認為抓住作為真正的當下的真正東西,“如果烏托邦不指明現在,尋找他所分給的當下,它就徒勞無功,毫無價值。”而我們每個人都應成為這個具體烏托邦的實踐者,尚未形成的現實理想匯集之后就是烏托邦形態的同一。
三、布洛赫烏托邦精神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比較分析
希望哲學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變革關系來看,布洛赫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希望具體的、現實的含義,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含有希望的成分,指出希望的真正意義是指引當下、引領未來。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歸的一個現實的,是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產物,它是將來必然的形式和能動的原則。從“緊迫的需求”與人本質活動的“需要”分析來看,布洛赫“緊迫的需求”與馬克思關于人本質活動的“需要”相對比,布洛赫認為人活著、思考著、行動著,這本身就是一種貧困,這貧困即饑餓、憧憬和探求。他認為最緊迫的需求是人自身最飽滿的愿望,人的原始沖動有很多,相對于饑餓,權利和愛情需求等都是次要的。這里有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人最原初需求是無法壓抑的。馬克思認為,“對象性的本質在我身上的統治,我的本質活動的感性爆發在這里是一種成為我的本質活動的激情”。第二,人不得不在此需求之下發揮能動作用。烏托邦沖動不是人與生俱來,人的需要要在哲學啟蒙下喚醒,人的思想在新奇的創造性自由王國引導下踏上求知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人自己的實現表現在內在必然性,表現為需要。貧困是被動的紐帶,它迫使人感覺到需要最大的財富。”馬克思認為這是一種生命表現力。布洛赫在批判弗洛伊德、阿德勒精神分析論指出“饑餓是人自我保存的沖動,在一切變化無常的沖動中,也許這是人最基本的沖動,因為只有這沖動才使其他沖動開始進行工作”。作為個人都有對和平、美好生活的“饑餓”,這種緊迫的需求迫使人參與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
布洛赫以自身流亡經歷為例,累垮的失業者見證了生存的古老窘境。“無論如何,對饑餓者的同情感是人們擁有唯一廣泛的情感,或者能夠廣泛擁有的情感。”那么這種人道主義也是人和人聯系的紐帶,因此布洛赫認為冷酷的婦女看見乞丐滿足地喝下送給他的一碗湯時,她也得到了相應的滿足感,她不會嫌麻煩,也不會有吝嗇小氣心理。布洛赫認為這是一種“充滿的和期待的情緒”的人道主義。他從人性角度出發,認為在社會中,人在同情感中包含對自身困境的思考和自身飽滿的愿望。馬克思從自然界和人在社會中普遍的關系得出人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社會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實現了的人道主義”,人的希望如同饑餓是人的原初沖動,是壓抑不住的,人的存在就應該把這種希望導向正軌,烏托邦精神是人為希望的存在,人是烏托邦的主體更具有人道主義的烏托邦實踐的意味。
四、“具體的烏托邦實踐”與馬克思主義
20世紀初,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哲學代替了實證主義、黑格爾主義、新康德主義登上歷史舞臺,韋伯、齊美爾、布洛赫等哲學家反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戰爭行徑和罪惡剝削,他們痛恨戰爭,期望一個理想的社會降臨,渴望一個持久和平沒有敵意的國度。布洛赫認為“斯巴達軍事國家是遠離理想世界的。直觀的表述就是,理想世界只限于最好的體制(Best constitution),而不是抽象的體制,而是在有形的整體(The concrete totality of being)中被感知和培養。”按照布洛赫的表述,社會進步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這種最好的體制(Best constitution)是趨近于希望世界的一種社會形態下的必然產物。那么這里以古代斯巴達軍事國家為例,暗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國家是與充滿希望的理想國家背道而馳的,他們不存在希望,不是通過修正、改良可以步入正軌,由此可以從邏輯上推出資本工業是為戰爭侵略服務的,資本主義和平就是個悖論。同時布洛赫也是批判歐文、傅立葉抽象化的烏托邦世界,與盧卡奇的思想相似,布洛赫認為,一方面,資本主義將勞動和勞動者相剝離,在現實生產過程中,資產階級往往把生產從總體生產過程中分離,把工人作為人的個性湮滅,把工人勞動過程分化為部分所得。另一方面,法西斯軍國主義是支離破碎的病態體系,戰爭中的人面對喪失總體性的世界缺乏批判和超越維度,“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合理化導致形式規律的創造,全部這些事物都的確要歸入膚淺的觀察者看來是構成一般的規律的統一體系中。”人的實踐活動和人的關系而形成的具體的總體性是人與人之間的有機統一和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前提,盧卡奇認為“分化破壞了一切勞動和生活的有機統一的過程,并且把這個過程分解成其組成部分。”由此比較分析可以推出,布洛赫和盧卡奇在思想上有共同之處,布洛赫希望哲學是面向未來的辯證法,盧卡奇是致力于總體性原則和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他們都是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同程度地受韋伯等人的文化哲學和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滲透,“面對人受各種異己力量的壓迫與統治現狀,布洛赫關注人類解放或人的自由與全面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使現存世界面向未來發生變革,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希望哲學的基本原理是富有創造性的理論,有極強的實踐性和導向意義,希望實質上是預言者的一種預言,意味著永恒理想的具體實踐,在這里布洛赫更加強調自己非未來的預言者而是參與現實歷史進程的實踐者。布洛赫打破了固有的絕對社會形態,對資產階級的文化功利主義、虛無主義和市儈主義進行了強烈批判,布洛赫希望哲學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分化與演進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在《希望的原理》這部關于希望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中,更加明確布洛赫分析和揭示了白日夢對人們的作用,探尋出希望對人們追求美好世界的積極動力,定義尚未確定的概念和范疇,描繪了人類最終要到達的烏托邦世界的未來圖景。布洛赫的希望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和完善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布洛赫本人也是一位對人類社會發展充滿希望的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辯證法中尋找烏托邦希望,在希望中運用辯證法,卓有成效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新的廣闊視域。
參考文獻:
[1][德]伊曼努爾·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42.
[2]段德智.宗教學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311.
[4]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 王偉光,張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01,104.
[5]衣俊卿.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