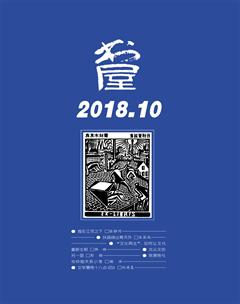文學慧悟十八點(四)
劉再復
第十一講 文學的拐點
(一)文學史上的轉折現象
文學的拐點,只是個通俗的說法。如果作點書面化的表述,便是文學的“轉折點”。正如哲學上講“矛盾”、“悖論”、“二律背反”,其實三個概念是一個意思,只是通俗一些和哲學化一些的不同表述。文學發展到一定時候,它會拐彎,發生轉折。對于文學思潮的研究,歸根結底是對文學拐點與轉折點的研究。例如,我們常說的“悲劇”,在古希臘那是“命運的悲劇”,如《俄狄浦斯王》,先知預言他將發生“殺父娶母”的不幸。他拼命逃脫這個預言,結果還是陷入這種命運,這是無可逃遁的宿命。這是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命運悲劇”。那是“神”主宰一切的時代,“人”無能為力,也無可逃脫。文藝復興之后,我們看到的悲劇,如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則是“性格悲劇”,無論是哈姆雷特、奧賽羅,還是麥克白·李爾王,他們都是“人”,其悲劇,都是性格所決定的。這個時期作家的理念是“性格決定命運”。到了近代,則出現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這些作品也可以稱作悲劇,但已不算命運悲劇或性格悲劇。正像《紅樓夢》一樣,大家都認定它是悲劇,但沒有人把它界定為“命運悲劇”或“性格悲劇”。若稱它為“關系悲劇”,就更為貼切一些。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就說林黛玉之死,乃是“共同關系”的結果,也就是說悲劇是日常生活人際關系合力的結果。魯迅說,寫實的悲劇是“幾乎無事的悲劇”,即人們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發生“關系”,相互作用,動機都是“善”的,性格也無可挑剔,結果就產生了悲劇。所以稱這種悲劇為“關系悲劇”也有道理。綜上所述,就可以說,從命運悲劇到性格悲劇,是一個“拐點”;從性格悲劇到關系悲劇,又是一個拐點。至于在拐彎(轉折中)中哪一個作家的哪一部作品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那是需要研究和探討的。
悲劇有許多“拐點”,喜劇同樣也有許多拐點。喜劇開始于丑角戲,那是“滑稽”,那是“諷刺”。諷刺劇之后是“冷嘲”劇,“冷嘲”之后則是“幽默”,幽默之后又是“黑色幽默”。那是令人落淚的幽默。還有“怪誕”等,也屬于“喜劇”的大范疇。一部喜劇發展史,大體上是喜劇的拐點史。喜劇的幾度轉折,最后產生《堂·吉訶德》、《西游記》、《儒林外史》等杰作。
(二)中國文學的拐點
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文學以“詩”、“文”為正宗,以戲劇、小說為邪宗。而西方文學的主脈一直是戲劇與小說。
因為以“詩”、“文”為正宗,所以詩的拐點也正是文學的拐點。中國的詩原是古詩,也稱古體詩。從古體詩變為近體詩,這就成了一大拐點。在此拐彎中,律詩的出現便是一個關鍵點。古體詩有三言、四言、六言諸體。律詩則只有五律(五言)與七律(七言)。兩種律體都有押韻與平仄的規定。詩發展到唐代便走向高峰。那么,唐詩如何走向宋詞?這又是一個“拐點”。要說明這個拐點,就得研究詞是怎樣發生與發展。我讀過盧翼野先生一篇研究詞的文章,他說,從詩到詞的轉折,重要的是“樂”的需求與參與。樂包括“古樂”、“胡樂”、“俚樂”(民間歌聲)。由于樂的影響,“詞”便逐漸成為獨立的文體。這種文體本身的發展又有自己的拐點。詞論家說:“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那么在向“大”向“深”發展的路上,誰又是扭轉詞性與詞風的拐點呢?盧文說這其中有四個關鍵點:(1)宋初,有晏殊寫的保守五代十國之舊作風;(2)到了柳永,便開“慢詞”之源;(3)蘇東坡橫掃綺羅香澤之習,這是詞的“變正”;(4)周邦彥完成了詞的文章與音樂的結合。但盧文沒有提到李后主李煜。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則把李煜視為中國詞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點。他說,到了李后主,詞的格局始“大”。這說明,確定文學的“轉折點”(拐點),不同的文論家會有不同的看法,爭議是難免的。
中國的小說發展也有自己的“拐點”。從《山海經》這種小說胚胎,變成《世說新語》小故事,再發展為“話本”,最后變成敘事性小說。這一過程的“拐點”在哪里?大可研究。小說拐彎的歷程中,佛教“變文”的傳入產生了什么影響?哪部小說的出現真把敘事藝術帶入長篇?梁啟超提倡新小說之后,中國小說產生了什么“突變”?種種問題,都值得我們探討。
(三)西方文學的拐點
西方文學的“拐點”內涵,更多地表現為文學思潮的轉折。例如從古典主義(真古典主義→偽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的轉折,從浪漫主義到自然主義的轉折,從自然主義到寫實主義的轉折,從寫實主義到荒誕主義的轉折,都是大拐彎。在這些大拐彎中,哪一位作家的作品稱得上“拐點”即轉折的標志,文學史家的看法常有分歧。例如從古典主義思潮轉向浪漫主義思潮,有人說拐點是雨果(法國),有人說是拜倫(英國),也有人說是斯達爾夫人,甚至有人說是始于盧梭。其實,浪漫主義作為沖擊“完美”古典主義的革命文學運動,它在不同的國家中有不同的重心和不同的形態。在法國,雨果無疑起著杠桿作用,但盧梭何嘗不是“動力源”之一;在英國,濟慈、拜倫、雪萊都可視為浪漫先鋒。三者誰為首席,不易說清。而在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可視為“拐點”;在西班牙,其浪漫主義顯然受英國與德國影響,但誰為始作俑者,則不明顯;在意大利,其浪漫文學原是受宗教影響較烈,其特點與英、法又有不同。
(四)自然轉折與人為轉折
在研究“文學拐點”時應當注意自然拐點和人為拐點之分,也就是注意自然轉折與人為轉折不同特點。
自然轉折是文學發展到一定時候,某種文學形式發展到飽和狀況,難以繼續前行,那么“鐘擺現象”,從此一方向轉向彼一方向。而人為轉折則帶有“改革”與“革命”形態,這乃是一些作家對文學現狀不滿而刻意推動的文學轉型。我對這兩種不同形態的拐彎,均不作籠統的價值判斷,只看轉折的后果是推動文學前行還是障礙文學的自由。但是,一般地說,自然轉折才是正道,而人為轉折即革命形態的轉折,往往會破壞文學本身。
因為文學乃是充分個人化的精神活動,而且是純粹的精神活動。它本來是無須革命的。我一再說,文學是心靈的事業,是一個字一個字從心靈深處流出來的事業,并不是外力可以控制的事業。今天我還要說,即使是推動文學進步的改革活動即人為拐彎活動,例如五四新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那也是需要創作實績才能實現拐彎的。那個時代,固然有陳獨秀的《文字革命論》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打先鋒。但是,如果沒有之后出現的魯迅新白話小說和胡適、郭沫若的新白話詩,那也實現不了文學的轉折。所以我提出一個論點,即創作先于轉折。最好是像卡夫卡那樣,先有了《變形記》、《審判》、《城堡》這些創作,然而才談得上從浪漫寫實文學到荒誕文學的轉折。創造文學拐點的人,畢竟是那些真正的作家與詩人。雨果、濟慈、拜倫、雪萊、卡夫卡等等,他們都先是文學創造者,然后才是文學轉折的代表性人物。
(五)作家個體創作的拐點
上邊所說,均是文學整個的轉折拐彎現象,即多少帶有“文學思潮”與“文學風氣”的特點。下邊要說的,不是文學整體現象,而是作家詩人個體的“拐點”與“轉折點”。
作家詩人個體,他們的文學創作中,或由于國家變故,或由于個體人生變故,也會發生大拐彎與大轉折。而轉折的方向有朝前進步而更輝煌的,也有朝后退步而彷徨無地甚至一落千丈的。
前者可以李煜為典型。他原是后唐君主,在宮廷中就寫詩詞,但是當時他或為太子或為國君,過的日子都是征歌逐舞、沉湎聲色,所寫下的也都是艷情與傷情,內容平庸,脂粉氣很重,與花間詞派的基調沒有多大差別。后唐被宋滅后,他的個體人生隨著“國家”發生巨大變故,從帝王變成囚徒,因此,其詞也發生了大轉折,轉折之后的詞與轉折之前的詞風、詞色完全不同。亡國之前,他的詞可以《玉樓春》、《菩薩蠻》為代表,前者云:“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云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后者寫道:“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刬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這首詩寫的是他與小周后的月夜幽會。深院邂逅,席間調情,卿卿我我,依依難舍。說到底,也只是艷情艷詞。而亡國之后,李煜詞則一掃前期的“娘娘腔”,把家國的苦難與天下蒼生的苦難連在一起,如基督、釋迦那樣擔負起人間罪惡,所以才寫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詩句。李煜詞的拐點是“亡國”,亡國導致他帝王的巨大落差(從帝王變囚徒),這種落差又進入他的心靈,促成他的心靈轉折最后又化為詞風的轉折。
李煜人生與詞作的拐點是非常積極的拐點。中國人常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在他身上全都應驗了。但也有國家變故與人生變故造成消極的拐點的。例如張愛玲,她在新中國建立之前,青年時代就寫出《金鎖記》與《傾城之戀》等天才之作。可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她彷徨無地,逃離內地到香港后,她又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放棄原來的“美學立場”,拐到她原先反對的立場上去,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寫了《秧歌》與《赤地之戀》,把自己的作品變成反共宣傳品,其創作再也沒有文學價值可言。張愛玲這一拐彎,可以理解(生活所迫),但讓人感到可惜,她的拐點顯然是失敗的拐點。
第十二講 文學的制高點
(一)文學高峰現象
文學的制高點,是指文學的高峰。這是每個作家所追求的目標。作家的立志,立的便是“高峰之志”。作家的夢,也是“高峰夢”。“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是杜甫歌吟泰山的詩。我們今天所講述的正是什么才算登上了文學的“絕頂”,作家“凌絕頂”如何可能。什么是文學的高峰?我們可以做出的一種回答,凡是能夠代表一個民族或整體人類的精神水準并能夠成為一個民族或整個人類共同仰慕、閱讀、長久傳頌的文學經典,都可稱之為“文學高峰”,或“文學制高點”。例如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希臘的悲劇(《俄狄浦斯王》等),但丁的《神曲》,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雨果的《悲慘世界》,拜倫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變形記》,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這是世界文學公認的高峰。中國文學的高峰,則有《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就詩人作家而言,則有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李煜、蘇東坡、湯顯祖、吳承恩、曹雪芹等,這些名字都標志著文學的制高點。如果我們再進行分類,那么,可以說,中國的貴族文學,高峰有屈原、李煜、曹雪芹三座。山林文學的高峰則是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等。倘若再細分,那么,中國的愛情詩、邊塞詩、頌歌、挽歌等都有自己的高峰。詩有詩的高峰,詞有詞的高峰,散文有散文的高峰,小說有小說的高峰。
(二)文學高峰有無標準
那么,高峰有沒有標準?更具體地問:有沒有客觀標準?有人認為沒有。中國有句話說:“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說,對美人的判斷是主觀的。對文學的判斷也是如此,各有各的評判標準和審美趣味。古人說“燕瘦環肥”,講的是漢代以“瘦”為美,認為像趙飛燕那樣瘦才算美。到了唐代,則以“胖”為美,認定唯有像楊玉環那么“肥”才美。宋以后又不喜肥,甚至認為瘦得有點病態才美。《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十分瘦弱,而且有肺癆病,卻被許多人認定為絕世美人。托爾斯泰也不喜歡強悍的女人,他希望理想的女人應當瘦弱,甚至常常有點病。可見,審美帶有主觀性,而且有動態性(即有變遷)。魯迅說,對于同樣一部《紅樓夢》,革命家看到的是“排滿”,道學家看到的是“淫”,賈寶玉看到的是許多人的“死亡”。莎士比亞是世界公認的文學高峰,但另一位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卻不喜歡,他批評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說的話都是一個腔調,連仆人口里的語言也如詩歌。可見,兩位文豪之間的審美標準是何等不同。后人猜測托爾斯泰排斥莎翁的種種原因。我說過,可能是兩個:一是托爾斯泰不滿莎士比亞對基督教的輕蔑態度;二是守持寫實主義的托爾斯泰不滿莎士比亞的浪漫筆調。總之,美學是“有人美學”,而非“無人美學”。因為有“人”,才有善與惡,才有美與丑之分,這乃是真理。說美只有純粹客觀性,這不對。
然而,美與文學就沒有客觀標準了嗎?高峰沒有客觀標準嗎?不。那些經過大浪淘沙,經過時間淘汰而讓千百代人所喜愛的作品,例如李白、杜甫、蘇東坡的詩,例如李后主的詞,例如《西游記》、《紅樓夢》等小說,大家都喜歡,批評抹不掉,它們確實有種永恒性的魅力。這里,實際上有種客觀標準在起作用。
那么,什么是衡量“高峰”(經典)的客觀標準呢?意大利著名的小說家卡爾維諾提出關于經典的十三個標準。我在《文學常識二十二講》里已引述過。他的論述最值得注意的是說經典可以“不斷重讀”,即常讀常新。也就是說,經典是那些經得起不斷進行審美再創造的作品。
近日,韓少功先生到校做學術訪問。這期間,他到中文大學作了演講,說經典有三個標準:一是“原創的難度”;二是“價值的高度”;三是“共鳴的廣度”。我對“三度”解釋道,原創的難度只要想想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吳承恩的《西游記》就明白了。《尤利西斯》一掃過去的創作程式,那么長的長篇,書寫的僅僅是一天的故事。他還創造了“意識流”的全新寫作方法,難怪一問世就遭到排斥與禁錮。還有《西游記》,過去的小說,要么寫“人”,要么寫“鬼”,而它則把天、地、人、佛、神、鬼、妖怪等全都放入作品,融為浩浩蕩蕩的一爐,真是奇觀。韓少功所講的這三個標準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第三個,即“共鳴的廣度”。所謂共鳴廣度,當然不是指“暢銷量”,即不是當下市場的買賣指數。如果是指市場,那么,莎士比亞與托爾斯泰恐怕比不上現在年輕的中國網絡作家。我猜想,“共鳴廣度”應該是一個長遠的標準,也就是說,它應該能夠超越歷史時間的阻隔,從而找到廣泛的后世知音。而且,它還能沖破政治、宗教、民族的阻隔而找到各種知音。還有,它應當沖破老年、中年、青年、少年的年齡阻隔和這一代與那一代的“代溝”,而讓人產生廣泛的共鳴。
(三)中國美學家眼中的文學制高點
中國的美學家,如鐘嶸(《詩品》)和陸機(《文賦》)等,把詩人分為若干等級,并規定了最高等級。今天時間有限,只講兩位現代美學家的高峰尺度。
一是李澤厚的高峰尺度。他在解述“審美形態”時說,把審美形態分為三級。較低的一級的作品只能“悅目悅耳”;中間的一級則可“悅心悅意”;最高的一級則可“悅神悅志”。第一級只是感官的愉悅,屬于生理性愉悅,當然比較低級。第二級則是內心愉悅,屬于心理性愉悅,這就較為高級了。最高級的悅神悅志,這就完全超世俗而進入靈魂深處,“心有靈犀一點通”了。他解釋道:這大概是人類具有的最高級的審美能力了……悅志悅神是在道德的基礎上達到某種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所謂超道德,并非否定道德,而是不受規律包括不受道德規則、更不用說不受自然規律的強制、束縛,卻又符合規律(包括道德規律與自然規律)的自由感受。悅志悅神與崇高有關,是一種崇高感。
李澤厚先生的這段解說,是在說明最高級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感受(這當然包括文學藝術提供的審美感受),應是一種超越道德、超越自然規律又符合道德和自然規律的自由感受。這是超世俗、超人間的與天地相通、與神志共鳴的境界。偉大的作家詩人,他們抵達文學的制高點,在精神層面上就得抵達“悅神悅志”的天地境界。這是把文學情感提升到精神的頂端,即只可領會很難口傳的頂端。人們用“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來形容莎士比亞,就因為莎士比亞代表文學頂端那種讓人闡釋不盡的精神內涵。
在李澤厚先生之前,朱光潛先生在《談文學》一書中,則具體講述了寫作“四境”,也就是說,寫作也要攀登最高境界。如果說,李澤厚是從宏觀上把握文學境界,那么,朱先生則是在微觀上把握文學境界。他說寫作可分為“四境”,寫作者一般都得歷經這四境而抵達高峰。這四境是“疵境”、“隱境”、“醇境”、“化境”。制高點是“化境”。朱先生的說法,對我們這些剛走進文學之門的學子特別相宜。他以寫字作比喻解釋說:
文學是一種很艱難的藝術,從初學到成家,中間須經過若干步驟,學者必須循序漸進,不可一蹴而就。拿一個比較淺而易見的比喻來講,作文有如寫字。在初學時,筆拿不穩,手腕運用不能自如,所以結體不能端正勻稱,用筆不能平實遒勁,字常是歪的,筆鋒常是笨拙扭曲的。這可以說是“疵境”。
朱先生說經過不斷練筆,字才能寫得平正工穩,合乎法度,進入“隱境”;再苦練下去,不僅工穩,而且有美感,這便是“醇境”。最后才抵達高峰進入“化境”。朱先生說:
最高的是“化境”,不但字的藝術成熟了,而且胸襟學問的修養也成熟了,成熟的藝術修養與成熟的胸襟學問的修養融成一片,于是字不但可以見出純熟的手腕,還可以表現高超的人格;悲歡離合的情調,山川風云的姿態,哲學宗教的蘊藉,都可以在無形中流露于字里行間,增加字的韻味。這是包世臣和康有為所稱的“神品”、“妙品”,這種極境只有極少數幸運者才能達到。
朱光潛先生所說的“化境”,也就是我們這堂課所講的“制高點”。無論是李澤厚先生所說的“悅神悅志”之境,還是朱光潛先生所說的“化境”,都告訴我們,寫字作文,創造經典,道理是相通的。要攀登文學藝術的高峰,首先從境界上去占領“制高點”,實現技巧和精神的高度融合,實現手腕、人格、情調、姿態、意蘊、神志的完美合一。
第十三講 文學的焦慮點
(一)文學的焦慮點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焦慮。從事政治的,焦慮的往往是官位坐不穩;從事經濟的,焦慮的往往是企業虧損或工廠倒閉;從事宗教的,焦慮的往往是信徒不真誠;而從事文學、藝術、體育的,焦慮的則是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線。如果你有一個作家朋友,而且他是一個好作家,那么,你問他,你的焦慮是什么?他大約會回答:如何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現在偽作家很多,他們想的是出名、賺錢、當官,其焦慮內容我們無須談論。我們要探討的只是好作家、認真的作家會有什么焦慮。我相信,好作家的唯一焦慮是寫不出好作品,是難以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二)焦慮的爆炸與作家的自殺
寫出好作品,突破(超越)自己,這是好作家最內在、最深刻的焦慮。這種焦慮如果長期不得釋放,就會產生消滅自己(自殺)或面臨深淵的恐懼。有些著名的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突然自殺,如法捷耶夫、馬雅可夫斯基,如川端康成等,許多人研究他們的死因,但都無法了解他們自殺的最隱秘、最深刻的原因。就以法捷耶夫而言,他原是蘇聯的一位極為優秀的小說家,其代表作《毀滅》,魯迅譯成中文后自己愛不釋手,給予很高的評價。后來,法捷耶夫又寫出另一代表作《青年近衛軍》。但是,他成了斯大林手下掌管蘇聯文壇的文藝官僚(擔任蘇聯作協總書記)后,其創作卻無法長進,他被困死在自己參與制造的各種囚牢中,其痛苦和焦慮有多深,無人說得清,最后他選擇了自我毀滅。從寫作《毀滅》到走向“自我毀滅”,其道路令人驚心動魄。自我毀滅之前,他給蘇共中央寫了遺書,此信是他內心焦慮的總爆發,說的全是真話心里話,他說:
上蒼賦予我巨大的創作才能,我原本應當為創作而生。可是,我像一匹拉車的老馬那樣被驅使著,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些誰都會做的平庸的不合理的官僚事務之中,甚至現在當我總結自己一生的時候,多少呵斥、訓斥、訓誨向我襲來,而我本應是我國優秀人民引以為榮的人,因為我具有真正的、質樸的、滲透著共產主義的天才。文學——這新制度的最高產物——已被玷污、戕害、扼殺。暴發戶們在以列寧學說宣誓時他們的自負就已背離偉大的列寧學說,令我對他們完全不信任,因為他們將比暴君斯大林更惡劣。后者還算有知識,而這些人不學無術。
法捷耶夫的遺書值得我們一讀再讀。他作為蘇聯作協領導人,最后走上自我毀滅之路,完全是焦慮發展到極限即焦慮爆炸的結果。他深知自己具有創作才能,也應當走文學創作之路,然而,那個龐大的政治組織卻壓抑他的才能,讓他陷入無益的、平庸的官僚事務之中,他不僅消耗了本可以創造的生命,而且招惹了其他人的嫉妒與打擊。一個真正的作家對此不能不陷入嚴重的苦悶和焦慮,而這種大苦悶與大焦慮又無處可以解脫,那就只能自殺了。
請同學們注意,我國也有一些法捷耶夫式的擁有創作才能的文藝界領導人,如郭沫若、周揚、張光年等,但他們都缺少法捷耶夫式的巨大文學良心與剛毅的自由精神,即缺少可以為文學去死、去自我毀滅的精神。其中如周揚,他晚年也有所覺悟并有所懺悔,內心也充滿苦悶和焦慮,但其對文學的真誠度和酷愛度還是未無法與法捷耶夫相比。為什么?這正是值得我們反省之處。
法捷耶夫于1956年自殺,過了十六年,日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自殺。關于川端康成為什么自殺,研究的文章很多,有的還加以歸納,說明可能有六種原因。這六種原因是:(1)死于病魔纏身;(2)死于安眠藥中毒;(3)死于思想負擔過重;(4)死于精神崩潰和文學危機;(5)死于三島由紀夫自殺的打擊;(6)死于支持秦野競選的失敗。自殺的緣由往往是綜合性的,上述的原因可能都道破川端康成自殺的部分原因。但我認為,他的自殺肯定與第三點、第四點有關,即所謂思想負擔過重、精神崩潰、文學危機。因為川端康成獲獎后日本舉國慶賀,連裕仁天皇也通過宮廷的一名高級官員,還有佐藤首相都親自打電話表示祝賀。可是,他在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獲獎之后再也寫不出傳世經典了。他一直堅持唯美主義的創作路向,以虛幻、悲哀、頹廢為自己的創作基石,獲獎后,其頹廢主義加速發展,病態心理和色情描寫更為濃烈,顯然,他已找不到突破自己的出路,于是便為大苦悶與大焦慮所壓倒。我想,這才是川端康成自殺最內在的原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川端康成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他固然為日本的戰敗而憂傷,但一定是把文學當作自己的第一生命。文學上發生危機,再也拿不出與自己盛名相副之作品,這才是他的第一焦慮。
(三)從焦慮到恐懼
卡夫卡是個天才。他扭轉了世界文學的杠桿,把以寫實、抒情、浪漫為基調的文學改變成以荒誕為基調的文學。他生前默默無聞,但也默默地洞察世界與人生。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學,竟也常常為不能突破自己而感到恐懼。他清醒地認識到,唯有這種恐懼,才是對文學的摯愛與真誠,所以他把這種屬于自己的恐懼視為內心最美好的部分,并為之傾注全部智慧。他說:“我的本質是恐懼,確實,恐懼是我的一部分,也許是我身上最好的那部分。完全存在對恐懼合理的承認,比恐懼本身所要求獲得的還要多,我這么做并不是由于任何的壓力,而是欣喜若狂,將自己的整個身心全部地向它傾注。”
卡夫卡這段話里所講的“恐懼”,乃是內心的焦慮,并非外部的“壓力”。可以肯定,這是“突破自己”的焦慮。所以他說這是生命中最好的部分。不錯,有什么能比憂慮自己的創作如何突破更有價值更值得引為自豪呢?一個真正的作家、藝術家,他對自己的藝術未能進步會產生焦慮與恐懼,這與那些當不了大官、賺不了大錢而陷入困頓的政客和財主們相比,是何等高貴,何等寶貴!可惜這種內在的焦慮和恐懼感,也是人間最美的情操,快要滅絕了。人們正在瘋狂追求權力、追求財富、追求功名,“世人都說神仙好,唯有金錢忘不了”。人們瘋狂追求榮華富貴,哪能想到另有一些真正的人,真正的作家和詩人,他們心中卻有另一種焦慮,另一種恐懼。這是文學的焦慮與恐懼,這是何其芳、李準、曹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卡夫卡的焦慮。但愿在座的同學們,也永遠只有這種高貴的焦慮,而少有世俗人那種權力、財富、功名的煎熬與痛苦。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