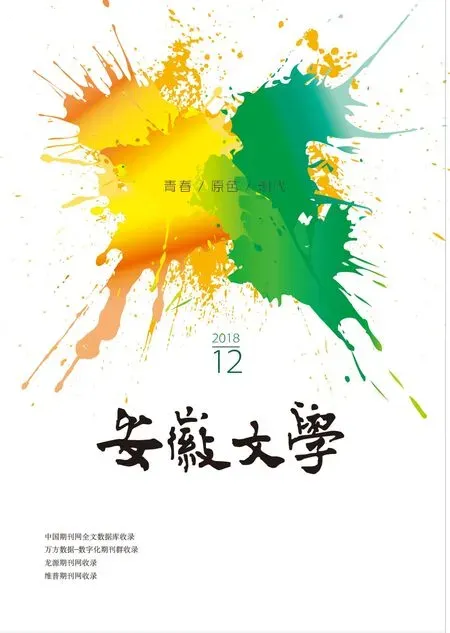扭曲·扼抑·偽形
——試論子弟書對于《牡丹亭》的改編
毛譽澄
江蘇師范大學敬文書院
湯顯祖是中國古代戲曲創作上廣為人知的大家,他的《牡丹亭》亦是中國戲曲史上的一座奇峰。湯顯祖曾經自稱,“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①。《牡丹亭》之所以在橫空出世之后就備受贊譽,直到今天依然受到社會廣泛人士的喜愛,不僅在于其辭藻的唯美華麗,感情的真切動人,更在于湯顯祖在其中傾注了對于兩性情感與人性的自由和解放的思考,可以說,《牡丹亭》是晚明個性思潮下結出的文化碩果。
子弟書是一種由八旗子弟創制的曲藝形式,在清代曾經廣泛流傳,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在存世的子弟書中,有五部是改編自《牡丹亭》的作品,本文就試圖圍繞子弟書對于《牡丹亭》的改編展開,試圖以《牡丹亭》為例,就明清易代之后,在滿清統治者的文化政策下,晚明倡導思想與個性解放的文化藝術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扭曲、扼抑、偽形的狀況進行探究。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是提出形態歷史學的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與哲學家,本文的選題即是受到斯賓格勒的影響,他在《西方的沒落》中分析了阿拉伯文化的變形,陳曉林先生概括斯賓格勒對于阿拉伯文化之所以發生“偽形”現象原因的分析時這么說,“所謂‘歷史的偽形’,即是指在阿拉伯文化尚未成形時,由于古典文明的對外擴張,武力占領,以致整個被古典文明覆壓于上,不能正常地發展,故而其文化型態與宗教生命,皆一時被扭曲而扼抑,但古典文明其實已經血盡精枯,只剩下一個空殼”②。就筆者的看法而言,在《牡丹亭》的傳播過程中,也發生了所謂文化的“偽形”現象,《牡丹亭》在傳播過程中,原本表達對于個體的尊重,對于愛情,對于自由的真摯追求,揭露美好的生命被社會的禮教壓制與摧殘的主旨逐漸消失,表現出了一種空有其形,而無其神的狀態,筆者認為,至少子弟書這一說唱藝術的樣式對于《牡丹亭》的改編就是如此。
一、子弟書這一曲藝樣式的特性與扭曲、扼抑發生之外部條件
子弟書這一說唱藝術樣式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由清代旗人所創制。子弟書《子弟圖》中這樣寫道:“曾聽說子弟二字因書起,創自名門與巨族”,“題昔年凡吾們旗人多富貴,家庭內時時唱戲狠聽俗。因評論昆戲南音推費解,弋腔北曲又嫌粗。故作書詞分段落,所為的是既能警雅又可通俗。”,由此可知,子弟書原本是滿清入關之后,旗人生活大多富裕之際,產生的用來消閑娛樂的曲藝,只因為不習慣昆曲的南方聲調,又認為弋陽腔等比較粗淺,因而自己創制了子弟書。《子弟圖》后文“按此說,如今子弟比昔年的苦,總因家道窄,愛押個大寶,葬送在十胡。”,又因為“一分糧,輕易時完不了饑荒多款,六力弓,拼了命也拉不開是水不足”,就“惟有這玩笑場中一條活路,是爺們解讒養命的護身符。”,在日漸貧困,生計難以維持之際,一些旗人開始將子弟書的表演視為自己的 “一條活路,但是盡管如此,“也當想那些無業貧民曾經過告示”,生怕惹出事端,到了衙門之后,“辦一個寡廉鮮恥把旗黨銷除”。
細玩上敘的詞句,我們可以看出,子弟書這一曲藝,實際上是清代旗人這一既得利益群體的玩意兒,在旗人普遍富貴的時期,子弟書出自旗人中的“名門與巨族”,是統治階層的產品,即便是在相當多的旗人在經濟水平上逐漸淪落下層之際,表演子弟書的藝人依然為自己是旗人這一享受國家特殊照顧的群體而感到不同于一般的平民,并且生怕自己失去做旗人的資格。因此,我認為,在對待文化的觀念與品味上,子弟書幾乎始終與帝國的統治階層——滿蒙貴族趨近于一致。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建立政權之后,開始推行實行“振興文教”的政策,并且隨著清初統治者文化素質的提高,清廷選擇了將尊孔具體化而趨向朱學獨尊的歷史道路,對于叛逆性強的陽明心學加以摒棄,并且升格朱熹在祀孔廟的地位,將朱熹的學說確立為官方哲學,作為一種強化封建國家文化凝聚力的努力。③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受到王學左派思想巨大影響的《牡丹亭》,在傳播過程中由于外在文化環境的影響,出現了扭曲,扼抑與變形。
二、子弟書對于《牡丹亭》內容之改造——扭曲、扼抑之內部發生
有學者曾經撰文提出,《牡丹亭》子弟書根據傅惜華《子弟書總目》共有五段(其中的“鬧學”實際上有《鬧學》和《學堂》兩種),子弟書基本表現杜柳的愛情主題,并且說《牡丹亭》通過子弟書的形式其思想性與藝術性更加得到了北方民眾的認可。④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后來已有學者確認所謂五段子弟書中的《游園驚夢》實際上與《尋夢》重合⑤,如果將《鬧學》(全三回)和應為前者刪改本的《學堂》(全二回)分開,仍然視作五段子弟書的話,我認為這五段子弟書幾乎與杜柳的愛情主題無關,甚至連柳夢梅都沒有出現,其中《鬧學》和《學堂》表現的主要是春香戲弄陳最良,《游園尋夢》(全三回)實際上只有第三回才是在表現杜麗娘游園尋夢,《離魂》則是寫杜麗娘與父母訣別,至于《還魂》,他的情節與《牡丹亭》的不同之處在于是觀音說“兒乃龍女來世界,放奴輪回奉二親。壽活五十零九歲,那時復轉紫竹林。”,然后讓杜麗娘還魂,跟柳夢梅毫無關系,而且這一情節表現的是就連神仙菩薩都尊重世俗禮教中所要求的兒女對父母的孝道,與湯顯祖試圖極力表現的“情至”能夠讓“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對于傳統倫理的叛逆思想可謂是完全背道而馳。《牡丹亭》雖然寫的是愛情的主題,但是主旨并不完全在愛情本身,而是在于借此表達對人性的尊重,對自由的渴望以及作者的“情至”思想,然而子弟書中將愛情都已經幾乎剔除了出去,又怎么可能表達湯顯祖由兩性感情生發出的深刻思想內涵呢?其偉大的藝術性又如何為因為子弟書被廣大北方民眾所認可呢?
在《牡丹亭》中,杜寶請陳最良作塾師教杜麗娘讀書,可以說是湯顯祖開明士大夫思想的體現,“看來古今賢淑,多曉詩書。他日嫁一書生,不枉了談吐相稱”,這樣的想法,相比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念,無疑是湯顯祖思想進步性的體現,《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也確實是一個才貌雙全,吟詩作畫的佳人形象,然而在子弟書中,作者借著杜麗娘的口,生造出了“煩死人,一個女孩兒人家進什么學堂?”“念這些《雅》《頌》《國風》何處用?縱學得滿懷錦繡也只平常”,可見子弟書的作者覺得女性進學堂毫無必要,這一點與湯顯祖的想法顯然是背道而馳。
在陳最良講《關雎》的情節上,湯顯祖的《牡丹亭》寫的是此事引發了杜麗娘的春愁,以及對戀人的渴望和思慕,這一點從杜麗娘的話“圣人之情,盡見于此矣。今古同懷,豈不然乎?”和春香責備陳最良講《關雎》引發了杜麗娘之后的一系列事端這兩處可以明顯地看出來。然而在子弟書中,則變成了陳最良說了一通《詩經》“有許多風雅在閨閣”,“無邪二字總包攬”,讓杜麗娘“細心自體”,告誡她這一道理“久自明”,給杜麗娘加上了“小姐揖說承教誨,‘今世難忘師父的德’”的情節,對于所謂由《關雎》引發的春情更是只字不提。《牡丹亭》中原本借此表現出的人性本來的、自然的欲望的不可遏止,禮教的虛偽,在子弟書中全然成為了禮教的規訓,其進步性可以說是蕩然無存。
再比如在杜麗娘在《鬧殤》中,是這樣的表現:
【囀林鶯】(旦醒介)甚飛絲繾的陽神動,弄悠揚風馬叮咚。(泣介)娘,兒拜謝你了。(拜跌介)從小來覷的千金重,不孝女孝順無終。娘呵,此乃天之數也。當今生花開一紅,愿來生把萱椿再奉。(眾泣介)(合)恨西風,一霎無端碎綠摧紅。
雖然不過寥寥數語,卻將杜麗娘即將與母親訣別的悲傷、不舍、內心不能侍奉父母頤養天年的愧疚表現地淋漓盡致,讀來動人肺腑。但是在子弟書《離魂》中,杜麗娘在行將就木之際,開始大段大段地說自己不孝,“短命的丫頭身有罪,糊涂的逆子喪良心。二死后娘阿休念我,分明是討債鬼,父母的仇人”,“叫孩兒生前已做無恩鬼,使麗娘死后還為不孝魂。難道說父母恩情不報也?眼睜睜就是這樣兩難分。世間人養的女兒全像我,可不就哭死為娘作父心?孩兒愿托身犬馬填還父母,雖是個畜生,現在杜門。”原本真實的母女情深、難舍難分,一下子套上了禮教中孝道的枷鎖,仿佛變成了枯燥乏味的說教,甚至是為人子女者的自我虐待,這一轉變,無疑是清代理學官方意識形態的產物,雖然一樣是杜麗娘母女訣別,原本湯顯祖筆下真摯的感情沒有了,加入的是禮教與傳統倫理的異質。
有些令人難受的還在后頭,在這一種子弟書中,杜麗娘主動提出讓父親收下春香為嗣,“勸爹爹收在身邊為一子,豈不是少陵命脈一條根?”,這是子弟書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內容,還有的子弟書寫的不是要杜寶收其為嗣,而是納春香為妾,《還魂》中杜麗娘說“奉勸老父依兒話,春香收下作妾身。上天垂佑生下子,萬代香煙祭先人。”而就在杜寶不同意這么做之后,這部子弟書硬生生地加上了一句 “老夫人五十二歲生一子,鰲頭獨占狀元尊。”,然后就這樣收尾了。中國封建倫理中強調子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對于男性強調要有一個兒子作為繼承人,最好還要能夠金榜題名,光宗耀祖,而子弟書中這樣的情節恰恰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這樣的情節強加在《牡丹亭》故事的改編之下,令我不由想起了斯賓格勒運用“歷史上的假晶現象”來表述“歷史的偽形”時的說法:
一種礦石的結晶埋藏在巖層中。罅隙發生了,裂縫出現了,水分滲進去了,結晶慢慢地被沖刷出來了,因而它們順次只剩下些空洞。隨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發;熔化了的物質依次傾瀉、凝聚、結晶。但它們不是隨意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進行這一切的。它們必須填滿可填的空隙。這樣就出現了歪曲的形狀,出現了內部結構和外表形狀矛盾的結晶,出現了一種石頭呈現另種石頭形狀的情況。⑥
在筆者看來,那種火山爆發的強大力量,就好比清朝統治者通過一系列軟性與硬性的文化手段所扶持的作為官方意志的程朱理學在意識形態所構成的壓力,而這一針對《牡丹亭》的改編過程,恰恰就造成了《牡丹亭》子弟書“內部結構和外表形狀矛盾”的狀況,給予我們讀者好像“一種石頭呈現另種石頭形狀”的觀感,因為原本反對禮教、追求個體解放與自由的內容就像結晶“被沖刷出來”一樣失去了,而在其內部又被加入了原本湯顯祖所反對的壓抑人性的禮教的內容,進而形成了這種非驢非馬的現象,在戲曲發展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頗為奇特的景象。
三、對于子弟書改編《牡丹亭》產生的扭曲、扼抑、偽形之思考
《牡丹亭》是中國戲曲史上的不朽之作,但也因為過于雅化而受到過一些批評,尤其是當時的下層民眾,恐怕缺乏足夠的文化修養去理解《牡丹亭》,從這一角度來說,子弟書對于《牡丹亭》故事的改編,對于《牡丹亭》故事的普及,以及培養其在民間的愛好者和生命力無疑是有意義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子弟書在對于《牡丹亭》的改編過程中,對《牡丹亭》的內容以及湯顯祖在其中表達的思想進行了扭曲和扼抑,進而產生了文化的偽形。
從更為廣闊的視角來說,《牡丹亭》是晚明個性思潮影響下的文化產物,而在清代,晚明產生的個性思潮受到了壓制,培育《牡丹亭》的外在文化環境不復存在,進而其文化的變形,在改編的過程中消失本來先進的文化內涵實際上是一種必然。
20世紀日本京都學派的重要人物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認為中國的現代性是從宋代開始發生的,這一觀點某種意義上也對中國的文學史書寫產生了影響,例如章培恒先生就認為中國自元代以來近世文學的發展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學發展的方向,從而對于我們長期以來受到費正清“沖擊——回應”模式的影響進而將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割裂的認知進行了一定的修正。但是我以為,我們仍然不能低估新文化的傳入對于中國文學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影響,筆者個人對于中國能否在不受外來文化的沖擊的情況下將近世以來出現的一些新的文學發展方向確立為主流是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因為從子弟書改編《牡丹亭》這一個案也可以看出,《牡丹亭》所表現出的尊重個體、解放個性的思想并沒有成為在后世戲曲發展中形成一種不絕如縷、日益強大的力量,甚至在對于它的戲曲改編作品中都出現了扭曲、扼抑、偽形的現象,在這樣一種狀況下,《牡丹亭》中湯顯祖個人帶有先進性的思想恐怕難以被很好地接受。以上僅僅是我個人一些淺薄的思考。
注釋
① (明)湯顯祖,著.(明)王思任,(清)王文治,評點.張秀芬,校.牡丹亭[M].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1.
②轉引自劉再復.雙典批判[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10-11.
③陳祖武.關于清初文化政策的思考[J].文史知識,1990(6).
④王省民,鄒紅梅.《牡丹亭》在民俗文化中的傳播[J].民族藝術,2008(1).
⑤ 昝紅宇,張仲偉,李雪梅.清代八旗子弟書總目提要[M].山西傳媒出版集團,2010:664.
⑥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M].商務印書館,200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