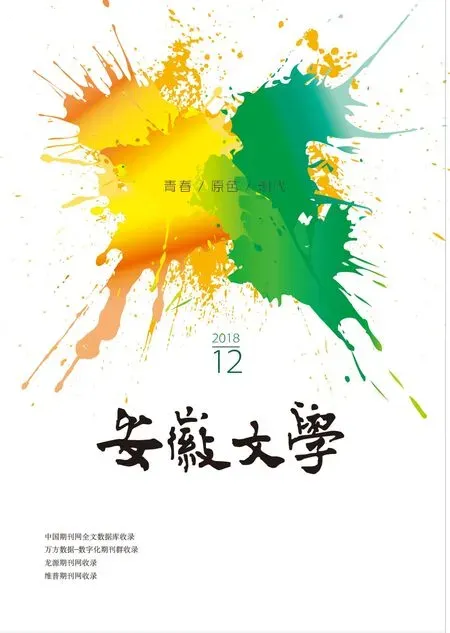味覺詞“酸、甜、辣”通感隱喻式的詞義引申路徑研究
任怡菲
一、引 言
在飲食文化中,“酸、甜、苦、辣”是人所感受到的基本味道,它們的基本義都指向味覺域。一般情況下,人的視、聽、嗅、味、觸五種感官各司其職,不得逾越各自的權限,但在現實表達里似乎并不是這樣。由于常用詞有限而意義無限,人們往往會突破常規語境的限制,在其他領域創造性地使用同一詞語而使該詞具有了特殊含義,推動詞義的發展演變。這樣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人美歌甜”、“口甜心辣”、“酸言冷語”等等,這里的“酸、甜、辣”發生了移位,不再指向味覺域。所以說,人的五官并沒有嚴格分工,它們是彼此相通的,這就是隱喻的特殊形式——通感隱喻。
二、“酸、甜、辣”詞義引申路徑及規律
通感是味覺詞詞義引申的主要原因,而從“酸、甜、辣”的詞義引申中我們可以發現,其詞義不拘泥于某一單純領域,而是多角度、發散性的投射到各個復雜領域。下面本文將從“移域”角度詳細分析味覺詞形容詞“酸”、“甜”、“辣”中存在的通感隱喻現象,并歸納其引申路徑:
(一)從味覺域向嗅覺域的投射
人的口鼻相通,嗅覺與味覺緊密相連,從味覺到嗅覺的通感隱喻最為常見:
(1)一進門,一股刺鼻的酸臭味撲面而來,窗臺、地下全是待發的郵件。
(2)男孩子撥開她的劉海,輕輕的吻了上去,空氣里都是香甜的味道。
表味覺的“甜”、“酸”和表示氣味的“香”、“臭”的組合體現了味覺與嗅覺兩種感官的結合,根據語義特征分析中語義句法的雙向選擇性,兩類詞存在共同特征,當味覺詞與嗅覺類詞語組合時,味覺詞單純表味覺的意義被削弱,轉而增加了嗅覺義,實現了跨感官的感知,當其真正轉化為與之組合的詞義的某一成份時,味覺詞就已經徹底隱喻化了。
(二)從味覺域向觸覺域的投射
(3)兒子問她,老師都說了些什么。她鼻子一酸,差點流下淚來。
(4)大娘說:“在家呆著總覺腰酸腿疼,出來修車干活,身子倒舒坦。
味覺詞“酸”可以指向觸覺域,因“酸”味有時給人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所以被借用來表示因疲勞或疾病而引起的微痛無力、酸脹酸軟的感覺,從生理上看,“骨酸、腰酸、鼻子酸”均表示肌肉酸痛或酸脹,是身體接受刺激而產生的疼痛不適感。此處沒有找到“甜”的用法。
(三)從味覺域向情感域的投射
(5)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
(6)每當看到別人的成功,他便心里泛酸,總要私下酸上幾句。
(7)兩人在節目中的互動真甜。
除五官互通外,“酸”、“甜”、“辣”詞義引申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味覺向情感的投射。例(5)中的“酸”意為辛酸、悲痛;例(6)中的“酸”表示嫉妒之情;例(7)中的“甜”表示幸福的感覺,三例都表示人的心理活動,指向情感域。由于每個人對味道的感知不同,無法為“酸甜苦辣”設置一個固定的標準,所以味覺詞就帶有了較強的主觀性,其引申義多與情感相聯,味覺詞的引申義多與個人喜好相關,Sweetser(1990)將這稱為以身喻心隱喻。由于“酸”是一種刺激性味道,聞起來刺鼻,喝起來味沖,人們對這種刺激性味道往往產生排斥感,這種強烈的味覺刺激體驗從生理感知域投射到心理感知域時,會使其帶上消極色彩,引申出了心理上的不快或內心的辛酸、悲痛。而“酸”的“嫉妒”義與“酸”的本義“醋”密切相關,是“吃醋”義在程度上的加深。與“酸”相反,“甜”具有的甜蜜美好的味覺體驗則會給人帶來愉悅、幸福的心理感受,人們在吃甜食時這種感受更為直觀,所以“甜”投射到情感域時常帶有積極色彩,表舒服、幸福。
(四)從味覺域向聽覺域的投射
(8)工廠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你只能聽人家的酸言冷語。
(9)她在晚會上高歌一曲,被隔壁廠房的小伙子夸贊人美歌甜。
(10)在他的甜言蜜語下,大青很快的相信了。
例(8)中的“酸”表示譏諷語氣,使人反感、不快;例(9)中的“甜”表示“聲音潤澤、動聽”;例(10)中的“甜”表示“討好、奉承”。這些例句中的味覺詞均投射到了聽覺域,形容語氣、曲調及言論。因為“酸”表刺激性味道,會給人帶來不適感,而譏諷的言語同樣令人難過、反感,情感體驗的相似性使“酸”投射到了聽覺域,且多帶有消極色彩。“甜”通常表美味可口義,能給人帶來美好的心理感受,但物極必反,當我們所食甜食過多時,會產生甜膩感,甚至帶來生理上的不適。同樣,當我們聽到過于親密、奉迎的言辭、語氣時,也會感到心理不適,甚至產生生理排斥反應,比如反胃。基于身心上相同的不適感,感官得以互通,味覺“甜”可投射到聽覺域,但略含貶義。
(五)從味覺域向視覺域的投射
(11)臉兒甜,話兒粘。
(12)有底滑稽堪羨處,金蓮燭底話窮酸。
(13)聞得郎君倜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
在以上三例中,“酸”、“甜”向視覺域進行了移位。因為“酸”可引申為內心的不快,在古代,寒門書生迂腐的言談舉止,或其故作儒雅之態,或其窮酸潦倒之態,都同樣能引起旁觀者的心理上的不痛快,因而用“酸”描寫書生儀態。同時,“酸”還可引申為辛酸、傷心的感覺,書生落第常會產生此感,“酸楚、悲痛”如影隨形。所以“酸”與書生形象緊密相聯,常見的表達為“酸秀才”。“甜”投射到視覺域一般指面容甜美,使人心理上感覺舒服、暢快的容貌,這里的“甜”可以視為“甜美”的單音化,“甜”具有了“美”的語義特征,擴大了“甜”的語義內涵,可以用來指稱視覺域。
(六)從觸覺域向其他感官域的投射
前面我們分析了“酸”、“甜”的通感隱喻現象,原因在于“辣”這一味覺詞所表示的義域不屬于味覺域,而是觸覺域。從生物化學的角度說,人的四種基本味道是“酸甜苦咸”,“辣”本不是一種味道。它本質上是舌頭灼傷的痛感,所謂的酸辣、甜辣是一些更為基礎的味道和通感的組合。
“辣”的義項1“刺激性氣味”為本義,義項2“辣味刺激(人的感覺器官)”是由義項1引申來的,如,“這洋蔥辣得他眼淚直流。”表示刺激性氣體刺激了眼睛引起了某種生理反應,這里的“辣”指向觸覺域。義項3“刺激性畫面使人難以直視”是在義項2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這畫面辣眼睛。”表示畫面太丑,視覺上受到了沖擊。此處的“辣眼睛”不同于義項2的“辣眼睛”,這里的“辣”是畫面刺激而非氣體刺激。但由于它們所引起的生理感覺上的不適感相似,“辣”由觸覺域投射到了視覺域。
由于“辣”本質上是一種烈性痛感,使人感到不適,人們通過聯想和比附,又使它獲得了“暴躁、兇悍”的引申義,表示消極情緒或性格,實現了從觸覺域向情感域的投射。但“辣”也可以表示積極性格,用來形容“性格直爽的人”,如四川人所講的“辣妹子”,表示此人說話爽朗直接,讓人痛快。“辣”產生了“直爽、坦率”的引申義,這種引申關系還存在著生理基礎。研究表明,人體會為了平衡辣味帶來的痛苦,自動分泌內啡肽,這種類似嗎啡的物質會給人帶來痛快酣暢感,久而久之,人們便將酣暢感與辣聯系起來,并進一步歸納出“直爽、坦率”義,從生理移位到心理,完成詞義的隱喻轉義。
“辣”較為獨特的一點是它還可以表指稱,“辣子”可以指稱“厲害不好惹的人”。如:
(14)“他是我們這里有名的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
“潑辣貨”、“辣子”、“鳳辣子”這里都是指“鳳姐”,鳳姐喜歡爭強斗志,性格跋扈,無人敢惹,與“辣”在特定的視角下所表現出來了一種內在相似性,因此能夠對應起來,實現了從觸覺域向指稱域的投射。
當“辣”對人的味覺及人體各部位的刺激過于強烈時,往往使人渾身冒汗,產生燥熱、火熱的感覺。而夏季高溫天氣出現時,常常會給人帶來同樣的感覺體驗。此時,人們便會聯想起吃“辣”的感覺,實現“辣”的隱喻轉義,產生“酷熱”義。
綜上所說,通感隱喻中,從基本認知域到復雜認知域的投射主要是指從觸覺、嗅覺、味覺到聽覺和視覺的投射。觸覺、味覺、嗅覺屬于低級的感官,聽覺和視覺屬于較高級的感官。盡管通感發生在不同層次的認知域之間,但是它們都遵循著從低到高的規律。
三、對于詞義通感隱喻式引申的思考
詞義的擴展與人的通感具有密切的關系,正是由于感官上的互通有余,我們的語言才更具有豐富性、簡約性、生動性,以致人們時常用味覺詞的詞義來表達對事物的看法與評價,這也是各個國家、不同民族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
但是同一詞語,由于不同民族的思維特征及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會引申出不同的意義,比如,韓語中的“酸”可以用于指光線太足,從而引申出“耀眼”義,漢語中無對應用法。日語中的“甜”可以用于指一個人思維不靈敏,引申出“笨、遲鈍”義,這種用法在漢語中同樣沒有對應表達。所以,對于詞義通感隱喻式引申的研究,對于克服語際交流障礙,促進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通,以及對外漢語詞匯教學與修辭教學,都具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