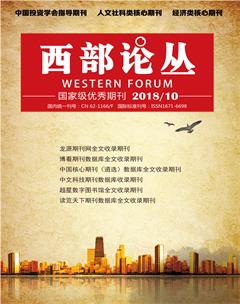從行為主義到認(rèn)知主義
摘 要:錢(qián)夢(mèng)龍老師的語(yǔ)文教學(xué)理念,以“三主”、“四式”為中心,實(shí)現(xiàn)了語(yǔ)文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中由行為主義學(xué)習(xí)導(dǎo)向向認(rèn)知主義的轉(zhuǎn)變,并且在這一過(guò)程中,對(duì)語(yǔ)文閱讀的目的、老師功能的定義以及學(xué)生自我價(jià)值確立等方面都進(jìn)行了重估,顛覆了以往語(yǔ)文教學(xué)中的既定模式,對(duì)于當(dāng)前語(yǔ)文教育提供了諸多思考和研究空間。通過(guò)對(duì)于錢(qián)夢(mèng)龍老師語(yǔ)文導(dǎo)讀論的再分析,也可以對(duì)當(dāng)前教育改革提供更加深刻的啟示。
關(guān)鍵詞:錢(qián)夢(mèng)龍 導(dǎo)讀論 認(rèn)知主義 三主 四式
一、當(dāng)前語(yǔ)文教育中的行為主義學(xué)習(xí)困境
在當(dāng)前的語(yǔ)文教學(xué)中,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的“三主”、“四式”理論,即以學(xué)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dǎo),以訓(xùn)練為主線(xiàn),以及自讀式、教讀式、練習(xí)式、復(fù)讀式的教學(xué)模式開(kāi)創(chuàng)了對(duì)于語(yǔ)文教育的新認(rèn)知。此外,通過(guò)錢(qián)先生語(yǔ)文教學(xué)理念不斷收到追捧這一現(xiàn)象,就不難看出當(dāng)前的語(yǔ)文教學(xué)并未走出傳統(tǒng)模式的藩籬,克服和超越行為主義學(xué)習(xí)方式的桎梏。
行為主義學(xué)習(xí)觀(guān),最早是由斯金納(Skinner)等學(xué)者開(kāi)創(chuàng)的,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是“一種與心智或內(nèi)在思維過(guò)程幾乎沒(méi)有任何實(shí)質(zhì)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yàn)所引起的行為變化”[1],是由前因和后果的變化相對(duì)決定的。從行為主義的視角出發(fā),行為所造成的結(jié)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為重復(fù)發(fā)生的可能性,并進(jìn)而把行為的結(jié)果區(qū)分為強(qiáng)化性行為和懲罰性行為。這兩種結(jié)果作為經(jīng)典(或傳統(tǒng))教育模式的適用原則,多年來(lái)在我國(guó)的語(yǔ)文教學(xué)中被奉為圭臬。因此在教學(xué)目標(biāo)的設(shè)定上,也多以教師作為評(píng)判者來(lái)確定學(xué)生學(xué)習(xí)目標(biāo)的達(dá)成,如羅伯特·馬杰(Robert Mager)將一個(gè)良好教育的目標(biāo)分為三個(gè)部分:①目標(biāo)應(yīng)描述預(yù)期的學(xué)生行為;②羅列行為發(fā)生的各種條件;③給出行為可接受的標(biāo)準(zhǔn)。[2]
這些框架在當(dāng)前的語(yǔ)文教育中仍普遍存在,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兩個(gè)方面加以分析。
(一)強(qiáng)化式的機(jī)械重復(fù)
強(qiáng)化式的機(jī)械重復(fù),著眼于對(duì)行為結(jié)果的重視,通過(guò)對(duì)行為強(qiáng)化以達(dá)到預(yù)期的目標(biāo)。具體而言,主要體現(xiàn)在學(xué)校教學(xué)中的題海戰(zhàn)術(shù),即通過(guò)大量練習(xí)題的訓(xùn)練,提高學(xué)生應(yīng)對(duì)各種題型的能力。但是這種強(qiáng)化并不單單只是停留在結(jié)果層面的指向,對(duì)于能夠加強(qiáng)行為并獲得預(yù)期目標(biāo)的刺激行為,也可以視為強(qiáng)化功能的一部分,即激勵(lì)手段。
首先來(lái)看一下作為經(jīng)驗(yàn)性(Empiricism)的語(yǔ)文教學(xué)模式中,行為主義的強(qiáng)化機(jī)制是如何發(fā)生作用和造成結(jié)果的。在過(guò)程強(qiáng)化階段,背誦、默寫(xiě)、抄題等傳統(tǒng)的強(qiáng)化方式,在基礎(chǔ)教育資源分布不夠平均的當(dāng)下,仍占據(jù)語(yǔ)文課堂的主流。而這種方式能夠被廣泛并長(zhǎng)期使用,原因在于明確目的指向能夠獲得明確預(yù)期結(jié)果(至少在行為主義的觀(guān)點(diǎn)下是如此),并且在這種強(qiáng)化方式下,對(duì)于教師群體的專(zhuān)業(yè)素養(yǎng)要求較低,可以節(jié)省教育成本。因此所得到的結(jié)果是,通過(guò)這種強(qiáng)化手段,學(xué)生作為考試目的的語(yǔ)文學(xué)習(xí)達(dá)到了考核標(biāo)準(zhǔn),但卻與作為教學(xué)的語(yǔ)文學(xué)習(xí)理念相差甚遠(yuǎn),甚至在枯燥的重復(fù)之中對(duì)語(yǔ)文心生厭惡。這在語(yǔ)文教學(xué)中是得不償失的。
此外,以行為過(guò)程為導(dǎo)向的激勵(lì),在具體實(shí)施的過(guò)程中由于前文提到的經(jīng)典行為主義教育觀(guān)念的影響,也常常會(huì)出現(xiàn)矯枉過(guò)正的現(xiàn)象,因此對(duì)于激勵(lì)手段的選擇也存在諸多問(wèn)題。舉例而言,當(dāng)前學(xué)校中普遍存在的考試排名現(xiàn)象,美其名曰讓學(xué)生明白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差距,并且對(duì)排名靠前的學(xué)生也是一種鼓勵(lì)。但是這種粗糙的鼓勵(lì)方式往往帶來(lái)更多的問(wèn)題,如造成學(xué)生相處的間隙,忽略學(xué)生間的差異等。以上這些特征都是由于行為主義的學(xué)習(xí)觀(guān)念直接的功利性質(zhì)所導(dǎo)致的,而錢(qián)夢(mèng)龍老師的語(yǔ)文教學(xué)理念正是針對(duì)上述問(wèn)題做出了諸多調(diào)整,下文將詳細(xì)論述。
(二)懲罰式的負(fù)面導(dǎo)向
與強(qiáng)化行為相對(duì)應(yīng)的,對(duì)于達(dá)不到老師所定制的預(yù)期教育目標(biāo)的對(duì)象,懲罰式的導(dǎo)向?qū)?huì)以粗暴的手段發(fā)生作用。在當(dāng)前的教育改革中,懲罰作為一種不提倡的教育方式,往往會(huì)引起學(xué)生的抵抗情緒,帶來(lái)新的問(wèn)題。但是通過(guò)當(dāng)前的教育實(shí)踐反饋不難發(fā)現(xiàn),懲罰措施的受限會(huì)消弭教師與學(xué)生之間的身份差距,卻并不會(huì)為師生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關(guān)系。在著眼于預(yù)期目標(biāo)的懲罰舉措中,首先忽略了標(biāo)準(zhǔn)制定者的合理性。當(dāng)教師作為標(biāo)準(zhǔn)的制定者,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學(xué)生主體性特點(diǎn);其次,懲罰作為手段,如果只以學(xué)生的行為目標(biāo)為考量,就會(huì)造成懲罰措施濫用,更加加劇了學(xué)生與老師身份的對(duì)立;再者,當(dāng)懲罰達(dá)不到老師要求的目標(biāo)時(shí),就會(huì)形成加劇的惡性循環(huán);最后,懲罰手段也趨于簡(jiǎn)單粗暴,難以強(qiáng)化行動(dòng)過(guò)程。在此基礎(chǔ)上,錢(qián)夢(mèng)龍老師所提出的“三主”理念,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這一弊端。
二、錢(qián)夢(mèng)龍導(dǎo)讀法的認(rèn)知主義轉(zhuǎn)向
錢(qián)夢(mèng)龍老師“三導(dǎo)”、“四式”語(yǔ)文教學(xué)思想的提出,標(biāo)志著以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為代表的新型語(yǔ)文教學(xué)觀(guān)念,完成了從行為主義到認(rèn)知主義的轉(zhuǎn)型。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從閱讀方式、教師功能、學(xué)生價(jià)值三個(gè)方面重新構(gòu)建了語(yǔ)文教學(xué)觀(guān)念,在價(jià)值理念的層面上顛覆了傳統(tǒng)語(yǔ)文教學(xué)中的問(wèn)題,對(duì)解決當(dāng)前的語(yǔ)文教學(xué)困境提供了新的解決策略。
認(rèn)知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是一種積極的心智過(guò)程,區(qū)分了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的普適性知識(shí)(general knowledge)和專(zhuān)門(mén)化知識(shí)(domain-specific knowledge),強(qiáng)調(diào)教師不僅要很好地運(yùn)用行為理論,還要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融入有效的認(rèn)知方法。而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的導(dǎo)讀法就是這種認(rèn)知主義教育方式的體現(xiàn)。具體而言,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對(duì)傳統(tǒng)行為主義教學(xué)觀(guān)念的顛覆,主要從以下三個(gè)方面展開(kāi)。
(一)認(rèn)知主義觀(guān)照下的語(yǔ)文閱讀
對(duì)于傳統(tǒng)的語(yǔ)文教學(xué)活動(dòng)而言,閱讀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塊,但是在具體的教學(xué)情境中,語(yǔ)文老師對(duì)于閱讀把握和理解的程度卻有所差異。對(duì)于語(yǔ)文閱讀的理解,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將之概括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tǒng)一”[3],但實(shí)際情況是,或出于功利性的考量、或出于教師理念更新的速率存在偏差,“人文性”的概念或多或少缺失。如果從認(rèn)知主義角度加以考量,人文性是語(yǔ)文閱讀體驗(yàn)的經(jīng)驗(yàn)性?xún)?nèi)容,而工具性則通過(guò)認(rèn)知角度,將語(yǔ)文學(xué)習(xí)中逐漸熟知的知識(shí)加以靈活運(yùn)用的能力。
在傳統(tǒng)的功利性課堂上,語(yǔ)文閱讀往往最容易被忽視,常常有老師將課文拆解成獨(dú)立的表意單元,然后展開(kāi)句理分析,割裂了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tǒng)一,學(xué)生的閱讀體驗(yàn)淪落為對(duì)句子的學(xué)習(xí)和理解。而最理想的語(yǔ)文教學(xué)途徑,應(yīng)當(dāng)是像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一般,由閱讀入手開(kāi)始認(rèn)知與能力的架構(gòu),即“以訓(xùn)練為主線(xiàn)”。
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認(rèn)為,訓(xùn)練是達(dá)成語(yǔ)文學(xué)習(xí)能力和提高語(yǔ)文素養(yǎng)的必經(jīng)之路,它不是單純的練習(xí)、不是題海戰(zhàn)術(shù),也不是簡(jiǎn)單的言語(yǔ)實(shí)踐,而是要在訓(xùn)練的過(guò)程中感知母語(yǔ)語(yǔ)文文字的魅力,以及其中所蘊(yùn)含的人文理念。這種由認(rèn)知到能力的語(yǔ)文閱讀學(xué)習(xí)路徑,可以看作是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與認(rèn)知主義學(xué)習(xí)觀(guān)念的遙契。
(二)教師功能的再建構(gòu)
對(duì)于語(yǔ)文老師在語(yǔ)文教學(xué)中的作用,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將之概括為“以教師為主導(dǎo)”。導(dǎo),即引導(dǎo),意為把握方向。這里的方向既課堂走向,又是對(duì)學(xué)生的導(dǎo)向。這一觀(guān)點(diǎn)的提出,旨在消解傳統(tǒng)課堂中老師定于一尊的崇高地位,將教師的功能,由知識(shí)的轉(zhuǎn)運(yùn)轉(zhuǎn)向?qū)W(xué)生能力的建構(gòu)。以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的《死海不死》課堂教學(xué)實(shí)踐為例,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將提問(wèn)作為引導(dǎo)學(xué)生回答和思考的核心方式,在學(xué)生思路屢次受阻的情況下,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通過(guò)將學(xué)生不熟悉的知識(shí)(說(shuō)明文的概念)引導(dǎo)至學(xué)生已有的認(rèn)知范圍中(對(duì)知識(shí)小品的模糊認(rèn)知),并成功總結(jié)出知識(shí)小品特點(diǎn)。并且在這一過(guò)程中,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的提問(wèn)始終帶動(dòng)課堂節(jié)奏,把握學(xué)生思考方向,卻又沒(méi)有以教師的身份權(quán)威去影響學(xué)生對(duì)自己知識(shí)認(rèn)知的自信。此外,對(duì)于被提問(wèn)的學(xué)生而言,他既是問(wèn)題的回答者,又是答案的制造者,這種雙重身份帶來(lái)的是對(duì)自我認(rèn)知的再確認(rèn),成功的將認(rèn)知轉(zhuǎn)化為描述答案的能力,這一點(diǎn)也是認(rèn)知主義的學(xué)習(xí)觀(guān)念所強(qiáng)調(diào)的對(duì)于學(xué)生的指導(dǎo)和對(duì)已有知識(shí)的把握。
(三)學(xué)生身份的重估
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對(duì)傳統(tǒng)課堂中像學(xué)生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進(jìn)行重估,這一點(diǎn)主要通過(guò)“以學(xué)生為主體”來(lái)實(shí)現(xiàn)。其顛覆以往語(yǔ)文課堂中教師中心主義的狀況,學(xué)生做為教育的目標(biāo),自然也應(yīng)該把學(xué)生作為教學(xué)環(huán)境、課程設(shè)計(jì)等內(nèi)容的核心要素,以學(xué)生為主體的理念正是在這一邏輯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闡發(fā)。
從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來(lái)看,教師和學(xué)生的主體地位隨著教學(xué)環(huán)境和教學(xué)內(nèi)容的變化,相對(duì)的會(huì)發(fā)生調(diào)整。但是從認(rèn)知主義學(xué)習(xí)觀(guān)念的角度加以考量,學(xué)生作為認(rèn)知的主題,所有認(rèn)知環(huán)境都應(yīng)還以學(xué)生為中心加以塑造。此外,加之教師作為教學(xué)過(guò)程中的主導(dǎo)因素,“滿(mǎn)堂灌”式的教學(xué)方式并不能很好的契合學(xué)生之間對(duì)課堂內(nèi)容的不同接受狀況,因此以學(xué)生為主體的理念,也是充分考量了學(xué)生之間的差異而提出的有效措施,可以更好的暴露學(xué)生對(duì)于教育內(nèi)容中所存在的困惑和問(wèn)題,有利于提高教學(xué)的效率。
綜上所述,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的認(rèn)知主義轉(zhuǎn)向,從教與學(xué)、教師功能與學(xué)生身份,語(yǔ)文教學(xué)中閱讀的功能與目的等方面,對(duì)當(dāng)前語(yǔ)文教學(xué)中存在的問(wèn)題進(jìn)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應(yīng)的解決策略,對(duì)當(dāng)前語(yǔ)文老師的課堂實(shí)踐提供了啟發(fā)。語(yǔ)文訓(xùn)練是培養(yǎng)學(xué)生語(yǔ)文能力的必然途徑,這也是新世紀(jì)對(duì)我們語(yǔ)文工作者的呼喚,生動(dòng)活潑的、高效的語(yǔ)文教學(xué)訓(xùn)練形式,能使我們更好地完成語(yǔ)文教學(xué)的根本任務(wù)。
參考文獻(xiàn):
[1] [美]韋恩·K.霍伊,塞西爾·G.米斯克爾《教育管理學(xué):理論·研究·實(shí)踐》,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15.
[2] Mager,Preparing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Palo Alto,CA:Fearon.
[3] 何郁,《用正確的訓(xùn)練提升語(yǔ)文學(xué)習(xí)能力——錢(qián)夢(mèng)龍先生訪(fǎng)問(wèn)錄》,教研天地,2005.
作者簡(jiǎn)介:楊思蒙(1993-),女,蒙古族,陜西西安,碩士在讀,單位:陜西師范大學(xué),研究方向:學(xué)科教學(xué)(語(y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