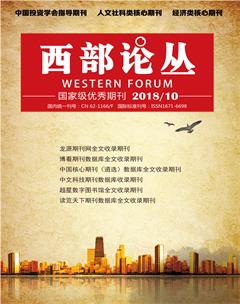簡論石濤“筆墨當隨時代”
趙冬子
“筆墨當隨時代,猶詩文風氣所轉。”單品這句話,石濤是在表述書畫的筆墨應當與時俱進,不斷開拓。然而該句出處的原畫跋,又表露出了“恐無復佳矣”這樣厚古薄今,覺得書畫和詩文一樣都在逐漸衰退的意思。石濤本意究竟如何,在他其他一些的文字表述中,還有頗多自相矛盾,難以自圓的現(xiàn)象,顯得對這個問題的思辯撲朔迷離。所以本篇小文,不在于探究石濤寫下這句話的初心,而想就其字面意思進行一些解讀。
一、“筆墨”的意涵是什么
筆墨是中國畫的基本技法和單位,也是最本初的形式。然而在本文所要論述的“現(xiàn)實意義”當中,筆墨則有另一種重要的文化可能。筆墨是一種文人的精神氣息,一位畫師,是通過筆觸來表達出自己內(nèi)心的態(tài)度、情緒的。不論是否帶著明顯的主觀表達(例如一定把魚鳥畫成“白眼看青天”),即使只是一副普通的山水冊頁,在樹木山石的疏密之間,也會流露出一種藝術精神。這種態(tài)度,和石濤所說的隨著朝代興衰,在詩文精神氣質上的反映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作者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自由發(fā)出強有力的呼聲時(石濤語“我自用我法。”),也不得不承認,這種自由,還是無法跳脫出歷史背景的。
那么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既然我們對“時代當下”的背景前提如此在意,那么我們的表達將對其有何作用呢?這在石濤的另一句廣為人知的又號“借古以開今”中給出了答案,和唐代韓、柳領導的古文運動一樣,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順從時代,才能做到“化古為新”“古為今用”,開創(chuàng)一代新風。另外需要捋清的是,單純以時間順序將時代分為“新舊”是不那么妥當?shù)摹v史有時像一種循環(huán),在曲折中前進上升。站在這種史觀上,能幫助我們更好認識為什么要通過“復古”來“出新”的這種動機。
二、如何“隨”時代
石濤的個人經(jīng)歷,和四僧當中的朱耷相仿,都是前朝的遺族。這種背景使得他們有著相同的心態(tài),對于過去的東西既向往,又回避。向往是因為曾經(jīng)的歷史懷藏著整個家族乃至民族更欣榮豐盛的美好回憶,但是這種回憶,又會帶來對現(xiàn)實反照的蟄痛,使得他們不斷提醒自己要和過去保持距離。這樣的個人經(jīng)歷,給這些清初畫家的藝術風格注入了一種冷僻、獨立的藝術氣質,他們以自己的筆觸做出了自己對時代態(tài)度的答卷。古代的畫家和散文家不同,他們是離廟堂更遠的隱士,對于社會政治現(xiàn)狀,既沒有一言興邦的野心,也沒有得君行道的途徑。所以在畫卷上所展開的,只能是對時代脈搏的“隨”,而不是“引”或“領”。
然而正是這種“隨”的態(tài)度,恰好在“繪畫”這種藝術形式中,找到了對于現(xiàn)實和藝術的微妙平衡。畫作即是對實物的刻畫,卻并非“還原”,而是藝術的再現(xiàn)。“時代”這種字眼,總會使人蒙蔽地覺得,對客觀環(huán)境的把握是創(chuàng)作的訣竅。其實法門恰恰相反,是因為創(chuàng)作者有了不同于前人的經(jīng)歷、才造就了另一種心境,再由此想要做出不同的表達,這完全是由內(nèi)到外的一種噴薄。沒有內(nèi)心的變化,縱使跟隨著當下的新風氣去做新的事物,也只是一種無意義的盲從。
三、筆墨在時代中的回響
石濤的這句話能夠廣為流傳,是因為他捕捉到了某種歷史規(guī)律。石濤以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作證明了自己沒有淹沒在歷史當中,當然他也絕非以一個完全逆流而上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現(xiàn),我更愿意把他想做劃著一葉扁舟,在浩渺江水中找到一灣蘆葦蕩,或是一處桃花源,然后成全了自己的位置。
在石濤最初援引的例子里,“中古之畫,如初盛唐之句,雄渾壯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辯證案例。提到盛唐,總使人心中浮現(xiàn)出無數(shù)瑰麗的詩句。然而到底是盛唐造就了這些詩句,還是這些詩句裝點了盛唐呢,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對立又統(tǒng)一的問題。盛唐的時代背景為唐詩提供了土壤,唐詩是在上面長出的閬草仙葩。如果不是花草,我們也不會注意到這下面的土地。
以每個人從自身看時代,總會將自己和時代割裂開來,我們企圖和這個時代對話,好像我們自己不是當下的一份子。然而所有當下的東西,在下一秒到來之前,就又都成為了歷史。這種前后都無法著顧的空虛和焦慮,被那些經(jīng)歷過時代更替的遺民們一早深刻地體察到了。歷史的汪洋中,人如浮萍飄絮,無法決定自己的去向,好在藝術是自由的,我們不必照著任何規(guī)矩定論來下筆著墨。所謂的“筆墨當隨時代”,即是筆墨可以比人更早走一步,只有未來的可能,才是時代,而其他的都只是不同的歷史。“筆墨”的精神意義正在于此,一切尚未被定義的才能稱之為時代,這也就為一種新的精神態(tài)度提供了空間。
正是因為石濤能夠在時代中留下了自己的注腳,我們至今還能聽到他清澈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