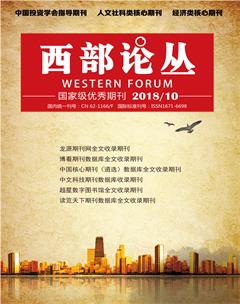道德話語與政治話語的關系之思
都東平
摘 要:漢納·皮特金曾提出道德話語與政治話語的區分,而對這兩種話語的關系之思考可以讓我們加深對這兩種話語的理解,從而允許政治哲學、倫理學或道德哲學以一種更加契合的方式施加對政治的規范。本文通過分析羅爾斯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墨菲的“激進民主”中蘊含的兩種話語的關系,揭示政治話語內在的政治向度、道德話語對其的忽視,從而反思這兩種話語之間應有的關系。
關鍵詞:道德話語 政治話語
漢納·皮特金曾在其著作《維特根斯坦與正義》一書中,將道德話語與政治話語之間作出了如下區分:“道德話語是個人的對話,政治話語關涉公眾、共同體,并且一般地總是發生在成員之間……離開了相互抗衡的主張和利益之間的沖突,政治領域就沒有了主題;就無需做什么政治決策。”我們將從這個角度,觀察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M.桑德爾等人的社群主義政治哲學和對他們的批判。
羅爾斯:個人道德語言替代政治語言
羅爾斯認為,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目標在于提出“正義的一個政治觀念,它不僅要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合法化提供一種公平的公共基礎,而且還要有助于確保代代相沿的穩定性。”搭建這種“公共基礎”“穩定性”的基石,應該由個人對一種政治的重疊共識來建立。在這里,羅爾斯以 “康德式構造主義”的方式建立個人:個人同時服從關照個人利益的理性、和關照道德、社會合作的合理性;由此,個人被視為理性的道德人。
社群主義者揭示出了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政治主體背后的個人主義邏輯,并批評這種抽象的、理性化的個人主體遺忘了政治和群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因而不能建構出處于共同體之中的、參與共同體政治的形象;
而施米特認為,純粹、嚴格的個人自由主義原則不能產生任何政治概念,因為個人主義要求個人必須是起點和終點,從而在實際的政治層面上“出現了一種自由政策。它以愛爭論的、對立的形式反對政府、教會或其他束縛個體自由的機構、制度”(可以聯想到許多美國喜劇中對政府的抨擊、不信任、諷刺挖苦已然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這背后“不是一種自由政治學,只是對政治學的一種自由批判”。因而對于施米特,自由概念只是在倫理學和經濟學之間徘徊(這與羅爾斯的“康德式構造主義”恰相對應),但唯獨回避了政治。結合前述的社群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所使用的是一套個人的而非群體的、道德的而非政治的話語。
社群主義:以群體道德語言替代政治語言
社群主義者從自由主義的“權利先于善”走向了“善先于權利”,并且這一轉向和市民共和主義結合在了一起:這種結合強調積極參與政治的“市民德性”以及圍繞這種“市民德性”所建立的共同體所共同分享的“共同善”。“共同善”指向了共同體內的道德次序,在其之上才能建立共同體、政治、個人權利等范疇和概念。而“市民德性”最早源于亞里士多德對人作為“政治動物”的界定,其中個人的善和城邦的善的統一性直接支持了后來市民共和主義中的市民政治參與對于個人的至高重要性。
墨菲卻指出了這背后蘊含的道德話語。墨菲在社群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對于“權利先于善”和“善先于權利”的無休止的“兩難”間發現,他們兩方已然都混淆了兩種善:實質性的道德善和制度性的政治善——前者標識的是個人的自由、權利的底線,而后者是民主政治的底線。自由主義者將兩種善都試圖劃入私人并對其中立,因而取消了政治的公共維度,只能從個人出發并回到個人;社群主義者則將兩種善都置于公共領域,因而忽視了個人的權利,不分公私。同時,社群主義所建立的實質性的、同一性的共同體,和自由主義的理性個人一樣,沒有為共同體內部的沖突性留下空間(因而內部沖突很可能被極端化,如反對者被描述為“民族的敵人”),因而只是以群體的而非個人的道德話語代替了政治話語。
墨菲式的分離:是否超越了當前矛盾?
墨菲通過分離實質性的道德善和制度性的政治善,間接分離了道德語言和政治語言;但是,這種間接分離是否成功?
墨菲自己的政治主體便是在以兩種善的分離為前提下建立的:它認同共和主義是政治應有的規則。這里的“政治應有的規則”是指這樣的行為規則、前提,即必須把其他人看成自由和平等的人(政治善),而不論這一行為有任何具體的、實質的目的(道德善)。墨菲鼓勵以這一標準重塑政治主體的“斗爭性”,以此劃清認同這一概念的“我們”和不認同的“他們”。但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政治主體的觀念,在身份政治的觀念市場里其實是很無力的:共和主義本身已充滿爭議,而這種爭議在普通民眾看來是十分專業化的,相比“民族”、“種族”、“階級”、“宗教”就已是抽象的、學術的、不直接的。因而這一“斗爭”似乎成了學者間的斗爭,而其期待的圍繞共和主義的“團結”似乎也與民眾絕緣。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墨菲分離政治善與道德善時,她卻未能在重提“斗爭”時,支撐起“團結”的概念,這一“團結”在民主革命時,曾被個人道德話語所吸納,以“平等”“博愛”為名會聚起革命者,也曾在民族獨立時,被群體道德話語所采用,以“解放”為名召集起獨立軍,從而將道德話語政治化。政治話語的兩個重要向度在這里顯現:個人—群體、斗爭—團結,任何一種偏向這兩個向度中的一極的話語似乎都將趨向道德話語:當今的自由主義忽視群體與斗爭、社群主義忽視個人與斗爭,而墨菲的共和主義忽視了團結,它們都最終成為了道德話語。
可以這樣說,“分離”“代替”都不能很好地被確立為道德話語和政治話語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在“分離”“代替”視域下的兩種話語之間的關系,本身就失去了政治的某種向度,本身便是以道德話語展開的,因而對具體的政治實踐而言可能過于抽象與理想化。政治哲學、倫理學或是道德哲學固然不會滿足于對政治的純粹的“實然描述”;但沉迷于忽視了政治向度的道德話語,卻也不利于其本身所期待的對政治的規范、約束;尤其是當時代的問題正召喚智慧、思考時,如何讓道德話語更有效地介入政治,是極為重要的。
參考文獻:
[1] 漢納·皮特金.維特根斯坦與正義[M].貝克萊. 1972, P216
[2] 羅爾斯.一種重疊共識理念[J]. 牛津法律研究.1987(7) 第一期:P12.
[3] 羅爾斯.道德理論中的康德式構造主義.[J].Philosophy. Vol.77, 1980(9), 第九期
[4]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 Rutgers,1971,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