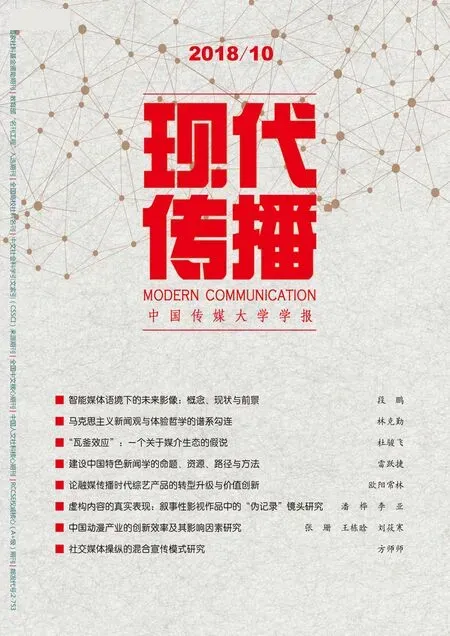點贊行為的代際差異研究
■ 陳素白 邵 舒
一、研究背景
社交媒體的飛速發展不斷改變著受眾的娛樂及交流方式。伴隨社交功能便捷化、快速化的趨勢,“點贊”已經成為數字化溝通的重要途徑。①2009年,Facebook在其頁面中加入“Like”按鈕,受眾通過其表達對相關內容“喜愛”“支持”等正面情緒。之后“Like”被國內社交類、視頻類網站紛紛引入并設定為“點贊”功能。截至2018年6月,我國8.02億網民中,微信朋友圈的使用率達到86.9%。②作為一種新型溝通方式,“點贊”使快捷的情感表達成為現實。③事實上,“點贊”功能間接導致文字評論大幅減少,使受眾的溝通趨于淺層化和不確定;“點贊”的過度使用可能使其偏離了初始含義④,給許多災難和悲劇等負面內容“點贊”表現出受眾對媒介初始含義的反叛和解構。因此,關于“點贊”的傳播學新現象引發了人們對于“媒介如何影響人”這一命題的深刻反思。
目前媒介環境相關研究主要有“新舊媒介技術的研究/比較”“媒介環境對受眾社會化的作用”等。其中在“媒介環境對受眾社會化的作用”范疇下,研究多以受眾在各大媒介平臺/技術(如報紙、電視、手機、Facebook、微博等)的活動情況為研究對象,分析受眾對媒介平臺/技術的差異化表現。擬通過細微的“點贊”功能探究受眾媒介使用的差異化表現,剖析媒介環境對受眾的改造作用。
基于微信朋友圈“點贊”功能,以“70后”“90后”用戶為研究對象,擬通過實證研究探索不同媒介時代背景下的受眾媒介使用行為差異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意義:其一,目前國內學者對于媒介接觸與使用的研究傾向于關注同一時態背景中不同社會成員接觸媒介的狀況,而通過將新媒介功能的考察置于媒介環境學背景下,微信“點贊”行為研究實現了從單一時間維度到代際層面的延伸。其二,調查數據可為新媒介功能的優化和受眾體驗感的增強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二、研究問題及假設
媒介技術的快速更新使得以媒介發展史為尺,將受眾劃分為不同群代成為可能。馬克·波斯特指出電子媒介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大眾的交流習慣,據此他將媒介時代一分為二:播放型傳播模式盛行的大眾媒介時代為“第一媒介時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和衛星技術與電視、電腦和電話結合形成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二媒介時代”。⑤邁克·普倫斯基進一步將出生和成長于不同媒介時代的受眾定義為數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數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⑥,前者是與網絡技術同時誕生和成長的一代,后者則是從傳統媒介使用逐漸邁向互聯網使用的一代。
經文獻梳理可知,媒介代際研究與不同群代間青少年成長期所接觸的媒介密切相關。我國互聯網時代始于1994年,結合波斯特的觀點,可以大致確定1994年之前為“第一媒介時代”,1994年之后為“第二媒介時代”。因此研究選取社會學標準界定的“70后”與“90后”為研究對象,而非精準的時間裁定標準。“70后”指成長于第一媒介時代,青少年時期受收音機、報紙等缺少互動和反饋機制的傳統媒介影響較大,大約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一代人;“90后”指成長于第二媒介時代,青少年時期與互聯網的興起時期相吻合,約為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
(一)“點贊”動機研究
在前人的研究中,社交動機、實用動機和娛樂動機被證實為“點贊”的重要動機。由于“點贊”人群的異質性不斷增強,一些偏離設計者初衷的“點贊”意義被深度挖掘。“非言語溝通”、網絡社交圈的“敷衍工具”⑦、習慣性“點贊”⑧成為新媒體時代的全新文化現象。綜上可知,在不斷變動的媒體環境和受眾心理下,微信“點贊”動機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點贊”的動機應當被重新審視。
RQ1:“70后”和“90后”微信受眾的“點贊”動機是什么?
RQ2:社交溝通作為“點贊”的重要動機,“70后”和“90后”在使用微信“點贊”進行溝通時是否存在差異?
H1:溝通是“70后”和“90后”“點贊”的首要動機。
H2:“70后”與“90后”“點贊”溝通的實質存在差異。
H2.1:“70后”傾向于通過“點贊”增進溝通。
H2.2:“90后”傾向于通過“點贊”回避溝通。
(二)“點贊”內涵研究
“點贊”作為一種虛擬認可,對受眾意味著什么樣的含義鮮為人知。⑨同時伴隨著朋友圈內容的多樣化、受眾年齡的分層化、對象的多元化,受眾對于“點贊”內涵的理解逐漸偏離其初始含義。有研究表明年齡對于“點贊”行為具有顯著影響。⑩同時伴隨著大量網絡熱詞的出現,個性化的自我表達成為常態,以“90后”為代表的非主流一代正在迅速崛起,“90后”對于網絡文化的理解和使用更為靈活,如“點贊”已衍生出“朕已閱”“嗨,你好”“支持”“調侃悲傷”等各類曖昧意味。
RQ3:“70后”和“90后”微信受眾對于“點贊”內涵的理解是否存在差異?
H3:“70后”和“90后”對“點贊”內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差異。
H3.1:“70后”傾向于使用“喜歡”“支持”等“點贊”的初始含義。
H3.2:除“點贊”初始含義外,“90后”會延伸使用“點贊”含義,如“調侃”“揶揄”。
(三)“點贊”對象
隨著網絡社交常態化,現實人際延伸到線上的情況不在少數。經過文獻研究發現,針對不同的“點贊”對象時(如朋友、品牌或機構等)行為存在差異。
RQ4:就好友發表的朋友圈內容而言,“70后”和“90后”的“點贊”對象是否存在差異?
H4:從親疏程度考慮,“70后”與“90后”的“點贊”對象存在差異。
三、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分為兩步:第一步,對4個方便樣本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訪談對象均來自廈門,其中 “70后”及“90后”各2名,詢問其互聯網及“點贊”使用情況,綜合文獻和訪談結果,編制預試問卷。第二步,通過深度訪談探究差異的具體表征及其成因。
(一)問卷設計
本文從“點贊”動機、內涵和對象三個層面,由內而外考察“70后”“90后”在“點贊”動機和行為上的異同,以此研究媒介環境對受眾的影響,研究框架如圖1。

圖1 研究框架與假設
“點贊”動機的考察細分為“點贊”動因和溝通實質兩個維度。參考既有社交網絡使用動機研究,將“點贊”動機劃分為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外在因素主要起激勵作用,包括“內容”“發布對象與自己的關系程度”“商業激勵”“群體壓力”“潮流趨勢”等;“點贊”的內在因素起決定性作用,包括“維系人際關系”“自我表達”“溝通交流”“回避深層次溝通”“關心和支持他人”“尋求回贊”和“體現自我和品味”。
“點贊”溝通實質和內涵的測量均采用李克特七級量表,1分到7分遞增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從傳者和受者雙重角度進行考察。“點贊”溝通的實質即受眾使用“點贊”傾向于增進或回避溝通;“點贊”的內涵著重測量受眾“點贊”多用于表達正面或負面態度。為加強受訪者填答時的代入感,該部分題目包含部分的情景模擬題,諸如“以下哪一條微信朋友圈的狀態您最有可能點贊”等。
“點贊”對象的考察主要依據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絡強弱連接原理,將“點贊”對象按連接從強到弱依次劃分為六類:關系很好、關系較好、關系一般、點頭之交、陌生和其他六個梯度。
(二)問卷信度
本研究預調查階段共選取30名方便樣本進行預調查,15名“90后”樣本來自廈門大學在讀生,15名“70后”樣本均來自中山大學。根據試測數據對問卷進行調整,修正過后問卷各部分Cronbach α值均大于0.736。正式問卷調查中,問卷總體Cronbach α值為0.938,信度較為理想。
(三)深度訪談提綱設計
參照調查問卷的結構和維度,本研究深訪提綱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受眾“點贊”使用情況,包括起始時間、日均頻率和常用“點贊”平臺等信息;第二部分則以開放式問題就受眾對“點贊”的認知、理解和行為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究。
預訪階段采用判斷抽樣的方式,選取微信黏著度較高的“70后”和“90后”樣本各2名,預訪談結束后就提綱表述不明和需補充的部分進行完善,形成正式提綱。
四、研究結果
(一)問卷數量及樣本結構
經預調查發現,“點贊”在“70后”群體中普及度略低,因此在抽樣過程中“70后”配額略少于“90后”樣本。正式研究采用配額抽樣,通過線下和線上結合的方式收集問卷,線上以問卷星作為平臺發布問卷,通過方便樣本和滾雪球抽樣,共收集316份問卷。線下問卷為廈門大學方便樣本,共計107份問卷,根據重復選項和漏選題項篩查,最終得到有效問卷35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3.7%,其中“70后”樣本148人,占總數41.8%;“90后”樣本206人,占58.2%。
在問卷調查和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對10個方便樣本進行半結構化訪談,其中“70后”及“90后”樣本各5名,“70后”樣本男女比例為2∶3,均來自廈門及廣州地區;“90后”樣本男女比例為2∶3,均為廈門地區樣本,詢問他們關于微信“點贊”基本使用情況及對于“點贊”的深層次理解。旨在對問卷調查結果的補充和深化,訪談時間為60~90分鐘。
(二)研究結果分析
1.“點贊”動機
“點贊”動因的測量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就外因而言,“70后”和“90后”最為關注的均為“發表的內容”,其次為人際關系強度,在位列第三的外因方面兩個群代產生差異,“70后”為“跟進朋友圈狀態”,“90后”為“潮流影響”。在內因方面,兩大群代“點贊”的最主要因素均為“自我表達”,但在位居第2、3位的內因方面存在分歧,影響“90后”“點贊”的內因分別為“給予他人關心與支持”和“維系人際關系”,而“70后”則為“與他人溝通交流”和“給予他人關心與支持”。
結果顯示,影響“70后”與“90后”“點贊”的首要外因均為“發表的內容”,首要內因均為“自我表達”。由此可知,對于兩大群代而言,自我表達均為“點贊”的首要動機(見圖2)。

圖2 “70后”與“90后”“點贊”動因內、外在因素得分排序
經過皮爾遜相關檢驗顯示,兩個群代在“點贊”的溝通實質上存在顯著差異。“70后”用“點贊”增進溝通,而“90后”在使用該功能是增進溝通和回避溝通的情況兼有。“出生年份”與“點贊溝通實質”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出生年份與增進溝通呈負相關,即年紀越大“點贊”時越傾向于增進溝通;與回避溝通呈正相關,即年紀越小“點贊”時越傾向于回避溝通。
2.“點贊”的內涵
本研究將“點贊”的內涵細化為認知和行為兩部分。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70后”與“90后”對“點贊”內涵的理解存在顯著差異(置信度95%,p<0.05)。認知1(我認為“點贊”代表正面態度,如“喜愛”“支持”等)和行為1(我會使用“點贊”表達積極正面的態度,如“欣賞”“支持”等)表示“點贊”的原始內涵,認知2(我認為“點贊”可以用來表達“調侃”“挖苦”等偏負面的意義)和行為2(我會使用“點贊”表達負面的態度,“調侃”“挖苦”“諷刺”等)代表“點贊”的引申內涵,“70后”在“點贊”認知1和行為1得分均值皆大于4分,即認同“點贊”初始正面含義,而對于“點贊”認知2和行為2則表示不贊同;“90后”認知1和行為1的得分分別為3.76和4.0,但在認知2和行為2得分顯著高于“70后”。
3.“點贊”對象
經過獨立樣本T檢驗可知,“70后”和“90后”的“點贊”對象均集中于“關系較好”和“關系很好”兩項,數據分析顯示“點贊”對象不存在顯著差異(置信度95%,p>0.05)。
五、討論
自媒體時代的到來為人際溝通提供了新的途徑,但在新技術發生的同時,人們如何理解和使用它則成為關注的焦點。通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70后”“90后”“點贊”行為及其差異的成因進行了探討。結果顯示“70后”“90后”的“點贊”動機及行為存在部分差異,我國互聯網文化的研究應當重視不同代際的語義差異。
(一)“點贊”動機:“70后”傾向于增進溝通,“90后”兼具增加溝通和回避溝通
研究證實,“70后”與“90后”都將“自我表達”作為“點贊”首要內驅力,而非“溝通”。受訪者普遍認為相較于評論功能,“點贊”在溝通效果上稍有欠缺,當受眾有強烈的溝通欲望受眾會直接選擇“文字評論”,因此“點贊”的“自我表達”動機高于“溝通”動機。此前國內學者徐智和楊莉明指出,相比起“點贊黨”表現出來的盲目隨大流,或是敷衍式的虛情假意,評論更加需要參與主體對內容進行認知上的加工,突破了點贊功能單一含義模糊的局限性,可傳達出內容更豐富且意義更明確的信息,使用戶之間進行更深層次的互動。從“點贊”動機的外在誘因看,兩個群代都將“發表內容”排在第一,而并非“發表者本人與自己的關系”或“跟進朋友圈狀態”此類以“溝通交流”為潛在目的的因素,進一步證實“溝通”并非“點贊”首要目的。可見在碎片化時代,“點贊”使受眾能夠快速表達對內容的偏好。
處于中年時期的“70后”將較多精力放在現實交往中,對新媒介的使用屬于跟進和學習狀態。“70后”傾向于在評論的同時“點贊”,使得溝通更加清晰和圓滿,該說法與丁道師口中的“非言語傳播”觀點相似。從心理層面來看,點贊加評論等互動相結合的交流方式能使人獲得更多滿足,孤獨感也會降低;而光是點贊,孤獨感并沒有發生變化。“90后”是伴隨互聯網成長的一代,網絡社交已經成為其重要的社交方式。他們在使用“點贊”進行溝通時更為靈活多元,會利用其增進溝通,甚至回避溝通,“點贊”被視作一種禮貌的回避方式,能夠將人際關系維持在淺層次交流的平衡點。“70后”指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也存在回避溝通的情況,諸如“吃飯了嗎”一類寒暄的話語,但對于“點贊”的回避溝通功能缺乏認知和使用。這一現象充分地反映了“數字土著”與“數字移民”在媒介使用想象力和創造力上存在差距。
(二)“點贊”的內涵:“70后”遵循“點贊”的正面含義,“90后”賦予“點贊”調侃、揶揄等衍生義
數據顯示,當關系較為親密的朋友發生悲傷程度較低的情況時(如“錢包掉了”),63.05%“90后”會通過“點贊”調侃朋友,而僅有35%的“70后”會對此類事件“點贊”。“火星文”和“非主流”的誕生印證了“90后”對網絡文化的靈活使用。他們將“點贊”視作可以自主定義用法的交流平臺,隨著時間和語義空間的轉化,其含義更具包容性,“調侃”“揶揄”等內涵就是新的語義延伸,如給地震消息“點贊”即表示關注和哀悼。“70后”將網絡視作不斷變化的工具,擔心超越“點贊”原有的含義可能會引發他人誤會,他們對于為地震等負面事件“點贊”的行為難以理解。可見“70后”對于“點贊”含義的使用較為遵循“點贊”設計者的初衷,即用“點贊”表達“喜愛”“支持”等正面意義;而“90后”則延伸出諸如“調侃”“嘲諷”“哀悼”等意義。
媒介社會意義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發明者、信息生產者、傳播者、使用者等各方不斷交互中得以產生。對于“70后”而言,微信是現實社交圈的網絡化遷移,它成為現實社會文化與互聯網文化的連接點,尊卑有別、以禮相待的社會關系結構在微信中得以延續。“90后”親歷了從QQ到微信的社交網絡更迭,從孩提時代開始他們的網絡社交圈即是網友與現實好友的集合,具有更強的匿名性和開放度,因而“90后”對于媒介功能、話語的創新與反叛就不足為奇。
(三)“點贊”對象:均傾向給關系較好的人“點贊”
研究發現“70后”與“90后”都傾向給關系較好的人“點贊”。當關系很好的人發表內容時,他們更傾向于直接評論,以滿足溝通和聯絡感情的需要;而關系較好的人則可以通過“點贊”體現對其的關注和尊重,維持關系。“點贊”成為衡量網絡人際關系的標尺之一,“評論”及 “點贊”意味著雙方關系較好,如果關系僅是一般甚至陌生,則通常表現為漠不關心。總體而言,“70后”與“90后”在“點贊”對象上并無顯著差異。
美國社會學家路易斯·沃斯在研究城市發展對人際關系的影響時指出,城市人口規模增長減少了人們以個人身份交往的機會,這種交往又是非個人性的、表面的、短暫的以及片面的,導致“次屬關系”占據人際關系中的主導地位。有趣的是,在社交媒體時代,微信好友的增長同樣消解了人們首屬關系的緊密度,從而催生出一大批僅需片面交流的“點贊之交”。
(四)媒介環境對受眾的影響:“70后”受自上而下、一對多的單向傳播媒介影響,媒介使用行為遵循規范;“90后”成長于自媒體興起的第二媒介時代,媒介使用行為更具創造性和反叛性
新媒介技術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后開始對受眾進行“馴化”,這種“馴化”不僅使信息傳播方式得以變革,甚至給人們情感體驗方式、表達方式、思維方式乃至整個文化環境和價值觀都帶來巨大沖擊。傳統媒介報紙、雜志和后來居上的電視、電影、廣播等電子媒介,構成我國改革開放最初十年的主流媒介格局,“70后”在青少年時期受傳統媒介的浸潤,媒介使用觀念及行為從屬于第一媒介時代,即由少數文化精英和知識分子主導的自上而下、由一對多的單向傳播。如今“70后”已到不惑之年,性格的成熟與穩重使他們多了一重遵循,這一特點也體現在媒體使用習慣上。他們傾向于遵從“點贊”的原有含義,對于媒介功能的使用有種“儀式感”,擔心“觸犯知識分子權威感”,也擔心他人無法理解自己的延伸而產生誤解,普倫斯基生動地將這一現象描述為“數字化移民”的“口音”,他們必須去適應自己面臨的新媒介環境,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仍保留著傳統媒體時代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與此對應的是“90后”開放的、雙向互動的第二媒介時代屬性。“90后”正值追逐潮流和表達自我的黃金年齡,獨生子女一代的“90后”形成了勇于打破傳統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加之以用戶為中心的自媒體迅速發展,“90后”的自主性在媒介使用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他們眼中的“點贊”更接近“全能型”符碼,并將“贊”發展成具有多重語義的溝通工具。一方面,“點贊”被青年群體灌注了豐富的情感要素;另一方面,“點贊”也包含更為復雜的社會功能。正如雷尼·李在《數字土著侵入工場》中借一位22歲大學生之口闡述了數字化時代的代際差異:“我才是生活在數字世界中的人。對我父親而言,數字化運用是工作;對我而言,這卻是生活。”
注釋:
②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2018年8月20日。
③ Gerlitz C.Helmond A.TheLikeEconomy:SocialButtonsandtheData-IntensiveWeb.New Media & Society,15,no.8,2013.pp.1348-1365.
④ Bosch T:OnFacebook,“Like”CanMean“Dislike”.http://www.slate.com/blogs/future_tense/2013/04/03/dislike_button_why_facebook_doesn_t_need_one.html,2015-07-15,2017-08-15.
⑤ [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曄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⑩ Hong C.Chen Z.& Li C.“Liking”andBeing“Liked”:HowArePersonalityTraitsandDemographicsAssociatedWithGivingandReceiving“Likes”onFacebook?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68,2017.pp.292-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