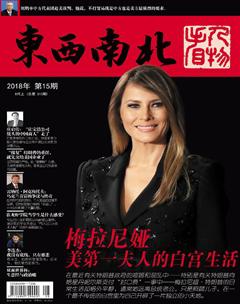數字游民的眼前與遠方
黃麟云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隨著無線上網技術、遠程工作方式和“世界公民”的出現和發展,近20年來,一群名為“數字游民”的全球性勞工群體,正將旅行、旅居與工作結合起來,游走世界。
“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逃離北上廣,去外地流浪”……借助文藝作品、社交網絡和自媒體傳播,旅行與工作似乎水火不容、不可兼得。
然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隨著無線上網技術、遠程工作方式和“世界公民”的出現和發展,近20年來,一群名為“數字游民”的全球性勞工群體,正將旅行、旅居與工作結合在一起,邊工作邊游走世界。
這個群體與自由職業者、SOHO族、斜杠青年、背包客、輕資產一代、間隔年旅行者等新興群體有諸多重疊,但又別有特色——數字游民本質是借助互聯網遠程工作,并借此實現地點獨立之人。自媒體從業者、互聯網創客、旅行設計師、客服、程序員……無論職業,只要可通過互聯網創造收入,都可成為數字游民,享受地點獨立帶來的自由生活。
數字游民還有一大特點,即“地理套利”,他們掙著高工資、高生活成本地區的薪酬,卻在東南亞、南歐、東歐、南美這些生活較便宜的地方生活。一些人旅行,在一個城市待數周到數月;另一些人則選擇在一個城市旅居1-3年,用慢旅行和沉浸式生活體驗人生。
數字游民真能兼顧眼前與遠方嗎?成為數字游民之前需做哪些準備?游民生活中有哪些自由與束縛?
被動收入流
每天固定工作4-5個小時,使用Trello項目管理應用及番茄工作法,一次工作1個番茄鐘(25分鐘),一天8個番茄鐘——這是數字游民張樂的工作日常。
同時運營“數字游民部落”“智用英語”兩個自媒體賬號,張樂的工作圍繞著內容創業:早飯后,晨讀資訊、整理資料做選題;到了晚上,則為在線付費課程做準備規劃。
每年2/3的時間,張樂會在呼和浩特的家中工作,其余時間則游走在曼谷、布拉格、布達佩斯、華沙等城市,一邊工作、一邊旅居。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旅居至少一個月,工作時則前往當地的咖啡館、聯合辦公空間或在酒店就地工作。這種慢節奏旅居生活,讓他有更多時間和心情感受各個城市的細節。
成為數字游民之前,張樂曾在油田服務公司斯倫貝謝在非洲乍得的基地擔任石油工程師。駐非期間,他利用輪休間隙走過埃及、法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國家,成為環球旅行達人。
張樂開啟數字游民生活與一本書、一次旅行密切相關。2009年,他碰巧讀到了蒂莫西·費里斯的自我管理書籍《每周工作四小時》,書中的工作生活方式讓他十分向往。
2015年春節期間,張樂在清邁和曼谷旅行時遇到了一群外國年輕人,這群人做網站、寫程序、寫博客、做翻譯、電商創業……工作內容五花八門,但都有相同的內核:通過互聯網工作養活自己,實現地域不設限。他意識到這群人就是《每周工作四小時》的實踐者,而自己也必須成為其中一員。
依靠此前的工作積蓄與投資收入、環球旅行培養的心理適應度、長期的個人生活方式設計準備,2015年張樂終于選擇通過內容創業,開啟數字游民生活。然而,這一切并不容易,起初兩年他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收入。
在張樂看來,數字游民與自由職業者最大區別是后者靠出租時間換取主動收入流,而前者更強調被動收入流,即只需付出一些努力做后續維護,就能定期獲得收入。
經過3年半的時間,張樂已小有所成。他在知乎上已收獲了約2.3萬名粉絲、53287次贊和88803次收藏;其“數字游民部落”付費社群已吸引了580多位成員。目前,他正在準備“地域獨立的生活方式”付費課程,幫助人們從零開始一步步設計自己的生活方式。
張樂還說:“人的財富有兩個面,一是時間,二是金錢。如果賺錢很多,但時間很少,那依然是窮人。只有創建穩定的被動收入流并獲取規模化的收入,才能變成真正的富人。”
遇見更多積極與勇氣
張樂和陳釗慶的數字游民生活是出于內心選擇,而行之(化名)走上數字游民的道路,開始卻有一些無奈和被迫。
2010年,行之大學畢業后開始找工作,卻屢遭拒絕,原因只是他身患殘疾。
先天性的腦癱和運動神經損傷,讓行之所有與肌肉相關的活動都受到影響,既包括跑、跳、爬山等運動,也包括面部表情、呼吸、說話等一系列功能。
找工作屢屢碰壁,行之只好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從網上找項目做。一開始,他什么項目都接,做網頁、做flash,甚至幫個人站長配置服務器,饑不擇食只是為了養活自己。
此后,行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職業人脈圈,他的工作與生活日漸好轉。現在,他已成功轉型,從事數據庫與后端程序開發,“現在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選項目。盡管收入還不穩定、也不算高,但只要肯干活就會有足夠收入。”
行之說:“此前我也會偶爾旅行,但不喜歡帶著工作,否則會覺得旅行玩不好、工作做不好。但這次的經歷啟發了我,其實可以邊旅行邊工作。”
現在,每年有約一半的時間,行之會在成都的家中工作,而另外一半時間則在外一邊工作、一邊旅居。旅居期間,他會在民宿的院子中或附近的咖啡館工作。上午工作、下午則視情況而定,節奏有條不紊但并不過于緊張。去年,他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深圳、合肥、道孚各自旅居了約1個月,今年初,他又在土耳其旅居了約1個月。“從小就愛讀歷史,現在有機會就會去這些歷史地點旅居,將書本上的概念具象化。目前,我正沿著古文明游走,已經去過埃及、以色列,接下來會去希臘、意大利。”
誰可以成為數字游民?
通過互聯網創造收入、不再受地域限制,數字游民這種特質讓很多人向往。然而,想要成為數字游民,必須進行諸多前期準備,其中,語言、經濟儲備、心理調試、工作能力尤為重要。
在成為數字游民之前,張樂正是靠英語加成,獲得了世界最大油田服務公司斯倫貝謝的駐非工程師機會。之后的數字游民生活中,也是英語讓他可在旅居全球各地時真正深入當地社區,實現旅居的真正價值;而陳釗慶更是為了在拉美進行數字游民生活,學習了4個月的西語。
盡管數字游民可通過地理套利降低生活成本,但在準備期和游民生活初期,收入來源不穩定、不足是許多游民的常態。為此,在準備游民生活期間,就應積極謀劃如何創造更多被動收入流。
數字游民通過互聯網遠程工作或獨自創業,獨立思考與工作是生活常態。各地旅居,也對自身適應性提出挑戰。學會獨立、適應環境變化帶來的歸屬感與安全感缺失,這是一道長久的自我心理培訓課程。“特別戀家,或偏好在多人辦公室工作的人,就不太適合數字游民這種生活方式。”陳釗慶說。
擁有專業的工作技能,并能通過互聯網創造收入,這是成為數字游民的基礎。
開始游民生活后,還需改變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方式。
數字游民首先要做到比“組織中的人”更為自律,將工作與生活時間分開。工作無人監管,游民還需用科學的工作方法規劃工作,避免工作時間低效。項目管理軟件、網絡多人協作工具、GTD(盡管去做)或番茄工作法都是可選項。
游民生活缺少職場內培訓機會,這就需要自我培訓,保持技能與職場要求同步。行之舉了自身的例子,“IT業發展太快,因此我每天都會花時間追蹤新技術發展、保持學習,讓自己跟上互聯網行業的節奏”。
(張北北薦自《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