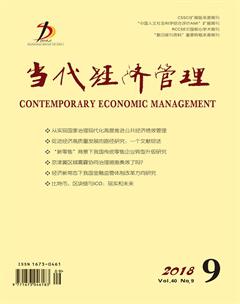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品牌權(quán)益的影響因素研究
焦勇兵 高靜
?眼摘 要?演以974名消費(fèi)者為樣本,對(duì)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品牌權(quán)益的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實(shí)證檢驗(yàn)。研究發(fā)現(xiàn):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通過(guò)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參與行為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進(jìn)而對(duì)品牌權(quán)益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也通過(guò)其群體認(rèn)同對(duì)其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行為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進(jìn)而對(duì)品牌權(quán)益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和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分別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和外部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當(dāng)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當(dāng)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眼關(guān)鍵詞?演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參與;生產(chǎn);消費(fèi);品牌權(quán)益
[中圖分類號(hào)]F27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1673-0461(2018)09-0046-07
一、引 言
品牌社區(qū)將消費(fèi)者與公司的品牌緊密地粘合,這對(duì)于品牌權(quán)益的提升至關(guān)重要[1]。品牌社區(qū)最初為線下形式,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催生了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2]。社會(huì)化媒體和品牌社區(qū)的聯(lián)姻產(chǎn)生了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使品牌與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更為親密[3]。因此,公司紛紛通過(guò)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來(lái)提升其品牌權(quán)益。然而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該方面話題的探討卻顯得滯后。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構(gòu)建了一個(gè)以品牌權(quán)益為因變量、以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和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為自變量、以參與、生產(chǎn)、消費(fèi)、關(guān)系強(qiáng)度、群體認(rèn)同、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和外部動(dòng)機(jī)為中介變量、以及以心理健康為調(diào)節(jié)變量的概念模型,旨在檢驗(yàn)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前置因素以及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對(duì)公司品牌權(quán)益的影響。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顯示: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會(huì)通過(guò)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的中介角色而積極影響其參與行為,進(jìn)而積極影響公司的品牌權(quán)益;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還會(huì)通過(guò)其群體認(rèn)同的中介角色而積極影響其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行為,進(jìn)而積極影響公司的品牌權(quán)益;消費(fèi)者的心理健康在其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外動(dòng)機(jī)的影響中具有調(diào)節(jié)作用,當(dāng)消費(fèi)者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當(dāng)消費(fèi)者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本研究的結(jié)論不僅為未來(lái)進(jìn)行基于調(diào)研的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消費(fèi)者行為研究帶來(lái)助益,而且也為營(yíng)銷經(jīng)理更加有效地開(kāi)展社會(huì)化媒體營(yíng)銷活動(dòng)提供指南。
二、文獻(xiàn)綜述
品牌社區(qū)是一個(gè)專門由品牌崇拜者構(gòu)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集合,是維系消費(fèi)者與營(yíng)銷者之間長(zhǎng)久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顯著影響消費(fèi)者忠誠(chéng)[1]。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以前,鑒于地理范圍約束,品牌社區(qū)需要成員之間面對(duì)面溝通才能建立,這就是線下品牌社區(qū)。線下品牌社區(qū)主要由公司而非消費(fèi)者創(chuàng)建,而且成員數(shù)量有限,成員之間的很少互動(dòng)和交流[2]。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使得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得以創(chuàng)建,社區(qū)成員可以隨時(shí)隨地地聚集在一起,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使成員擺脫了地理范圍約束,不需要親臨地理現(xiàn)場(chǎng)就可以進(jìn)行互動(dòng)和交流[4]。大多數(shù)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由消費(fèi)者創(chuàng)建[2]。
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使公司將社會(huì)化媒體引入品牌建設(shè)活動(dòng)。由于不受任何地理范圍和位置的約束,社會(huì)化媒體在培育消費(fèi)者和品牌的關(guān)系中起到關(guān)鍵作用。而且,社會(huì)化媒體本身就包含由不同品牌和顧客創(chuàng)建的品牌社區(qū),消費(fèi)者參與到這些社區(qū)中以從事與品牌相關(guān)的活動(dòng)如產(chǎn)生創(chuàng)意、評(píng)論張貼、分享信息、上傳圖片、下載視頻、購(gòu)買產(chǎn)品和服務(wù)等等[3]。不過(guò),鮮有學(xué)者將社會(huì)化媒體同品牌社區(qū)結(jié)合在一起進(jìn)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將社會(huì)化媒體與品牌社區(qū)的結(jié)合稱為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顯然,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是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的子集,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在于其所依托的平臺(tái)差異。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一開(kāi)始是建立在Web 1.0平臺(tái)上,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在線或虛擬品牌社區(qū)的平臺(tái)從Web 1.0拓展到Web 2.0,而Web 2.0則是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的核心平臺(tái)。隨著社會(huì)化媒體用戶的迅速增長(zhǎng),營(yíng)銷者紛紛創(chuàng)建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以吸引消費(fèi)者參與其中,從而產(chǎn)生和擴(kuò)大口碑,提高信息共享,驅(qū)動(dòng)銷售增長(zhǎng)[3]。
三、概念模型和關(guān)系假設(shè)
根據(jù)既有文獻(xiàn),本研究構(gòu)建了一個(gè)以品牌權(quán)益為因變量,以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和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為自變量,以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外部動(dòng)機(jī)、關(guān)系強(qiáng)度、群體認(rèn)同、參與、消費(fèi)和生產(chǎn)為中介變量,以心理健康為調(diào)節(jié)變量的概念模型(見(jiàn)圖1)。
(一)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對(duì)品牌權(quán)益的影響
品牌權(quán)益是企業(yè)營(yíng)銷活動(dòng)與消費(fèi)者互動(dòng)的過(guò)程中,使消費(fèi)者對(duì)其品牌形成知覺(jué)、聯(lián)想和態(tài)度傾向,從而轉(zhuǎn)化為實(shí)際購(gòu)買行為,并為企業(yè)建立長(zhǎng)期的差異化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5]。消費(fèi)者參與是指消費(fèi)者通過(guò)體力投入、情感投入和/或智力投入?yún)⑴c到他們共同感興趣的活動(dòng)[6]。在消費(fèi)者參與到企業(yè)營(yíng)銷活動(dòng)時(shí),也會(huì)引發(fā)消費(fèi)者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行為的產(chǎn)生。在和企業(yè)員工互動(dòng)時(shí),消費(fèi)者被看作企業(yè)的合作生產(chǎn)者或半個(gè)員工,以實(shí)現(xiàn)服務(wù)績(jī)效以及開(kāi)發(fā)新產(chǎn)品[7]。可見(jiàn),消費(fèi)者生產(chǎn)也是企業(yè)不可或缺的行為。另外,在參與企業(yè)營(yíng)銷活動(dòng)時(shí),消費(fèi)者一旦獲得令其滿意的價(jià)值體驗(yàn),就會(huì)產(chǎn)生消費(fèi)者忠誠(chéng),從而引發(fā)消費(fèi)者更多的消費(fèi)行為[8]。鑒于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深受企業(yè)和消費(fèi)者的歡迎,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已成為企業(yè)的流行話題,然而相應(yīng)的理論研究卻顯得滯后。社會(huì)化媒體具有參與性、創(chuàng)造性和互惠性等特征[9-13],消費(fèi)者不僅參與到企業(yè)營(yíng)銷活動(dòng),還同員工一起開(kāi)發(fā)新產(chǎn)品、創(chuàng)造內(nèi)容、共享信息以及重復(fù)購(gòu)買和推薦他人購(gòu)買。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的參與程度越高,其與員工之間的互動(dòng)程度就越高,從而會(huì)給其帶來(lái)更多的滿意[14],進(jìn)而會(huì)提升公司的品牌權(quán)益。而且,消費(fèi)者經(jīng)常聚集在一起進(jìn)行創(chuàng)意產(chǎn)生、產(chǎn)品評(píng)價(jià)、信息分享、圖片上傳、視頻下載、產(chǎn)品試用、服務(wù)購(gòu)買等活動(dòng),也經(jīng)常與員工一起進(jìn)行新產(chǎn)品開(kāi)發(fā)、內(nèi)容創(chuàng)造、信息共享、重復(fù)購(gòu)買和推薦他人購(gòu)買等活動(dòng)[12],這就會(huì)引致消費(fèi)者獲取更多的滿意[14],從而提升公司的品牌權(quán)益。鑒于此,本研究假設(shè):
H1:消費(fèi)者的參與(a)、生產(chǎn)(b)和消費(fèi)(c)對(duì)品牌權(quán)益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二)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行為的影響
關(guān)系強(qiáng)度是指一個(gè)網(wǎng)絡(luò)中成員之間的粘合效力,分為強(qiáng)關(guān)系和弱關(guān)系[15]。強(qiáng)關(guān)系構(gòu)成了個(gè)人網(wǎng)絡(luò)中較為強(qiáng)烈、親密的關(guān)系,能夠提供實(shí)質(zhì)性的情感支持[15];弱關(guān)系由廣泛的熟人和同事組成,促進(jìn)廣泛話題的信息搜尋[15]。研究發(fā)現(xiàn)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導(dǎo)致諸多后果,卻鮮有學(xué)者就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行為進(jìn)行探討。 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由于能輕易地獲取個(gè)人網(wǎng)絡(luò),強(qiáng)關(guān)系和弱關(guān)系都會(huì)影響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強(qiáng)關(guān)系在個(gè)體和小群體層次上會(huì)施加影響,弱關(guān)系則將個(gè)人網(wǎng)絡(luò)拓展到外群體,從而擴(kuò)展弱關(guān)系潛在的影響力。所以,本研究假設(shè):
H2: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參與(a)、生產(chǎn)(b)和消費(fèi)(c)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三)群體認(rèn)同對(duì)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行為的影響
群體認(rèn)同是指?jìng)€(gè)體對(duì)其屬于某一群體的認(rèn)可[16]。擁有一個(gè)特殊的群體認(rèn)同意味著和某個(gè)群體相融合、和內(nèi)群體其他成員相似以及從群體的觀點(diǎn)看待問(wèn)題[16]。群體認(rèn)同可以使成員推薦他人消費(fèi)[17]或參與群體活動(dòng)[18]。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會(huì)受到群體認(rèn)同的影響。當(dāng)消費(fèi)者認(rèn)同其所在的品牌社區(qū)時(shí),就會(huì)更加積極地參與品牌社區(qū)中的各種活動(dòng)[18],就會(huì)在朋友圈中越發(fā)積極地對(duì)相關(guān)品牌進(jìn)行正向評(píng)價(jià),就會(huì)推薦其聯(lián)絡(luò)人進(jìn)行相關(guān)品牌的購(gòu)買[17],就會(huì)更加積極地對(duì)相關(guān)品牌進(jìn)行口碑傳播,就會(huì)更加積極地購(gòu)買相關(guān)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因此,本研究假設(shè):
H3:消費(fèi)者的群體認(rèn)同對(duì)其參與(a)、生產(chǎn)(b)和消費(fèi)(c)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四)動(dòng)機(jī)對(duì)關(guān)系強(qiáng)度和群體認(rèn)同的影響
動(dòng)機(jī)是指?jìng)€(gè)體的行為傾向,分為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和外部動(dòng)機(jī)[19]。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是指因固有的興趣或愉悅感而做某事[19],外部動(dòng)機(jī)是指因?qū)е驴煞蛛x的某種結(jié)果而做某事[19],而不是因?yàn)樽鲞@件事情本身有內(nèi)在吸引力而采取行動(dòng)[20]。動(dòng)機(jī)被公認(rèn)是個(gè)體行為和信息技術(shù)采納行為的關(guān)鍵決定因素[20]。不過(guò),還未曾有學(xué)者探討動(dòng)機(jī)對(duì)關(guān)系強(qiáng)度和群體認(rèn)同的影響。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一方面,消費(fèi)者加強(qiáng)同其聯(lián)絡(luò)人的關(guān)系以及想獲取群體認(rèn)同是出于愉悅感和興趣的需要。另一方面,消費(fèi)者加強(qiáng)同其聯(lián)絡(luò)人的關(guān)系以及想獲取群體認(rèn)同是出于外在利益的驅(qū)使。因此, 本研究假設(shè):
H4: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對(duì)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a)和群體認(rèn)同(b)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消費(fèi)者的外部動(dòng)機(jī)對(duì)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c)和群體認(rèn)同(d)也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五)自我建構(gòu)對(duì)動(dòng)機(jī)的影響
自我建構(gòu)是指?jìng)€(gè)體如何認(rèn)識(shí)其自身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guān)系,分為獨(dú)立型與相依型兩個(gè)維度[9-12]。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的個(gè)體傾向于突出其本身的獨(dú)特和自主價(jià)值,傾向于追求表達(dá)其個(gè)性的目標(biāo)[9-12];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的個(gè)體則倚重于強(qiáng)調(diào)團(tuán)結(jié)與和諧的價(jià)值,傾向于追求社群融合的目標(biāo)[9-12]。學(xué)者們就自我建構(gòu)引發(fā)的后果進(jìn)行了研究[9-12]。不過(guò),鮮有學(xué)者就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自我建構(gòu)對(duì)動(dòng)機(jī)的影響進(jìn)行研究。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當(dāng)擁有較高程度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時(shí),消費(fèi)者傾向于追求象征其個(gè)性價(jià)值的目標(biāo),表現(xiàn)出追求愉悅和享樂(lè)價(jià)值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21];當(dāng)擁有較高程度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時(shí),消費(fèi)者傾向于追求突出團(tuán)結(jié)與和諧的價(jià)值目標(biāo),表現(xiàn)出與他人互動(dòng)與聯(lián)絡(luò)的外部動(dòng)機(jī)[21]。因此,本研究假設(shè):
H5: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a),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b)。
(六)心理健康在自我建構(gòu)對(duì)動(dòng)機(jī)影響中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心理健康是指積極情感對(duì)消極情感占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以及對(duì)整體生活感到滿意[21]。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心理健康會(huì)調(diào)節(jié)自我建構(gòu)對(duì)動(dòng)機(jī)的影響。當(dāng)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具有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的消費(fèi)者會(huì)呈現(xiàn)出更多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他們健康的心態(tài)會(huì)激勵(lì)他們沉浸于自己感興趣的內(nèi)容,從而強(qiáng)化其對(duì)固有興趣或愉悅感的體驗(yàn)。當(dāng)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具有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的消費(fèi)者會(huì)呈現(xiàn)出更多的外部動(dòng)機(jī),他們消極的心態(tài)會(huì)導(dǎo)致他們尋求親朋的聯(lián)絡(luò)以求心理?yè)嵛俊hb于此,本研究假設(shè):
H6:當(dāng)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a),當(dāng)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b)。
四、研究設(shè)計(jì)
(一)研究對(duì)象和資料收集
鑒于要檢驗(yàn)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的概念模型,本研究將目標(biāo)母體鎖定于社會(huì)化媒體中品牌社區(qū)中的所有成員。本研究對(duì)調(diào)查對(duì)象進(jìn)行了嚴(yán)格的條件篩選,即每一位問(wèn)卷填寫者必須是社會(huì)化媒體中某一或某些品牌社區(qū)中的成員,他們被要求列出所參與的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的名稱。問(wèn)卷的發(fā)放和回收通過(guò)微信、QQ、微博等社會(huì)化媒體進(jìn)行,時(shí)間持續(xù)210多天。調(diào)查對(duì)象來(lái)自各行各業(yè),包括服裝、護(hù)膚美容、手機(jī)、電腦、銀行、保險(xiǎn)、汽車、教育培訓(xùn)等。在受邀填寫問(wèn)卷的1797位調(diào)查對(duì)象中,974位返回了有效問(wèn)卷,問(wèn)卷答復(fù)率是54.2%。這種資料收集方法同既有的相關(guān)研究[9-13]是一致的。所有974位調(diào)查對(duì)象的平均年齡為31.9歲,其中50.6%為女性。
(二)變量操作化測(cè)量
所有的變量都采用里克特(Likert)5點(diǎn)量表來(lái)測(cè)量,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和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的量表開(kāi)發(fā)源于Jiao et al.[9]的研究,分別包括個(gè)4和5個(gè)問(wèn)項(xiàng);心理健康的量表設(shè)計(jì)源于Diener et al. [21]開(kāi)發(fā)的“積極樂(lè)觀”量表,包括5個(gè)問(wèn)項(xiàng);內(nèi)部動(dòng)機(jī)的量表源于Davis et al.[20]的研究,包括3個(gè)問(wèn)項(xiàng);外部動(dòng)機(jī)的量表依據(jù)Elliot & Covington[19]的研究而改編,也包括3個(gè)問(wèn)項(xiàng);關(guān)系強(qiáng)度的量表根據(jù)Granovetter[15]的定義自行創(chuàng)建,包括5個(gè)問(wèn)項(xiàng);群體認(rèn)同的量表源于Jiao et al.[9]開(kāi)發(fā)的量表,包括4個(gè)問(wèn)項(xiàng);參與的量表依據(jù)Rodie & Kleine[6]的研究而自行編制,包括5個(gè)問(wèn)項(xiàng);生產(chǎn)的量表基于Fang et al.[7]的研究而自行編制,亦包括5個(gè)問(wèn)項(xiàng);消費(fèi)的量表根據(jù)Gummerus et al.[8]的研究自行設(shè)計(jì),包括4個(gè)問(wèn)項(xiàng);品牌權(quán)益的量表根據(jù)Keller [5]的研究改編而成,包括6個(gè)問(wèn)項(xiàng)。
五、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
(一)測(cè)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檢驗(yàn)
本研究選取Cronbach's Alpha(α)系數(shù)值、組合信度(CR)值和平均變異數(shù)萃取量(AVE)值這3個(gè)最常用的指標(biāo)來(lái)檢驗(yàn)測(cè)量模型的信度,表1所示,所有變量的α系數(shù)值均在0.70以上,CR值均在0.60以上,AVE值均在0.50 以上,表明測(cè)量模型的信度很好。本研究通過(guò)χ2/df、RMSEA、CFI、GFI、AGFI、IFI、NFI和RFI等擬合指數(shù)指標(biāo)來(lái)評(píng)估測(cè)量模型建構(gòu)效度,通常χ2/df的值介于2和5之間;RMSEA的值通常在0.10以下表示好的擬合,在0.05以下則表示非常好的擬合;CFI、GFI、AGFI、IFI、NFI和RFI的值分別在0.90以上表示擬合很好,結(jié)果表明該11個(gè)變量構(gòu)成的測(cè)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χ2/df = 3.23,RMSEA = 0.08,CFI = 0.97,GFI = 0.94, AG= 0.93, IFI= 0.94,NFI= 0.96,RFI= 0.92。本研究選取完全標(biāo)準(zhǔn)化因子載荷(SFL)、復(fù)平方相關(guān)系數(shù)(SMC)來(lái)檢驗(yàn)測(cè)量模型的收斂效度,數(shù)據(jù)結(jié)果顯示所有的SFL值和SMC值均在p<0.001顯著性水平上達(dá)到 0.50 以上,表明測(cè)量模型的收斂效度很好。本研究也檢驗(yàn)了測(cè)量模型的區(qū)別效度, 數(shù)據(jù)顯示每?jī)蓚€(gè)變量之間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絕對(duì)值均在0.90以下,而且AVE 的平方根也大于每?jī)蓚€(gè)變量之間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值,說(shuō)明測(cè)量模型的區(qū)別效度很好(見(jiàn)表2)。
(二)結(jié)構(gòu)模型和假設(shè)關(guān)系檢驗(yàn)
驗(yàn)證性因子分析結(jié)果顯示整個(gè)結(jié)構(gòu)模型具有很好的擬合度:χ2/df= 3.26,達(dá)到了介于2與5之間的要求,RMSEA=0.06,達(dá)到了0.10好的標(biāo)準(zhǔn)并接近于0.05的非常好的標(biāo)準(zhǔn),CFI= 0.93、GFI= 0.97、AGFI=0.94、IFI= 0.92、NFI= 0.95、NNFI=0.91、RFI=0.98,也符合大于等于0.90的標(biāo)準(zhǔn)。
本研究通過(guò)路徑關(guān)系即標(biāo)準(zhǔn)化回歸系數(shù)β值來(lái)檢驗(yàn)結(jié)構(gòu)模型的前5個(gè)假設(shè)關(guān)系(H1~H5),β值愈大表示路徑的因果關(guān)系愈顯著。圖2顯示從H1a到H5b的假設(shè)關(guān)系中,H1a、H1b、H1c、H2a、H3a、H3b、H3c、H4a、H4b、H5a和H5b因達(dá)到顯著性水平(p≤0.001,p≤0.01或p≤0.05)而被支持;而H2b、H2c、H4c和H4d因未達(dá)到顯著性水平(p≤0.001,p≤0.01或p≤0.05)而被拒絕。
本研究發(fā)現(xiàn)H1a、H1b和H1c(消費(fèi)者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對(duì)品牌權(quán)益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都得到了強(qiáng)有力的支持。H1a、H1b和H1c的β值分別是0.431、0.448和0.437,3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均 在p≤0.001水平上顯著,說(shuō)明對(duì)H1a、H1b和H1c的支持成立。研究結(jié)果顯示,H2a(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參與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亦得到了強(qiáng)有力的支持。H2a的β值是0.384,該關(guān)系假設(shè)亦在p≤0.001水平上顯著,說(shuō)明對(duì)H2a的支持成立。研究結(jié)果還顯示,H3a、H3b和H3c(消費(fèi)者的群體認(rèn)同對(duì)其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亦都得到了強(qiáng)有力的支持。H3a、H3b和H3c的β值分別是0.634、0.705和0.592,三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亦均 在p≤0.001水平上顯著,說(shuō)明對(duì)H3a、H3b和H3c的支持亦成立。正如假設(shè)的那樣,H4a和H4b(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對(duì)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和群體認(rèn)同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也得到了強(qiáng)有力的支持。H4a和H4b的β值分別是0.139和0.141,兩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在p≤0.01水平上顯著,說(shuō)明對(duì)H4a和H4b的支持也成立。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表明H5a和H5b(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也得到了強(qiáng)有力的支持。H5a和H5b的β值分別是0.117和0.121,兩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在p≤0.05水平上顯著,說(shuō)明對(duì)H5a和H5b的支持也成立。
然而,H2b和H2c(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卻遭到了拒絕。H2b和H2c的β值分別是0.009和0.007,對(duì)應(yīng)的p值分別為0.923和0.916,說(shuō)明這兩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均在p≤0.001,p≤0.01或p≤0.05水平上呈現(xiàn)非顯著性,因此對(duì)H2b和H2c的支持不成立。;另外,H4c和H4d(消費(fèi)者的外部動(dòng)機(jī)對(duì)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和群體認(rèn)同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也沒(méi)有得到支持。H4c和H4d的的β值分別是0.005和0.008,兩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的顯著性p值分別為0.927和0.984,因達(dá)不到p≤0.05的標(biāo)準(zhǔn)而被拒絕。
本研究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回歸分析來(lái)檢驗(yàn)心理健康在自我建構(gòu)對(duì)動(dòng)機(jī)的影響中的調(diào)節(jié)作用(H6a和H6b),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也以標(biāo)準(zhǔn)化回歸系數(shù)β值來(lái)呈現(xiàn)(見(jiàn)圖2),系數(shù)愈大表示在因果關(guān)系中的重要性愈高。在H6a中,本研究預(yù)測(cè)心理健康在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的影響中具有調(diào)節(jié)作用。數(shù)據(jù)運(yùn)行結(jié)果顯示雙因子交互效應(yīng)(IS ×PW) 呈現(xiàn)顯著性(β= 0.394,p≤0.001)。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消費(fèi)者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當(dāng)消費(fèi)者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不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因此,H6a成立。在H6b中,本研究預(yù)測(cè)心理健康在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的影響中具有調(diào)節(jié)作用。數(shù)據(jù)運(yùn)行結(jié)果顯示雙因子交互效應(yīng)(ITS×PW) 呈現(xiàn)顯著性(β= -0.138,p≤0.01)。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消費(fèi)者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當(dāng)消費(fèi)者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不會(huì)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因此,H6b也成立。
六、研究結(jié)論和啟示
本研究聚焦于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行為的前置因素及其對(duì)品牌權(quán)益的影響并得出以下結(jié)論: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通過(guò)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參與行為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進(jìn)而對(duì)公司的品牌權(quán)益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消費(fèi)者的內(nèi)部動(dòng)機(jī)亦通過(guò)群體認(rèn)同對(duì)其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行為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進(jìn)而對(duì)公司的品牌權(quán)益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和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分別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和外部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當(dāng)擁有高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獨(dú)立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內(nèi)部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當(dāng)擁有低度的心理健康時(shí),消費(fèi)者的相依型自我建構(gòu)對(duì)其外部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出乎本研究預(yù)期的是,H2b(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生產(chǎn)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和H2c(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強(qiáng)度對(duì)其消費(fèi)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并不顯著。一個(gè)可能的原因是消費(fèi)者在參與到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時(shí),與這些消費(fèi)者呈現(xiàn)高關(guān)系強(qiáng)度的朋友圈基本上是這些消費(fèi)者的家庭成員或其他非常親密的人士,消費(fèi)者與他們這些家庭成員或其他非常親密的人士所構(gòu)成的高關(guān)系強(qiáng)度只會(huì)對(duì)消費(fèi)者在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的參與行為施加影響,但一旦消費(fèi)者產(chǎn)生生產(chǎn)(如張貼產(chǎn)品或服務(wù)的相關(guān)信息)意愿或消費(fèi)(如購(gòu)買相關(guān)產(chǎn)品或服務(wù))意圖時(shí),這些消費(fèi)者的家庭成員或其他非常親密的人士就會(huì)對(duì)他們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意愿提出建設(shè)性的意見(jiàn)、建議甚至是忠告,而且消費(fèi)者也愿意傾聽(tīng)他們這些最親密的家人或好友的意見(jiàn)、建議甚至是忠告,這就會(huì)導(dǎo)致消費(fèi)者在做出生產(chǎn)或消費(fèi)決策時(shí)會(huì)三思而后行。如此看來(lái),H2b和H2c這兩個(gè)關(guān)系假設(shè)遭到拒絕也就不奇怪了。另外,H4c(消費(fèi)者的外部動(dòng)機(jī)對(duì)其關(guān)系強(qiáng)度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和H4d(消費(fèi)者的外部動(dòng)機(jī)對(duì)其群體認(rèn)同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也不顯著。一個(gè)可能的原因是消費(fèi)者在進(jìn)行有關(guān)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活動(dòng)時(shí),并非出于其所在的朋友圈與其之間的粘性以及其所在的朋友圈對(duì)其本人的認(rèn)可程度等外界的壓力、刺激和誘惑,而是因?yàn)樗麄冊(cè)谄放粕鐓^(qū)中的參與、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過(guò)程能夠給他們帶來(lái)享受,這樣消費(fèi)者就會(huì)因樂(lè)趣、興趣或固有的心理需求而結(jié)成緊密的朋友圈,并相互聯(lián)絡(luò)和認(rèn)可。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xiàn)體現(xiàn)在:首先,本研究創(chuàng)建性地提出了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的概念,這為未來(lái)的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研究提供一個(gè)范式框架。其次,本研究對(duì)社會(huì)化媒體中品牌社區(qū)的消費(fèi)者行為進(jìn)行參與、消費(fèi)和生產(chǎn)3種類型的劃分,這為未來(lái)更加深入的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消費(fèi)者行為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第三,本研究引進(jìn)關(guān)系強(qiáng)度這一構(gòu)念以反映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所在朋友圈的關(guān)系親密程度,未來(lái)的研究可以就這個(gè)方向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挖掘。第四,本研究引進(jìn)群體認(rèn)同這一構(gòu)念以解釋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消費(fèi)者被所在朋友圈所認(rèn)可的程度,這為未來(lái)的進(jìn)一步研究指出了方向。
本研究給營(yíng)銷經(jīng)理帶來(lái)如下的管理啟示:首先,本研究的結(jié)論會(huì)幫助營(yíng)銷經(jīng)理對(duì)社會(huì)化媒體品牌社區(qū)中的消費(fèi)者行為進(jìn)行更深入的洞察,從而有益于他們更加針對(duì)性地制定和實(shí)施社會(huì)媒體營(yíng)銷戰(zhàn)略。其次,本研究將社會(huì)化媒體中的消費(fèi)者行為劃分為參與、消費(fèi)和生產(chǎn)3種類型,營(yíng)銷經(jīng)理可依據(jù)這3種行為對(duì)消費(fèi)者市場(chǎng)進(jìn)行細(xì)分,從而再依據(jù)相應(yīng)的目標(biāo)市場(chǎng)對(duì)公司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進(jìn)行定位。再次,營(yíng)銷經(jīng)理不僅要激發(fā)消費(fèi)者對(duì)品牌的內(nèi)在興趣,還要把具有共同愛(ài)好和興趣的消費(fèi)者聚集在一起以形成和鞏固品牌社區(qū),從而提升品牌權(quán)益。
[參考文獻(xiàn)]
[1] Muniz,A. M. Jr.,and O'Guinn,T. C. Brand Community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1,27 (3):412-432.
[2] Madupu,V.,and Cooley D. O.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Online Br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Internet Commerce,2010,9:127–147.
[3] Laroche,M.,Habibi,M.R. and Richard,M.O. To be or not to be in social media:How brand loyalty is affected by social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3,33(1):76-82.
[4] Ahn,H.,Kwon,M. W. and Sung,Y. Online Brand Community ac-ross Cultur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Business Management,2010,4 (1):34-52.
[5] Keller,K. L. Conceptualizing,Measuring,and Manag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3,57 (1):1-22.
[6] Rodie,A. R. and Kleine,S. S.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s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C]. Handbook of Services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Sage Publications,Beverley Hills,California,2000:111-125.
[7] Fang,E.,Palmatier,R.W. and Steenkamp,J-B.E.M. Effect of Service Transition Strategies on Firm Value [J]. Journal of Marketing,2008,72 (4):1-14.
[8] Gummerus,J. Liljander,V .Weman,E. and Pihlstro¨m,M. Customer engagement in a Facebook brand community [J].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2012,35 (9):857-877.
[9] Jiao,Y.,Jo,M-S.and Sarig?觟llü,E. Social value and content value in social media:Two paths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 and Electronic Commerce,2017,27 (1):3-24.
[10] Jiao,Y.,Gao,J.,and Yang,J. Social Value and Content Value in Social Media:Two Ways to Flow[J]. Journal of Advanced Management Science,2015,3 (4):299-306.
[11] 焦勇兵,高靜. 社會(huì)化媒體中消費(fèi)者的自我建構(gòu)、顧客價(jià)值與沉浸體驗(yàn) [J]. 財(cái)經(jīng)論叢,2017(5):89-101.
[12] 焦勇兵,高靜,楊健. 社會(huì)化媒體中自我建構(gòu)對(duì)顧客價(jià)值和自我概念的影響 [J]. 社會(huì)科學(xué)家,2017(4):77-83.
[13] 焦勇兵,高靜,楊健.顧客采納社會(huì)化媒體的影響因素——一個(gè)理論模型及其實(shí)證研究[J]. 山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3(7):43-55.
[14] Nah,F(xiàn). F.-H.,Eschenbrenner,B. and DeWester,D. Enhancing Brand Equity through Flow and Telepresence:A Comparison of 2D and 3D Virtual Worlds [J]. MIS Quarterly,2011,35(3):731-719.
[15] Granovetter,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1380.
[16] Hogg,M. A.,and Terry,D. J.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121-140.
[17] Mael,F(xiàn). and Ashforth,B. 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s:A partial test of the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2,13:103-123.
[18] Greenfield,E.A.,and Marks,N.F.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groups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adults who develop functional limitations: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s,2007,62B:S60-S68.
[19] Elliot,A. J.and Covington,M. V.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001,13 (2):73-92.
[20] Davis,F(xiàn). D.,Bagozzi,R. P.,and Warshaw,P. R.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Use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2,22 (14):1111–1132.
[21] Diener,E.,Wirtz,D.,Tov,W.,Kim-Prieto,C.,Choi. D.,Oishi,S.,and Biswas-Diener,R. New measures of well-being: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9,39:24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