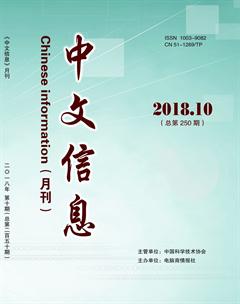淺談儒學發展
王一冰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8)10-0-01
儒學興起于春秋戰國之際,以仁與禮為主要內核,作為一傳承兩千年的學派,深刻的影響著國人的思想,其提出的許多言論,已經成為國人傳承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而且對現今社會仍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1],為此,本文以歷史為依據,將儒學發展分為先秦時期、秦漢時期、宋明時期三個時期,進行概述,以助力各位更好的了解儒學,從中汲取精神營養,補足文化鈣質。
一、先秦時期的儒學
儒家興于孔子,歷經子夏、子思、曾子、孟子、荀子等人,學術體系進一步完善,并在后期經儒學之人學說增補,達到一個高潮。通過研讀儒家體系,我們不難發現,其主要在于制定人倫,明確社會等級序列。
從興起緣由上來說,儒學的興起與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現實有關,在后期也極大可能的維護了社會安定,但是這一學術又一大弊端,在于固化,只利于維持,不利于前進和發展。具體來說,儒家強調以仁、孝、為本,孔子在論語里就曾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的學生有子也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同時講述仁者愛人,弘揚誠實守信,強調克己復禮,最終達到禮、信、孝的境界,成為一個‘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全面發展人才,這些在論語中都可以找到相關資料。
由于儒學是對當時禮崩樂壞現實的反應,其本質在于重塑或鞏固舊有的等級秩序,而禮是秩序最好的反應,所以禮樂與儒家思想有著天然的不解之緣。從整體上來說,我們知道禮樂其實要按照規則行事,宮商角徵羽有序運行,這與儒家‘人倫思想秩序理論不謀而合。同時禮樂一般也有相關的禮儀,比如不同場合使用不同的禮樂,不同人要使用不同級別的禮樂,這其實就是儒家‘禮之坐在。還記得,在論語中,孔子曾說“奚取于三家之堂。”可見其對禮的尊崇[2]。
二、秦漢時期的儒學
秦漢時期的儒學以漢武帝為高峰。那個時候,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之機。不過這一時期的儒學,與原有的儒學已經有了體系的不同。這一時期的儒學,主要采用了‘天人感應的理念,講求‘君權神授,講求‘倫理秩序,與傳統儒學以仁為中心有些不同。此時的儒學,已經不是一家思想之結晶,也不是學子共有的信仰,而開始成為一種統治工具,具有維護當時統治的作用。在秦漢時期,儒學極為發達,當時又專門的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學習儒學。而且,非但董仲舒等儒學門派之人得到了重用,就連當時宰相,也是儒門中人。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儒學達到了政治巔峰,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儒學漸漸成為讀書人必讀的經典,并傳承至今。
三、宋明時期的儒學
宋明時期的儒學,主要以集大成的朱子為代表。朱子做了四書集注一書,對儒學知識進行了適當的刪減。我們知道宋朝時代,仍有唐代遺風,整體社會風氣較為開放,很多人放縱貪欲,社會環境整體較為惡劣。針對這一實際,朱子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為主體的儒學思想,以正社會視聽,對儒學有一定的桎梏作用。但是其對四書的注解,以及明朝將四書作為朝廷取士的必考課,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了儒學的發展。
當時與朱子齊名的人,是王陽明。對于王陽明來說,其最大的理論成就在于“知行合一”學說。該學說提出于1509年,是王陽明在貴州的貴陽書院講學時提出,是王陽明思想最集中的體現。
王陽明之所以提出這一思想,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關。我們清楚,宋明時候中國和他國的交流進一步增多,與意大利、日本、葡萄牙都有交集。同時,傳教士也開始廣泛進入我國,社會進一步開放,思想進一步多元。在那一時期,曾經固化讀書階層有所分化,主要表現為部分人以咬文嚼字為功,皓首窮經,卻從不實踐,學習流于表面,不利于社會構建。也有部分人宣揚讀書無用論,只一味地在實踐中求知。王陽明始終認為學習讀書最終要反哺于社會。其實知行問題在中國由來已久,當時朱子認為,應當是知在先,而且知很重要,不太注重實踐。王陽明卻認為知行合一,即兩者是一體的。即人要學知識,唯有學知識才能夠運用于實踐,但是人也要去做事,唯有實踐才能夠完善和產生新的理論。
在宋明之后,儒學發展甚為緩慢,甚至出現過暫時的停滯。不過隨著國人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儒學漸漸又有興起之兆[3],開始作為重要的精神補品,用以指導現代人的學習,生活和工作。相信,在未來,儒學定會有更加良好的表現。
四、結語
都說‘觀懂一門學,勝讀十年書,在我看來觀懂一門學,勝為十年人。真正的知識分子,會注重從系統上學習一門科學,認真用心對待每一本經典。因為經典能夠帶領我們的思想馳騁萬里、感受千年文化,同時超越國界,能夠讓我們上下縱橫,在歷史的河流中探水舀湯;能夠讓我們對萬事萬物的認識上升一個層面,對外部世界也有了更精準的把握。這就是經典的意義,也是儒學的意義,在后續的學習工作中,我也會將我從儒學中感悟到的一切加以運用,切實將學思踐悟進行到底,讓我們無形的感悟完成實體的效果化,助推儒學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傅永軍.論東亞儒學的存有形態[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1):18-26.
[2]黃玉順.社會儒學與生活儒學之關系——與謝曉東教授商榷[J].學術界,2018(05):95-106.
[3]涂可國,Zhu Yuan,Wang Keyou.文化儒學:當代儒學新形態[J].孔學堂,2018,5(01):17-31+12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