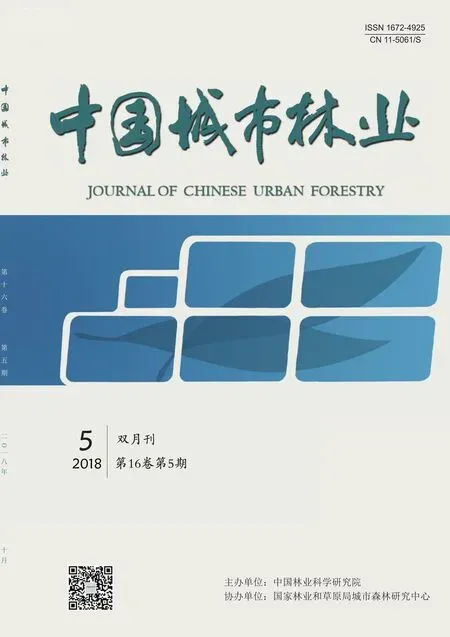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景觀研究動態及其進展*
劉 杉 張凱莉 周政旭 周 曦
1 北京林業大學 北京 100083 2 清華大學 北京 100084
我國西南地區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重慶市和西藏自治區,占我國陸地國土面積的24.5%[1]。該區地處青藏高原南部、橫斷山脈、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等區域,地貌類型復雜多樣,海拔高差懸殊,為我國生物種類和生態系統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也是我國少數民族最為集中的區域[2]。為此,本文在全面收集西南民族地區民族聚落研究成果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西南地區民族聚落研究的發展歷史、當代民族聚落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研究展望,試圖為西南民族聚落的研究、聚落景觀的保護,以及新建民族聚落規劃等提供理論參考。
1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聚落研究
我國古人對西南民族聚落早有記載。《史記·西南夷列傳》《華陽國志》《黔苗圖說》《云南志》等記錄了西南民族風俗及其與漢王朝的關系,以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從近代開始,我國西南民族聚落研究的發展歷史可分為4個階段,即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早期民族、人類學研究階段,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識別”工作階段,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系統性民族研究階段,以及2000年左右至今的跨學科研究階段。Cnki.net搜索的相關論文數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建國以后研究階段的變化(圖1,表1)。

圖1 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文獻發表年度趨勢

階段特征 社會背景時間/年 事件或成文 核心議題民族聚落調查、記錄開端戰爭不斷,中外學者、侵略者及探險家從不同路徑進入西南腹地,學者遷往西南1840—1949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呂思勉《中國民族史》林惠祥《中國民族史》梳理歷史民族關系和系統分類,確立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民族識別”工作建國初期,團結各民族1950—1969《云南民族情況匯集草稿》《傣族社會歷史調查》《貴州少數民族情況及民族工作》“民族識別”工作、民族政策的建立、逐步擺脫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思想系統性民族研究學術環境逐漸恢復1980—2000“民族問題五套叢書”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查研究民族研究開始走向細分學科研究方向發展跨學科研究加入WTO,中國越來越多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經濟高速發展2000—今地理、規劃、生態、體育、音樂等多學科多領域及交叉學科研究探索保護與發展方法的新方向
1.1 早期民族、人類學研究階段
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近代早期民族聚落研究主要來自考古學及人類學專業,并以調查記錄為主。19世紀末20世紀初,學者、侵略者及探險家進入中國西南地區,展開一系列調查記錄并成文成書,如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和榮赫鵬的《英國侵略西藏史》等。
20世紀初,我國學者從文獻研究和田野調查兩方面開始了早期的民族學研究,此時期的民族聚落研究以文獻考證結合調查記錄為主要研究模式。梁啟超論述了歷史民族關系問題和中國民族的系統分類,強調各民族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提高中華民族的自覺[3-4]。抗日戰爭爆發后,眾多學者聚集于西南,西南民族學、民族史等方面研究有了重要的發展,如林耀華的《涼山夷家》、方國瑜的《滇西邊區考察記》、江應樑的《擺夷的經濟文化生活》等為西南民族聚落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期,營造學社遷往西南開展建筑學的研究,劉敦楨的《西南古建筑調查》和劉致平的《四川住宅建筑》揭示出我國地域建筑文化研究發展的新趨勢[5-6]。
1.2 “民族識別”工作階段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開展了“民族識別”工作和民族政策建立工作,對西南民族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調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調查報告,如《云南民族情況匯集草稿》《傣族社會歷史調查》《貴州少數民族情況及民族工作》等[5]。此期的民族、歷史及經濟學者,如費孝通、黃現璠、夏康農、吳文藻、楊成志、馬長壽等對西南民族地區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民族研究逐漸擺脫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思想[3]。
1.3 系統性民族研究階段
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西南民族調查研究的深入和學術環境的逐漸恢復,民族研究又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7],民族聚落研究逐漸走向分學科系統研究階段,如藏學、彝學、苗學、納西學等[8]。
1.4 跨學科研究階段
2000年左右,隨著中國越來越多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研究逐漸深入,民族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中國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中國與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在民族研究理論和方法上開始受西方人類學研究的影響,民族研究也從早期的人類學研究轉變到地理、規劃、生態、體育、音樂等多學科多領域及交叉學科研究。在此期間,民族聚落景觀研究綜合多學科視野,從聚落層面、區域層面展開對聚落人居環境、文化生態、文化景觀等綜合研究[8]。
2 研究理論體系及研究方法
目前,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研究主要圍繞景觀生態、文化生態和文化景觀3個主題,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理論體系出發,以生態、歷史、文化、經濟等層面討論民族傳統聚落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表2)。

表2 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聚落研究理論體系、研究方法及核心議題
2.1 景觀生態研究
針對西南地區,景觀生態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觀空間研究。景觀空間研究主要利用GIS、RS為主的空間信息技術為支撐,從聚落的分布格局、空間機理、形態特征以及時空演變等入手,研究聚落景觀的基因信息圖譜、傳統村落景觀管理模式、聚落景觀保護管理信息系統、農村居民點空間變化,以及景觀格局分析等[14-16]。這些分析多考慮比較容易量化的社會經濟資源等客觀因素,而較難兼顧文化等難以量化的主觀因素,缺乏整體觀。
2.2 文化生態研究
西南地區民族豐富多樣,呈“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歷史上,民族文化經遷徙、通商、征戰等互相學習交融,文化產生、變遷、發展,豐富多樣。隨著19世紀以來西方外來文化及現代化的不斷沖擊,民族文化的保護及發展傳承受到挑戰,學者們多專注傳統聚落文化的保護及可持續發展。此地區以民族學、人類學考察為主,多為文化模式及文化變遷研究。布依族的社會變遷的原因歸為技術進步、異質文化的傳播、文化的自調適及城鎮化[17]。文化變遷本身不具備價值度量,變遷可以是正向或者負向的,而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變遷一直追求現代化的目標[17]。旅游發展造成的負向文化變遷,沖擊少數民族聚落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導向、同化民俗風情及民族文化被商品化等[18-20],此類研究多缺乏量化分析,以文獻研究、田野調查為主。
2.3 文化景觀研究
景觀一詞源于德語,意為“被塑造的土地”,表現自然對土地的塑造,德國地理學家奧托·施呂特(Otto Schlüter)將景觀分為“原始景觀”和“文化景觀”,提出景觀形態學和景觀研究是地理學的主題。世界教科文組織將文化景觀定義為“自然和人的聯合作品”,強調自然與人對土地的共同塑造,打開了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新視野[21]。針對中國西南地區的文化景觀研究主要集中在演進及驅動力、遺產保護以及設計策略等方面,將“時間-空間”“物質-非物質”以整體思想進行綜合分析研究,探究少數民族聚落文化景觀演進的背后邏輯[22-24],為未來的規劃設計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
3 研究展望
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的研究吸引了國內外大量學者參與,從近代開始,從地理、歷史、民族、建筑、文化遺產等多學科展開,各學科對聚落研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體系。進入跨學科研究階段之后,學科之間互相吸收融合,在聚落景觀方面,研究從傳統民居建筑、園林研究出發,吸收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擴大研究尺度、廣度及深度。
3.1 中國西南不同地貌類型區民族聚落研究
由于中國西南自然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存在山區民族聚落普遍貧困、社會發展水平低下、經濟落后、人口增長較快、生態環境脆弱等問題,從而導致山區民族聚落的差異。因此,研究中國西南山區民族聚落的差異,揭示其不同的人—地耦合關系規律,尋求山區民族聚落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方法和優化發展模式,對于促進民族聚落發展和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3.2 中國西南民族聚落多學科綜合性研究
西南地區多高山峽谷地形地貌,少數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地域的特殊性,民族聚落景觀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資源—生態諸要素的復雜系統。因此,研究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歷史聚落近現代演進變化、演進模式、動力機制,以及開展自然科學、經濟學、行政管理學以及系統工程學等交叉學科相融合的集成研究等,建立中國西南民族聚落景觀保護體系,能為民族聚落景觀保護、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3.3 中國西南地區新民族聚落的構建研究
隨著國家主體功能區和生態功能區規劃的實施,中國西南地區水電和礦產資源開發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生態脆弱區移民、工程建設移民、移民安置新聚落構建等的人地關系協調過程尤為重要。因此,研究構建新的西南地區民族聚落,構建生產、生活、居住、交通、防災減災等聚落功能,以及民族聚落景觀分布格局、生態過程(功能)和尺度及其3者關系,將為新的人地關系的協調、產業的重塑、生態旅游的引導、新居民社區的組織重構,以及民族聚落景觀的可持續性等提供理論依據。
3.4 經濟發展對民族聚落景觀保護的影響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加快發展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所帶來的人口、耕地(耕作規模)關系的變化,將給民族聚落的空間形態、分布格局等帶來深刻的影響。因此,應根據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的自然環境、發展水平、空間特征等,研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過程對中國西南民族聚落演變的影響因素及其動力機制,預測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的演變趨勢,篩選區域民族聚落的發展模式,并提出民族聚落景觀保護對策。這樣不但可以豐富和完善民族聚落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而且可以為西南地區民族聚落景觀的保護規劃和建設提供理論依據。
3.5 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脫貧策略研究
中國西南地區民族聚落多位于山區,地勢艱險、土地貧瘠、交通不便、自然條件惡劣。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脫貧從建國以來一直是我國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同時,民族聚落具有特色聚落建筑景觀、農業景觀、自然景觀以及豐富特色農業產品等特點。因此,在開展精準扶貧的工作中,在加大基礎建設的同時,旅游扶貧成為日益熱門的選擇;但是,旅游業的激進發展必將在不同程度破壞現有聚落景觀,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開展民族聚落的保護預警系統研究、旅游開發行為的評價反饋機制及環境影響預測等研究,為我國西南民族聚落景觀保護、未來可持續發展、旅游精準扶貧策略研究提供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