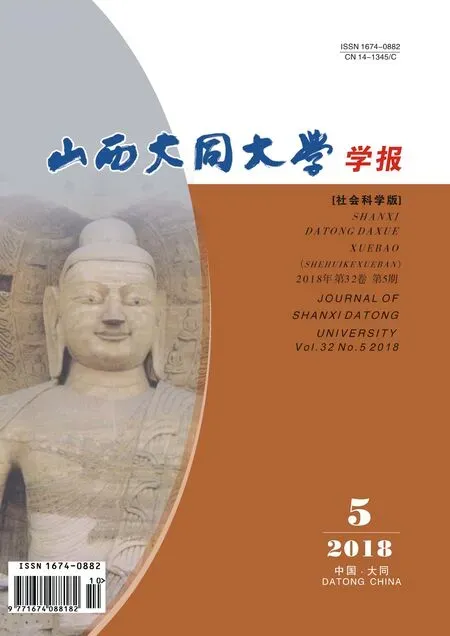農村“信息扶貧”過程中社交媒體的影響與趨勢
張 焱,王立斌,張 磊,王波波,盛 陽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84)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指出,解決好“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2]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規劃》,以及“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和2017年中央1號文件都明確提出,要大力發揮信息在扶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讓信息扶貧成為扶貧工作的強大力量,各社會群體包容性發展,以縮小數字鴻溝。[3]
目前社交媒體已超越搜索引擎,成為互聯網第一大流量來源,二者占比分別為46%和40%。[4]社交媒體由social media翻譯而來,也有人譯為“社會化媒體”。關于social media,普遍認為最早源自美國學者Antony Mayfield在2007年出版的名為What is social media(《什么是社會化媒體》)的電子書。[5]他認為社會化媒體是一系列在線媒體的總稱,這些媒體具有參與、公開、交流、對話、社區化、連通性的特點,賦予每個人創造并傳播內容的能力。清華大學彭蘭教授認為,社會化媒體主要有兩項特征:一是內容生產與社交的結合,也就是說,社會關系與內容生產兩者間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二是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的主角是用戶,而不是網站的運營者。[6]目前對于社交媒體的定義雖然表述不一,但有著共同的內涵,人數眾多和自發傳播是構成社交媒體的兩大要素。學者譚天將社交媒體分為四類:一是平臺型,例如微博;二是社群型,例如QQ群,微信群等;三是工具型,例如滴滴專車等用戶可以享受服務并進行評價的APP;四是泛在型,指將嵌入在各類媒體中的具有社交屬性的內容和服務。[7]
社交媒體作為新的傳播形態,其功能卻早已超越一個媒介工具的范疇,在各個領域都有所體現。例如:學者劉繼群從政治的角度,[8]認為網絡社交媒體積極主動參與網絡政治文化建設,培養了政治文化的公民氣質,引領了政治文化的發展方向;學者張喜艷從軍隊建設方面,[9]探討了社交媒體在美軍軍事領域所具有的信息發布、交流互動、戰略傳播、信息作戰以及危機溝通等五大功能;學者羅賢達以風險社會理論框架下的視角,考察了社交媒體在“3·11”東日本大地震事件的功能。[10]可以說,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民生活的一種必備信息工具,它不是某個領域的專門工具,也不是只為城市人服務的專利,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它也早已開花結果。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口占總人口的50.32%,[11]而農村是我國基層民主自治的重要實踐場所,也是我國諸多改革政策的先鋒。[12]社交媒體在農村的發展雖有障礙,但由于農民對其需求量巨大,也并不遲緩;然而學界對于農村社交媒體的應用與研究,還僅僅停留在硬件[13]或者某些特定群體,而非農村本土居民。例如:學者范瑩瀅以農民工群體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他們在社交媒體環境下的環境認知模式;[14]李智和楊子對女性農民工使用社交媒體的調查;[15]學者韓敏針對社交媒體對農村青年人際傳播的影響進行了研究;[16]田軼赟從推廣農業技術的角度,對農技人員使用社交媒體的現狀調查。[17]可以看出,以農村本土居民為研究對象的調查在學界仍然十分匱乏。
此次調研更為廣譜地著眼于農村本土,研究對象既非農村某一特殊群體,也非在城市的農民工群體,而是農村本土居民本身;不僅希望能夠了解使用社交媒體的那一部分農民,也同樣重視還未使用社交媒體的農民群體。此次調研以湖北巴東縣景家坪村為例,探索社交媒體作為一種新事物,農民的接受狀況,使用動機和作用,以及社交媒體對他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一、研究問題
本文著眼于鄉村本土語境,通過使用問卷調查、案例分析和訪談等研究方法,以湖北巴東縣水布埡鎮若干村落為例,旨在探尋社交媒體在農村“信息扶貧”過程中的作用、趨勢與瓶頸;并針對以下研究問題進行具體回應:①社交媒體在農村的擴散路徑;②社交媒體如何全方位重構村民的日常生活;③農村“工具型”與“泛在型”社交媒體發展潛力與障礙分別在何處;④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面臨的何種困境。
二、研究方法
本次調研使用了案例分析、問卷調查與訪談的研究方法。其中,案例選擇了湖北巴東縣水布埡鎮若干村落,這些村落的村民中包含少數民族、貧困群眾以及較為富裕的村民,異質性較大;且各個村落經濟水平差異懸殊不大,有一定的代表性。問卷設計分為兩部分,分別針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與“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回收有效問卷共93份,其中30.11%的填寫者屬于“不使用社交媒介”的村民,“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占到67.89%。

表1 人口學統計信息
為了能夠更好地反映研究問題中的因果機制,本文以方便抽樣的方式,在景家坪村選取23戶村民進行了重點采訪,力求信息異質性最大化,訪談以信息飽和為終點。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組成的“湖北巴東暑期實踐”隊的隊員在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8月3日,使用統一的“農村互聯網、社交媒體使用情況調查研究訪談報告表”入戶對村民進行半結構化訪談,并整理訪談記錄。隊員一般在村民家中圍繞三個研究問題與村民進行交流,每個問題包含若干子問題。被訪者的年齡、性別、家庭以及工作狀況差異較大,以此保證較好的信息異質性。
三、發現
(一)社交媒體在農村的擴散路徑
“人際交流”與“生活消費”是社交媒體在村民中的“擴散動力”。通過“五級量表”對一些題項進行態度測量,60%以上的被訪者“愿意向親友推薦微信、QQ等社交媒體”,54%的被訪者“通過網絡繳費購物”,這兩項原因是社交媒體在村民中最主要的“擴散動力”。
景家坪村向女士今年56歲,她家雖然是貧困戶,但三個女兒中的兩個都用手機上網,在接受訪談時其大女兒稱,上網購物會便宜很多,買東西會比市場便宜一半。網絡購物基本是信得過的。
39歲的被訪者景碧華認為網絡會讓家人關系更加親密,因為愛人在外打工,主要用手機和愛人聯系,視頻聊天等。用微信聯系,召集朋友打牌也很方便。因為家庭氛圍緣故,被訪者經常和女兒聊天,女兒也愛和被訪者說每天在學校發生的故事,所以現在有手機也不會影響家人之間的關系。
36歲的張世勇則更多受到周圍親友的帶動使用社交媒體,他說:“家中自己、妻子、兒子和女兒都會上網,只有老人不會上網。村里使用社交軟件的人比較多,自己通過觀看別人操作學會了使用社交軟件。”
將“性別、年齡、收入、學歷”分別與“是否使用社交媒體”進行交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性別”變量對擴散影響不大。被調查者中,男性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數為70.59%,女性為69.05%,社交媒體在男、女性群體中使用率并無顯著差異。
2.“年收入”與擴散程度呈正相關。年收入越高,使用社交媒體的可能性越大:年收入最低在5000元以下的被調查者中依然有62.5%的人會使用社交媒體,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上的人群會100%使用社交媒體。
3.在成年人中,“年齡”與“社交媒體”擴散呈負相關;“學歷”與“社交媒體”使用呈正相關,但在16-25歲的年齡段的答題者中,無論什么學歷的村民,都會使用社交媒體:
4.擴散之后在使用者中粘度高,93.85%的使用者“每天使用時間最長的信息媒介”是“手機”。
(二)社交媒體對村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重構
使用網路解決問題或維權的意識在農村已經生根發芽 “使用網絡尋求幫助”是村民除“向上級領導反映”之外,“在遇上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或需要維權時”認為最為有效的解決辦法,表現出村民已經有了運用互聯網尋求實際生活中困難解決方式的意識。
31歲的村民劉小顏則更偏向線下渠道解決困難,但她曾經因為一些糾紛無法在政府得到解決而上網發帖求助:“自己曾經在土豆網、百度上發布關于車禍的求助信息,因為政府解決不了,所以上網發了帖子。”
做茶葉生意的村民鄧貴愛認為,網絡使得信息流通更加快速,自己做生意也經常在網上了解茶葉的價格動態,他有一個茶商的QQ群,全州的茶葉價格都能知道。現在他在生活中遇到不懂的事情或困難,一般都會先在網上查。
一位18歲還在上學的被訪村民鄧梅敏稱:“使用微信頻率最高,經常發朋友圈。每天做了什么,好看的風景等記錄自己的生活內容會發到朋友圈,基本上一天一到兩條;也會點贊。評論、轉發別人的朋友圈內容,遇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比如搞笑的內容都會轉發,還比較喜歡描寫親情的文章。”對于不懂的事情,被訪者會先問同學,然后上網查,經常上百度。“有時發現有些問題網上的觀點和自己不一致,但覺得網上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使用社交軟件做的最多的事”里,前三名分別是“與他人聯系”、“交友聊天”與“瀏覽新聞”。
村民“獲取新聞最主要的方式”已發生重大轉變。調查顯示,在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中,“靠朋友圈轉發”與“網站推送”已經成為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二者總和達83.08%,非互聯網渠道僅占6.15%:鄒世國是原來景家坪村村支書,今年60歲,他在接受訪談時稱,“用手機上網最常做的事情是看新聞,主要使用騰訊新聞。一般是騰訊推送什么新聞就看什么新聞,自己很少搜索,對本地新聞比較關心。”除了看新聞就是用微信,鄒世國表示會用微信朋友圈轉發關于國家政策、國家大事的新聞,會評論別人的朋友圈,對一些時事新聞也會在網上發表自己的看法,但頻率不高。他認為互聯網可以提供致富信息,能夠幫助村民致富。
(三)“工具型”與“泛在型”社交媒體在鄉村的發展潛力與障礙
按照學者譚天對社交媒體的四種分類,只要是基于“評價”的網絡服務,例如網購等,都是具有社交媒體屬性;“評價”即“口碑”,用戶運用挑選網絡服務與內容的主要參考正是通過其社交屬性獲得的。[18]
此次調研可以看出,村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已不再僅局限于類似微博的“平臺型”社交媒體和類似QQ群、微信群的“社群型”社交媒體;而進一步對類似淘寶、大眾點評等的“工具型”社交媒體與類似視頻、直播網站中的“泛在型”社交媒體表現出越來越高的需求。在村民目前使用的“工具型”與“泛在型”社交媒體中,網購與追劇最具有代表性,成為最有潛力的門類。潛力一方面意味著此種服務或內容需求量大,受村民歡迎;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滿足農村此種服務與需求仍然面臨許多障礙。
“快遞”等基礎服務是農村發展網絡經濟的瓶頸。村民熱衷“網購”,試水“網店”,但存在快遞難以送到等問題。
鄧貴愛從12年開始接觸電腦,近兩年越來越發現電腦的作用很大,這主要體現在做生意和生活中,他說:“現在互聯網已經和生活息息相關。”鄧貴愛今年在網上買了一個大冰柜,比實體店便宜1000元。圍龍壩村的鄧軟翠稱,“家人會用手機交費,不用跑腿了”。
村民譚艷春今年35歲,她剛做一個月的農村淘寶,還會在電腦安裝培訓平臺的軟件(淘寶),她說:“以前經常在網上買東西。外面生意不好做,在鎮里做實體服裝生意也不好做,于是就想在網上開店擴大收入。”
網購方面雖然方便,但村民仍然有一些痛點需要解決,例如交通問題,村民鄧玉芝談到:“我平時會使用淘寶購物;用微信、支付寶繳納生活費用。但物流不能通達到村里,加之網絡信號還不夠流暢,希望這兩方面能得到改善。”
六成上網村民“追劇”,但內容生產很少針對農民。調查中,上網村民在使用媒體娛樂時,有64.62%的人選擇看電影電視劇,僅次于聊天交友的67.69%。隨著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興起,電視劇觀看平臺逐漸從傳統的電視機媒體向互聯網終端轉移,這一技術的變革沖擊了原有的電視劇觀看方式。[19]網上追劇的社交互動性不僅體現在用戶的直接評論、點贊與彈幕等方式,[20]也體現在間接通過其他“平臺型”或“社群型”社交媒體進行分享與傳播。
網絡“電視劇”等文化產品在農村“輿論陣地”作用未被重視。農村人口在我國比重大,也是精神文明建設與主流價值觀傳播的主陣地。調查顯示,六成上網村民熱衷“追劇”,這無疑是主流先進文化、中國本土特色文化在農村進行傳播的良好抓手,然而目前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反映農村現實狀況的影視作品數量少、質量參差不齊引人擔憂。[21]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注重現實生活、立足人民群體、把握時代特征”,創作我國本土文化內核深入挖掘和加強城鄉文化融合互動的中國農村題材電視劇的創作。
(四)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所面臨的困境
“日常生活不需要”、“太復雜不愿意學”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費用太高”、“沒有人教”等原因 年齡大和貧困的村民占不使用社交媒介的村民的大多數,貧困群體往往文化水平比較低,甚至“不識字”,這也是使用社交媒體的一大障礙。
超過60%的不使用者有意愿學習使用,是潛在使用者。未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中有60.71%表示“以后會考慮使用手機、電腦等上網”。目前這些村民的主要娛樂方式與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完全不同,他們中89.29%的人選擇“看電視與聽廣播”的方式進行消遣。
65歲的鄧中俊稱,家里除了自己和老伴,其他人都會上網。自己用手機只是打電話,聯系家人。無法學習使用的原因是自己年紀大了且視力不行,如果身體條件允許還是想學的。
村民金遠清從來沒有接觸過社交媒體,家庭情況確實比較困難。家中孩子都處在上學階段,家里沒有網絡設備,也沒有人教。她的情況屬于貧困戶中比較普遍的一種情況,主要是經濟能力無法支持新媒體的使用,同時他們也覺得現在的生活與交流很適應,并不覺得有必須使用新媒體的動力。另外被采訪者不識字,也加大了上網的難度。
不認為社交媒體讓他們與親友疏遠,但對“是否愿意給孩子買手機”的議題分歧最大。用五級量表對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進行部分題項的測試,結果顯示,他們并不認為“社交媒體讓他們與親友疏遠”,且他們的親人里基本會有“社交媒體使用者”,最有分歧的題項是“是否愿意給孩子買手機”。
37歲的戚艷認為,社交媒體給大家的溝通帶來了方便,幫助大家更好地交流。不只是自己與家人之間,也適用于村民之間。不認為會有什么負面、消極的影響。村民劉小顏則認為網絡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家人的關系,有時大家各玩各的,但關系也沒疏遠。
村民譚文順認為,網絡、手機對年輕人和兒童還是有影響的,孩子看到大人玩手機也會玩,有時會存在疏遠家庭成員關系的情況。
不使用社交媒介的村民正在被“虛擬社群”邊緣化,喪失參與公共生活、信息資源分享的重要渠道社交媒體正在重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生態。調研村落已經有了許多“QQ群”、“微信群”,村民可以通過這些群獲得政府的政策信息,互通有無;因此社交媒體在農村正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公共參與渠道,部分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在訪談時表示他們對村里的會議、政策等很少知道。
據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鄧玉芝介紹,她、丈夫和女兒都會使用智能手機上網,且手機都安裝了微信等社交媒體。景家坪村使用智能手機的村民較多,其中大部分都會使用社交軟件,以微信為主。該村有“景家坪村相親相愛微信群”,里面經常會發布招工信息。
然而不使用社交媒介的村民不但難以知道“招工信息”等信息資源,甚至對自身利益切身相關的政策信息也十分模糊。調研員劉王恢在訪談日志里這樣寫道:
第一家訪談的是43歲女戶主金遠清,因為家庭困難她沒有使用社交媒體的經歷。訪談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問題是,該戶主認為自己家庭達到了貧困戶標準,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村委會報到鎮里的名單里并沒有自己家庭,沒有評上貧困戶,因此很多貧困戶的優惠政策沒有享受到,也沒有評上低保。而村里一些沒有資格評選上的反而評上了貧困戶。當問到有資格而沒有評上貧困戶的家庭大概有幾戶時,回答是大約95%的都評上了,剩下5%本應該評上但沒有。但是當問到為什么沒有被評上貧困戶時,該戶主卻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也沒有聯系村里的扶貧干部,原因是根本不認識村里的扶貧干部,只是知道有這樣一個干部存在。
農村的基層民主在實踐過程中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它仍然是我國基層民主實踐最為充分的場所之一,社交媒體在基層民主政務公開,溝通信息,表達意見和整合輿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是基層民主政治的助推器。越來越多的村民正在通過這一渠道進行資源共享與公共事務參與,表達自己的態度以及爭取合法權益,促進村支兩委工作的公開透明。
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中一大部分是貧困的村民,他們信息意識、維權意識比較淡薄,而“信息扶貧”的政策還在路上,以致于他們的權利容易受到侵犯。保障他們的信息權,滿足他們的信息需求,將成為“信息扶貧”走完“最后一公里”的關鍵瓶頸;也是完成《“十三五”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規劃》,讓信息扶貧成為扶貧工作的強大力量,促進各社會群體包容性發展,縮小數字鴻溝的重要績效。
四、結論
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規劃》,以及“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和2017年中央1號文件,都明確提出,要大力發揮信息在扶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讓信息扶貧成為扶貧工作的強大力量,各社會群體包容性發展,以縮小數字鴻溝。[22]
中國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深刻影響著從城市到農村的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無論從東方視角,還是西方視角[23],相關研究對于農村的重視程度都遠遠小于城市。我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如果說因為曾經部分學者對農民在互聯網接觸方面有“信息失聯”的固有印象,[24]導致了學界認為對中國農村互聯網使用、尤其是社交媒體使用狀況研究的必要性不足,則是忽略了近年來農民對以社交媒體為主的互聯網服務迅猛增長的需求,以及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理念后,“信息扶貧”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在廣大農村逐步推進而取得的巨大成績。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訪談及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對湖北省巴東縣水布埡鎮的幾個村子進行了以“互聯網、社交媒體使用狀況”為主題的調研。全方位地了解了當地農村對于社交媒體的使用狀況。雖然因研究條件有限而只能做局部調研,無法概括全國所有村落的情況,但因其同時包含地處偏遠、民族雜居、經濟體量屬于中游水平等特點,故具有全國一般村落的普遍性特征,研究結果對于普通農村的社交媒體使用狀況具有一定的等價參考意義。
此次調研中,發現社交媒體在村民中間的“擴散”程度與年齡負相關、與收入正相關,但與性別無關,擴散動力來源于自身需要和圈子推薦,使用者普遍粘度較高并愿意將社交媒體向親友“二次擴散”。雖然使用社交媒體的原始動機是聊天交友,但在使用過程中社交媒體還具有讓村民“獲取新聞”、“追劇”、“購物繳費”及“娛樂游戲”等功能。。
“快遞”等基礎服務是農村發展網絡經濟的瓶頸。具有社交媒體屬性的網絡服務也越來越受村民歡迎,“工具型”、“泛在型”社交媒體在廣大農村地區發展具有潛力,目前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硬件服務還未滿足需求。
網絡“電視劇”等文化產品在農村“輿論陣地”的作用未被重視。二是軟件服務對農村關注不夠,如針對農民觀眾的電視劇內容生產的質與量都不足,這既是互聯網企業在農村地區投資的黃金區域,也是政府和社會縮小城鄉“信息鴻溝”,傳播主流文化的良好抓手。
使用網路解決問題或維權的意識在農村已經生根發芽。村民很大一部分會使用互聯網搜索信息,“在遇上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或需要維權時”,“使用網絡尋求幫助”是答題者認為“向上級領導反映”之外最為有效的尋求幫助的途徑,雖然利用社交媒體“網絡維權”只有少數村民實踐過,表明村民已經有了運用互聯網尋求解決實際生活中困難的意識。
農村網絡滲透還有很大空間與潛力。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更是不能夠被忽視的群體,他們往往是年齡大或者貧困的村民,“想學而沒人教”、“文化水平低”、“費用太高”及“沒有設備”是阻礙他們使用網絡及社交媒體的主要障礙,但他們中有60%以上仍然希望學習使用。這部分村民并非排斥網絡和社交媒體,他們同樣認為網絡、社交媒體對生活有一定幫助,甚至在一些貧困戶中,家長會支持子女“使用智能手機”。非使用者和使用者的“新聞獲取”方式有著根本差異,“看電視、聽廣播”是他們的主要休閑方式。
社交媒體正在重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生態。調研村落已經有了許多“QQ群”、“微信群”,村民可以通過這些群獲得政府的政策信息,互通有無,因此社交媒體在農村正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公共參與渠道,部分不使用社交媒體的村民在訪談時表示他們對村里的會議、政策等很少知道,他們在客觀上正在被新型“虛擬社群”邊緣化。因此保障未使用者的信息權,滿足他們的信息需求,是“信息扶貧”“最后一公里”的關鍵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