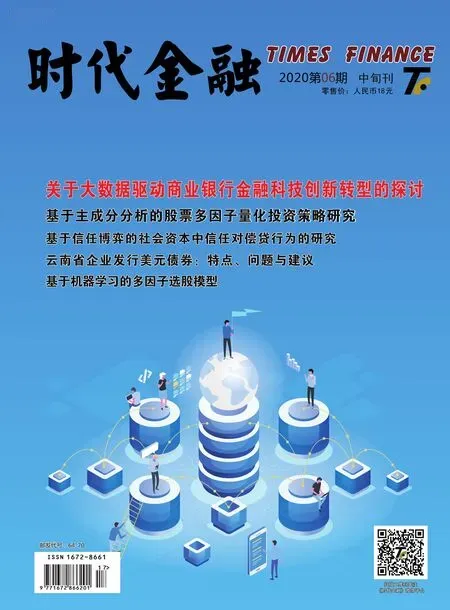澳大利亞消費者價格指數與澳元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李思影
【摘要】首先,本文以2005年5月到2016年1月期間澳大利亞名義匯率同澳中兩國消費者價格指數為樣本,運用VAR模型研究二者差值的關聯性。接著利用VECM模型研究同時期的澳大利亞名義匯率同澳大利亞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的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匯率呈負影響關系,即當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時,澳元匯率下跌;而澳元升值時,消費者價格指數也會隨之下降。與此同時,兩變量間關聯密切,且消費者價格指數是澳大利亞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其影響系數遠遠大于其他變量(GDP增長率、利率和國際收支)。
【關鍵詞】匯率 消費者價格指數 VAR模型 VECM模型
當今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各個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的首要目標便是追求消費者價格水平的平穩,而穩定的價格水平也是一個國家實現均衡經濟的重要保障。消費者價格水平的變動也同匯率的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購買力平價理論僅討論認為,價格水平的變動受到匯率的影響。但事實上,匯率變動也會對價格水平產生反向的影響。
近年來,國內學者在匯率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宏觀經濟環境,將通貨膨脹環境、貨幣政策與匯率的波動影響聯系到了一起,以此檢驗宏觀經濟環境對匯率影響因素的關系。國外近年來的一些研究,逐漸將匯率傳遞與宏觀經濟環境聯系到一起,藉以考察宏觀經濟環境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影響。由于變量間存在的復雜雙向因果關系,采用非結構性方法建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更加廣泛而合理。因此本文首先采用VAR模型研究2005年5月到2016年1月期間澳大利亞名義匯率同澳中兩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差的關聯性。接著又利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同時期的澳大利亞名義匯率同澳大利亞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的關聯性,并做了進一步的套利預測分析。
一、數據選擇與說明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線性相關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模型中包括4個變量,分別為:ExR、CPI、IR、GDP、BOP。其中,ExR表示澳元對人民幣名義匯率,CPI代表澳大利亞與中國兩國的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之差,GDP為澳大利亞和中國的國內GDP增長率的差值,IR代表澳大利亞和中國兩國的貸款利率之差,BOP代表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的外貿差額。
為了保證本文使用的時間序列的穩定性和避免謬誤回歸,首先使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數據是否平穩,本文使用的五個變量(匯率、消費者價格指數、利率、GDP增長率、國際收支)中原序列的匯率、利率和國際收支,原始序列不平穩,使用一階差分后的序列發現數據變為平穩。之后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與消費者價格指數和其他控制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判斷,檢驗結果證明國際收支(d_BOP)與匯率(ExR)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原因,這表明國際收支和中澳兩國匯率對互相的將來變化都有助于解釋,在后面的建模分析中需要繼續加強對該因素的考察。匯率是利率的格蘭杰原因,但利率卻不是匯率的格蘭杰原因。GDP增長率(GDP(-1))、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匯率互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二、實證結果分析與解釋
(一)VAR檢驗
VAR檢驗得出,匯率的滯后一階對自身有正影響,系數為0.0990而且顯著性水平很高,滯后二期對自身的影響顯著為負,影響系數-0.0233。可能原因為第一年的匯率上升會在下一年釋放,但在第三年后得到修正。CPI對匯率的影響是顯著的,且呈負相關。當澳大利亞和中國的CPI差距拉大時,即澳元的購買力減弱,澳元對人民幣匯率下降。依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澳大利亞的貨幣走弱。利率、國際收支和GDP增長率對匯率的影響能力都很弱。對匯率的影響參數都在0.03以下,說明利率、國際收支和GDP增長率對匯率只有少許的影響。由此可見,利率、國際收支和GDP增長率并不是影響匯率波動的主要原因。其中,利率、國際收支和GDP增長率都對匯率有正影響。
同時,澳大利亞CPI的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對自身有負影響,且影響因素分別為0.844和0.069。這說明第一年的CPI會對下一年的CPI起推動作用,但會在第三年后得到修正。并且CPI對匯率影響顯著且為負。當澳大利亞的CPI下降時,表明澳元的購買力上升,按照購買力平價理論,澳大利亞的貨幣應走強,即澳元升值。
(二)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
基于VAR模型,這里以國際收支為例,對國際收支和匯率進行方差分解。通過脈沖響應圖能夠清晰得出澳元對人民幣匯率對國際收支的沖擊在不同時期的脈沖響應以及國際收支。對國際收支而言,當一個單位的沖擊發生后,澳元匯率自身出現正反應,隨后出現快速增長,在第二期就達到最大值約為0.055%,隨后開始衰落逐漸減緩,直到在第六期達到最小值約為0.005%。隨后逐漸趨近于0.02%。表明當澳大利亞國際收支在受到外部的沖擊后,會快速傳遞給澳元匯率,給匯率帶來同向沖擊。
方差分解表結果表明匯率對國際收支的解釋力度較低。而國際收支對匯率的貢獻相對與前者較大且幾乎不存在滯后效應,第一期到第二期出現了較大幅度增長,在第二期開始之后一直較為穩定。總的來看,二者之間的解釋力度均較低。
(三)VECM模型
VECM結果可得,澳大利亞的CPI對澳元匯率的影響是顯著的,且呈負相關。當澳大利亞的消費物價指數下降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即澳元的購買力上升,澳元匯率應走強。
澳大利亞的貸款利率和中國的貸款利率對匯率的影響是顯著的,分別是正影響和負影響,但對澳元匯率的影響都很弱,其系數都在0.1以下,即當利率波動10%對澳元匯率的影響也只有1%。因此,兩國貸款利率并不是匯率波動的主要因素。
當澳大利亞貸款利率上升,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導致營業利潤下降,于是企業生產積極性下降,因此澳大利亞宏觀經濟增速減弱,最終澳大利亞外貿-出口下降導致貨幣需求下降,澳元幣值下降,即澳元匯率貶值。對于中國貸款利率則恰好相反。
(四)套利
通過預測值和實際匯率的誤差對比,本文發現預測模型能夠有效的在短期范圍內對澳元走勢進行預測,且誤差在可控范圍內。不過,若想要對澳元匯率進行長期的預測,則該模型會出現較大誤差,與實際值偏離幅度較大。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匯率呈負影響關系,即當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時,澳元匯率下跌;而澳元升值時,澳大利亞消費者價格指數也會隨之下降。兩變量間關聯密切,且消費者價格指數是澳大利亞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其影響系數遠遠大于其他變量(GDP增長率、利率和國際收支)。而且澳大利亞當月消費者價格指數會對下一期的數據有釋放效應,但會在第三年后獲得修正。
從政府角度而言,澳元的貶值使澳大利亞國家經濟競爭力削弱。同時,強勢的澳元政策也會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拖累。澳元的升值會加劇經濟的下行壓力,進而重挫本已受傷的澳大利亞礦業。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放緩,對澳大利亞經濟和澳元匯率的沖擊也會進一步隨之加大。對于澳大利亞政府而言,澳元的匯率政策將會是個兩難的問題。對企業而言,尤其是澳大利亞本土企業。面對政府調低現金利率使澳元貶值的經濟政策,隨之導致的進口成本上升,將會使本土產品市場競爭力下降。企業為保持原有利潤空間,被迫將成本壓力轉移給下游消費者。而消費者面對上升的價格,也許會放棄這些產品,進一步導致本土企業的生存危機。對普通民眾而言,本土商品的價格上漲以及原本廉價的中國商品的售價上升,將會加重普通民眾生活負擔,降低他們的生活質量,進一步加重他們對未來經濟的悲觀預測。
由于人民幣貨幣政策身兼數任,并不利于制定一個目標明確的貨幣政策。結果導致了治理通貨膨脹效果差強人意,本文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除消費者價格指數外,匯率對其他變量傳遞效應總體較小,因此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該突出其單一功能性,發揮術業有專攻的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