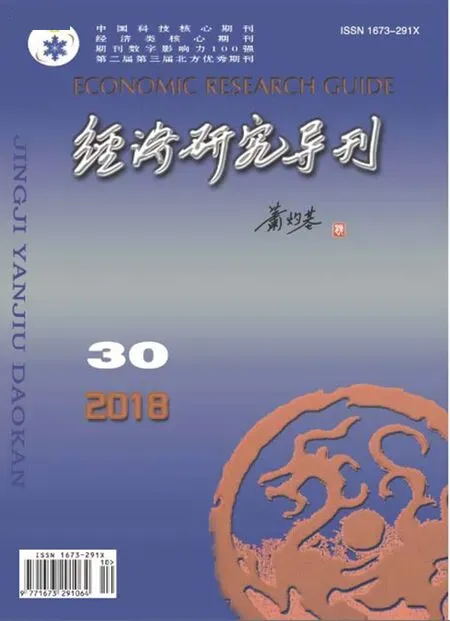河南省財稅政策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研究
趙天宇
(河南工學院經濟貿易系,河南 新鄉 453003)
一、河南省產業結構與稅收發展現狀
1.河南省經濟與產業結構現狀。近年來,河南省經濟始終處于平穩增長態勢,地區產值由2000年的5 052.99億元上升到2016年的40 417.79億元。在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同時,河南省三次產業結構得到逐步優化。截至2016年末,河南省三次產業產值分別為4 286.21億元、19 275.82億元、16 909.76億元;三次產業貢獻度分別為5.9%,43.5%,50.7%,同期三次產業就業人數分別為2 583萬人、2 056萬人、2 088萬人。相對2000年河南省三次產業就業人數的3 564萬人、977萬人、1 031萬人可以看出,二十年來河南省經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的同時引發了勞動力產業間的顯著流動。目前,第二、第三產業是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三次產業吸收就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64%、17.5%、18.5%,轉換為當前的38.4%、30.6%、31%。河南省已由傳統的農業大省逐步向工業與服務業轉化(數據來源于《河南省統計年鑒》)。
2.河南省各項稅收現狀。1995—2008年,營業稅是河南省各項稅收的主要構成部分。營業稅數額由1995年的22.78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209.55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20%。其間,營業稅與增值稅處于同升狀態,營業稅增加說明新開辦的企業數在增長,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經濟主體數量大幅增加。增值稅增長源自企業進項與銷項業務量的同步增長,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開改與加入世貿組織后河南省經濟增長顯著,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由此帶來稅收增長。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我國政府雖然審時度勢做出了積極應對措施,但外部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較為明顯,河南省也不例外。2008年河南省增值稅出現了明顯的拐點,且當年的增值稅增速已由此前的超過20%下降為18%。由于經濟運行存在時滯效應,尤其稅收是經濟事項發生后的事后征集,因此2009年的稅收數據表現更為明顯,2009年河南省增值稅增速再次大幅下降為負數(-8%),納稅額由2008年的157.89億元下降為2009年的140.82億元。經過一年調整后,2010年增值稅回到危機前2008年持平水準,納稅額為155.79億元。由此可以推斷,危機后兩年時間里河南省經濟經歷了下滑再上升的過程,兩年時間完成了對負向沖擊的反饋與修復,到2010年經濟再度回到危機前水平,此后直到國家推行“營改增”之前,增值稅增長始終處于緩慢狀態,意味著制造業全行業增長低迷,企業進銷業務增長緩慢。而金融危機之后,營業稅卻始終處于快速增長狀態,除2008年當前增長速度為14%外,危機后直到“營改增”前河南省營業稅增速始終在20%附近,有些年份超過25%。營業稅的納稅性質決定了此期間企業稅負日益加重,增值稅與營業稅的背離走勢是對全省經濟運行的真實寫照。2014年是兩類稅收的分水嶺,這是“營改增”帶來的改變,2014年開始營業稅與增值稅形成了明顯的“剪刀差”,營業稅大幅度下降,增值稅快速上升。在“營改增”的推動下,河南省宏觀稅負結構已發生了明顯變化。
二、相關文獻綜述
經濟增長是稅收增長的源泉,反之,財稅政策又作用于經濟增長與結構優化。新常態下結構調整優化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所在,現有財稅政策作用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考察總量財稅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另一類是針對不同稅種稅收調整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
1.總量財稅政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財稅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日本沒有受到財稅政策支持的產業發展大多較為成功,而那些受政策管束較多的產業發展卻受到了限制(竹內高宏,2002)。我國財稅政策通過介入資源配置而作用于企業決策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儲德銀、建克成,2014)。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顯著,財政收入結構政策對短期和長期產業結構調整都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應(宋來,2017)。安苑、宋凌云(2016)在考查財政結構調整對產業結構影響時發現,在制度約束影響下,稅收結構調整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遠優于補貼的影響。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存在“拉弗效應”,當結構性減稅與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一致時,就能夠達到財政增長與產業結構優化的共贏的效果(孔令池等,2017)。地方稅收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存在顯著的結構效應,直接稅比間接稅對產業結構優化作用更為明顯。
2.不同稅種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馮彥杰、婁峰(2018)運用模擬方法,分析企業增值稅對宏觀經濟及其結構的影響,發現降低增值稅有利于實際GDP增長。申廣軍等(2016)基于微觀數據的研究發現,降低增值稅稅率可以促進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進而改變經濟結構,且這一作用效應在私營企業、非出口企業以及中西部地區更為顯著。許偉、陳斌開(2016)以增值稅轉型所覆蓋的行業為研究對象發現,降低增值稅可以大幅度促進私人部門投資,減稅措施對穩增長調結構意義重大。周四軍、張平(2015)基于CGE模型的模擬研究發現,全面實行增值稅改革是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力工具。全行業統一稅率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胡怡建、田志偉(2014)研究認為,“營改增”具有顯著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何濤(2015)認為,應該降低科技服務產業的所得稅和流轉稅,以促進科技服務業發展為路徑推動產業結構優化。
對已有成果的梳理中發現,現有研究主要以全國樣本為研究對象考查稅收負擔對經濟結構的影響,而以地區為對象的研究則較為鮮見。本文則河南省以研究對象展開財稅政策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的實證研究,以此為基礎提出優化河南省稅負結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的針對性對策建議。
三、稅收對河南省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實證分析
1.河南省產業結構優化指標測算。產業結構優化包括結構高級化與結構合理化兩方面。首先,產業結構高級化(IDH)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的升級過程中,隨著工業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推進,總體看“經濟服務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同時也包含服務高端化的內涵,根據三大產業的演變規律,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發展已成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走向。因此,本文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三大產業產值之和的比例作為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指標。其次,產業結構合理化(IDR)要表現在生產要素投入產業發展的利用率上,本指標的設計也是從要素投入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協調程度角度進行的。依據上述理論,本研究中對產業結構優化指數界定如下:

該值越小產業偏離度越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越低。其中,Yi表示第i個產業的產值,Li表示第i個產業就業人數。
2.基礎指標的價格平減處理。由于基礎數據中的產業產值指標為以上一年為基期價格進行統計核算,而就業人數則是統計每年的實際值,因此在進行指標測算前需對產值指數進行以固定年份為基期的價格平減處理,本研究中選定以1999年為基期進行產值平減處理,以得到歷年河南省三次產業的實際產值。
3.稅負相關指標構建與其變量選取。本研究中擬檢驗河南省不同稅種稅負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因此構建如下兩個反映稅負的指標:直接稅負(ZT)=(直接稅收總額)/(地區國內生產總值);間接稅負(JT)=(間接稅收總額)/(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上述基礎數據均來源于歷年《河南省統計年鑒》。
在稅負影響產業結構的分析框架下,財政支出、創新技術應用等因素也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產生重要影響。主要指標的設計如下:財政支出指標(CZ)用地區政府支出占地區GDP比例表示;技術創新應用指標(CX)用地區技術市場交易額與地區GDP比例衡量。
4.計量模型設定見式(1)和式(2)。

第二產業結構逐年優化,第三產業結構呈現U型特征,近年來河南省第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逐步趨同。第一產業偏離度較為穩定,勞動生產率始終處于較低水平。
5.模型估計結果分析(見下頁表)。首先分析2000—2016年期間各變量對河南省產業高級化的影響。由表中第二行的檢驗結果可知,樣本期間間接稅收(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對河南省產業結構高級化起到促進作用。且作用乘數為7.53,直接稅收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未產生顯著性影響。地區財政支出以及創新應用對河南省產業結構高級起到明顯促進作用,從作用效應看,河南省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乘數為1.67,即財政支出每提高1個單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提高1.67。創新應用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促進作用則更為顯著,作用乘數為52.97。可見,直接稅(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并未對產業結構高級演進產生顯著性影響。因此,優化產業結構的著眼點應放在間接稅的調整上。
表中第三行的檢驗結果可知,以產業結構偏離度作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代理變量研究發現,間接稅導致河南省產業偏離度上升,作用乘數為280.9,但由間接稅二次項系數為負且在1%條件下顯著可知,間接稅對產業結構偏離度產生非線性影響,樣本期間間接稅對產業結構偏離度的作用效應表現為初始隨著間接稅收的增長產業結構偏離程度提高,即產業發展向非均衡偏離;但間接稅繼續提高,卻又對產業非均衡發展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

產業結構優化影響因素模型估計結果
表中第四行以第1產業偏離度為產業結構合理化代理變量的檢驗結果可知,樣本期間河南省間接稅收對第一產業結構偏離度仍然發揮著非線性影響,即隨著間接稅收的增長第一產業偏離度先上升再下降。但是,直接稅以及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技術創新應用等因素對第一產業偏離度未產生顯著影響,說明第一產業結構合理化受間接稅影響最為明顯。這啟發我們,將優化第一產業結構的財政著眼點落后在間接稅負調整上。
表中第五行以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為產業結構合理化代理變量的檢驗結果可知,間接稅稅負對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同樣產生顯著非線性影響,即隨著稅負增加第二產業結構偏向非均衡發展態勢,但間接稅負持續增長中又再次使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降低,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此外,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水平對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起到抑制作用,創新應用對第二產業偏離度起到推動作用。即在樣本期間,地方政府通過財政支出手段使河南省產業結構逐步向均衡方向發展。這與以往的直接感受可能有所不同,研究中我們并未找到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導致產業結構惡化的證據,反而為結構優化起到了推動作用。結合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檢驗結果可以概括為:樣本期間,河南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推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合理化,而創新應用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起到促進作用,卻導致了更高的產業偏離度。結合河南省經濟發展背景可知,創新的發生與應用不可能在各行業中均等化,反而由于某些創新性行業的快速發展導致要素快速流動,因而表現出由此帶來的產業結構偏離均衡,這種非均衡呈現出的是部分優質產業發展較快,而某些傳統行業發展滯后。當前應該采用有效手段選擇合宜途徑使所有行業都向創新驅動模式發展,使產業偏離度再次降低。即我們得到的有益結論是希望創新應用同樣對產業結構偏離度產生非線性影響,由初始的拉高偏離度再到產業再平衡,這將是產業發展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表中最后一行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均未對第三產業偏離度產生顯著影響。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選用河南省2000—2016年經濟增長、分產業就業、分類型稅收收入等數據,在構建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指數的基礎上,分別實證檢驗此期間河南省財稅政策對經濟結構優化產生的影響,得到了以下主要結論。
1.總體上看,財政支出對河南省產業結構高級與合理化均起到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創新應用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起到正向作用,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發揮抑制作用。直接稅促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間接稅對產業高級化無顯著性作用。
2.分稅種看,兩種稅收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均表現出非線性影響,但作用方向卻截然相反:直接稅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呈倒U型,即存在最優的直接稅負可以使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達到最高,而間接稅稅負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呈現U型影響,即存在最劣的間接稅稅負使得要素流動趨于固化。
3.分產業看,第一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受間接稅影響,且存在最優間接稅負能夠使第一產業合理化程度達到最高,兩項所得稅未對第一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顯著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創新應用均未對第一產業合理化產生顯著性影響。第二產業結構合理化受間接稅影響顯著,同樣存在最優間接稅負可使第二產業合理化水平達到最高,同時財政支出與創新應用對其作用截然相反,財政支出促進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創新應用則抑制要素流動。第三產業結構合理化與上述各變量均未呈現顯著性關聯。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首先,大力推進創新發展與創新應用。充分發揮創新在產業結構優化中的促進作用。雖然創新應用在短期抑制產業結構合理化,但創新發展可通過推動新興產業發展進而提高新經濟的比重并最終實現經濟結構優化。
其次,推進所得稅改革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由于存在最優的直接稅稅負可使得產業結構合理化達到最高水平,因此今后河南省可通過推進企業所得稅改革的途徑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最后,完善流轉稅稅負,促進第二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不斷提高。間接稅對第二產業的要素流動影響最為顯著,而第二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核心所在,因此應通過不斷完善流轉稅稅負促進第二產業結構優化,進而實現經濟結構的整體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