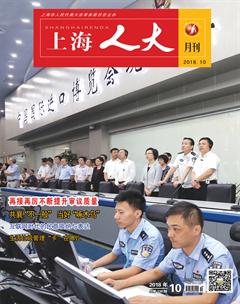“完美”的信訪程序究竟傷害了誰?
林茗 樓祝利 金四軍
“訴訪分離制度”始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改革信訪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的精神要求。這一制度性的變革對理清蕪雜的信訪矛盾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意義,對于從根本上改變“信訪不信法”,確立司法終局性,屏蔽外部權力對司法的干預和影響大有裨益。然而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存在被泛用甚至濫用等問題,需要對制度設計和實施進一步完善。
2017年9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信訪辦公室接待了一位來訪人。來訪人翁某72歲,女性,系新疆返滬知青。來訪人反映其家在原金山縣漕涇鎮阮巷有2間房屋以及九分面積宅地基的使用權(有1951年人民政府頒發的房屋土地所有權證)。20世紀60年代,其中的1間房屋及九分地基被金山區金衛供銷合作社(原金山縣漕涇供銷合作社,以下稱“金衛供銷社”)占用。1991年金衛供銷社對占用房屋和宅基地取得由原金山縣土地管理局頒發的《國有土地使用證》,2002年取得上海市土地管理局頒發的《房地產權證》。自2014年起,翁某先后向金衛供銷社、金山區政府、上海市政府進行信訪。翁某認為,金衛供銷社非法占有其祖傳房屋,要求政府歸還被侵占房屋及地基,歸還房屋土地確有困難的,賠償其財產損失。
為了解該事項的真實情況,市人大常委會信訪處一行數人于2017年10月專門赴金山區進行了專題調研,聽取金山區人大常委會、區政府信訪辦、區法院和區司法局的相關情況說明。
經調研了解,2013年11月翁某由新疆返滬定居后,曾于2014年5月8日到6月5日期間,先后四次向金衛供銷社反映房屋及宅基地被侵占的情況。金衛供銷社答復其“原金山縣漕涇供銷合作社2002年取得房地產權證的基礎是其1991年取得的國有土地使用證,相關房屋土地屬于依法取得合法使用,并無侵占事實”。翁某于2015年3月向金山區政府申請信訪復查,區政府維持了金衛供銷社的答復意見。同年5月又向市政府信申請信訪復核。2015年5月2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訪辦公室出具滬府信訪復核字﹝2015﹞第00163號《信訪復核意見書》,告知其“提出事項系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雙方可以協商解決,如協商不成,依法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2016年1月,信訪人依據市政府信訪辦公室的復核意見,將金衛供銷社等告上法庭,要求賠償財產損失。然而,由于翁某所主張的財產損害事實距今已遠遠超過最長20年的訴訟時效,上海各級法院一審、二審、再審均以其訴求超過訴訟時效為由,駁回翁某的訴訟請求。此時,翁某為此訴訟已先后支出訴訟費、律師費共計人民幣20萬余元。
回顧翁某的維權之路,就程序而言,無論是信訪處理還是訴訟裁判,都環環相扣、于法有據,但正是在走完了這一套“完美”的程序之后,翁某的信訪訴求依然沒有實現,反而又為此支付了20多萬元的費用,對其本來就很拮據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影響。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連續四年兜兜轉轉在“信訪—訴訟—信訪”的無解循環中,耗費了巨額財力,人力,精力,最終得到的只是一紙“超過訴訟時效,駁回訴請”的判決文書和一個“依法可以通過訴訟等法定途徑解決的事項,不屬于行政機構信訪受理范圍”的信訪復核意見。
由此信訪件引申出的“訴訪分離”究竟應當怎么分、怎樣的程序引導才更有助于信訪矛盾在處理過程中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最大程度的統一等問題,無疑是值得反思的。
一、“訴訪分離”絕非機械化、“一刀切”地將矛盾導向訴訟
訴訟與信訪,交集于權利救濟,分屬于不同的糾紛解決方式。“訴訪分離”究其根本,并非限制信訪人的權利,而是要根據信訪事項的性質和具體內容,分別導入普通信訪渠道和司法救濟程序進行處理,從而更好地引導信訪人選擇合法、有效的權利實現途徑。“訴訪分離”制度的有效運行,關鍵之一在于信訪部門能否根據信訪事項的具體情況,對信訪人作出最有助于其實現權利訴求的程序引導。機械化、“一刀切”地將矛盾導向訴訟絕非“訴訪分離”制度的初衷。
前述翁某的信訪案例涉及歷史遺留問題的認定和解決,這類信訪矛盾的處理,是需要在程序引導時進行慎重甄別的一類典型問題。涉歷史遺留問題的糾紛具有緣起時間久遠、處理難度大、相關檔案資料不全甚至滅失等特點。而按照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法院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一般為三年,最長不超過20年。換言之,對涉歷史遺留問題的糾紛,如一味導向訴訟解決,其結果可能是大量的糾紛以其所涉及的民事權利超過訴訟時效,無法通過司法途徑受到保護而收場;而即使糾紛所涉及的民事權利未超過訴訟時效,也可能因為時間久遠、相關當事人過世、相關檔案資料滅失等因素,導致權利請求人舉證不能、法院亦無從調查,最終敗訴的結果。如翁某的信訪案例所示,翁某循著政府信訪復查復核對其導向訴訟程序的意見,向法院提起了財產損害賠償訴訟,最后仍是敗訴于訴訟時效、舉證不能等原因。
二、“訴訪分離”不應成為政府塞責或者懶政的“擋箭牌”
“訴訪分離”制度的實行旨在解決信訪渠道入口過寬的問題,意義在于更好地運用法治方式保障信訪人的合法權益。具體來說,“訴訪分離”制度的一項重要內涵是,讓司法的歸司法、行政的歸行政。按照實踐操作,也可以通俗地理解為:已經訴訟、仲裁等司法途徑解決的事項,政府信訪部門不再受理,告知當事人向司法機關反映。但需要指出的是,實踐中“訴訪分離”制度的這項內涵存在被泛化情況。
回到翁某的信訪案件,翁某在多次信訪中反復要求政府對金衛供銷社如何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房地產權證以及取得的合法性作出說明。但金衛供銷社的信訪答復、金山區政府信訪事項復查意見書、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訪復核告知書等信訪答復材料,都只載明了翁某持有1951年《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以及金衛供銷社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房地產權證過程的簡單事實描述,缺乏關于翁某所持土地房產證演變為金衛供銷社持有房地產證的情況、政府在處理該信訪件過程中是否對重要事實進行了實質性審查,以及是否有相關材料能說明金衛供銷社與翁某父親或者姊妹曾達成占用補償協議等關鍵性問題的明確闡述。此外,各級政府信訪部門在對翁某作出訴訟的程序引導中,對于訴訟時效問題也缺乏必要的告知,而我們有理由認為,政府對翁某案件的訴訟時效問題應有足夠的法律判斷。或許正是由于政府信訪這樣“一分了之” “一導了之”的處理方式,正是由于政府信訪完全合法,但缺少實質性審查,缺少必要權利告知的信訪答復,讓信訪人翁某遭遇程序走完,維權無解,再負新債的困境。
平等主體間的民事糾紛雖已由法院裁判,但如該民事糾紛同時涉及相關政府部門法定職責履行的,相關政府部門不應以已經法院判決為由怠于或疏于履行自身法定職責。
三、“訴訪分離”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有效引導與合理抑制
大量的信訪實踐顯示,雖然相關規定對“訴訪分離”作了制度安排,但在實際運行中依然會產生交錯情況,一些通過正常訴訟解決的問題被復雜化了,結果不得不通過信訪的途徑給予解決,而一些適用于信訪的程序,卻又被置于訴訟程序之中。我們認為,在信訪矛盾錯綜復雜的現實情況下,有效引導和合理抑制更有助于“訴訪分離”制度的有效運行。
具體而言,“訴”與“訪”的剝離,一方面需要信訪部門在信訪處理過程中,對信訪矛盾糾紛的問題本身進行充分的甄別和判斷,既要判斷是否可以導向訴訟,又要判斷是否適合導向訴訟。
在多數情況下,應以有效引導為原則,屬于“訴”的應當依法導入訴訟程序;但對于如前文所述涉歷史遺留問題的信訪矛盾等,無法通過訴訟途徑調處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信訪矛盾,應當予以合理抑制,慎重導入訴訟,或對訴訟的相關權利規定和時效問題等均作出明確告知后,再由信訪人自行選擇是否進入訴訟程序。
對于是否應當導入訴訟上存在爭議的信訪案件,政府應當探索與司法機關聯動互通的機制,主動與司法部門搭建起良好的引導銜接互動機制;對于情況復雜、涉及多個部門的信訪矛盾,應當繼續建立多部門聯動處理機制,由各相關部門協調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尋求有效的矛盾化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