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筆談錄(三)
——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與“作品中心論”的審美哲學
舒飛群
在前兩篇有關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筆談錄中,我們分別探討了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社會性和倫理追求,以及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音樂文化觀和社會實踐觀。
本系列筆談錄之三的主題是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與“作品中心論”的審美哲學,主要內容是關于“作品中心論”及審美哲學的評論,還有審美哲學的往事今生,現整理如下(下文提問者舒飛群簡稱“舒”;戴維·埃里奧特博士簡稱“戴”)。
舒:談論音樂教育的哲學問題,不能不聯系實際,尤其是中國音樂教育的實際。多年來,音樂教師面臨這樣一個困惑,即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歷史文化觀、社會倫理觀,與看重作品本身結構和要素的審美哲學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如果我們站在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立場看這個問題,那么音樂教育審美哲學是否具有合理之處?如果有,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能否承認并包容審美哲學立于音樂作品本身的某些自律論美學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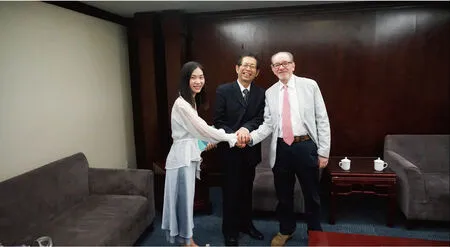
戴:對于這兩個問題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本系列文章所討論的《關注音樂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第二版)》這本著作中也提到了相似的問題,它并未全盤否定“作品中心論”的觀點,而是想與讀者一起來思考,“作品中心論”中的哪些觀點是具備一定道理的?就音樂的構成要素和音樂結構而言,“作品中心論”抓住了這樣一個事實:除了極少數的情況之外,說到音樂,人們難以回避的就是作品。此外,凡是音樂定然表現為某種結構樣式,具備人類音樂實踐的某些相通或相似的要素。我們的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誠如我們在之前的兩次探討一樣,看重的是人類音樂活動的社會、倫理、文化、歷史等內涵。我們的主張是要把人類的音樂活動及其教育活動放在更為廣闊的環境之中,但是我們并不否認“作品中心論”的合理之處,因而我們提出要運用包容的思維方式。這種方式包含“作品中心論”中的合理思想,包含“作品中心論”看重的音樂本身的構成形態,包括音樂的結構和要素,當然也包括具體的音樂作品。但是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廣泛吸取各個音樂學術領域的合理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各個時代和全球各地的音樂實踐的事實。
舒:從音樂教學的實際來說,以作品為中心,看重音樂本體,把作品的結構和要素作為核心,這在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看來存在不足和偏頗。請您聯系實際談談,在這樣的哲學思想指導下的音樂教學有些什么缺點?
戴:“作品中心論”對音樂教學的導向作用,勢必使學生的學習陷入被動的處境。采用西方傳統的審美方式來聆聽音樂,聽者的心態難免會變得冷漠,因為審美哲學提倡審美的主體與客體要有必要的距離。在音樂學院的音樂作品分析教學中,這種情形表現得十分典型,其焦點就是對作品結構的抽象提煉,以及對作品構成的各個音樂要素進行解剖式的分析。在音樂作品分析課堂上,這種專門的分析或許是必要的,但是它絕不是我們對音樂作品的全面認識。時至今日,這些守舊的分析套路統領了大學的音樂作品分析課程,統領著中小學的音樂賞析教學。音樂教育中的這種“風俗”,表現在演唱和演奏課堂中就是對音樂技能的磨煉。我們批評這些方法的片面性,因為它們把特定的音樂與其形成的豐富背景割裂開來。
舒:您的批評,就像我們中國人所謂的“見木不見林”,以及“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您提出的音樂哲學觀點,諸如音樂的歷史觀、社會觀、文化觀、倫理觀等,在中國哲學中具有深厚的文化與歷史基礎。我想在這里聯系音樂教學的實際,說說學習過的一些認識論和方法論。例如,您批判的被動的審美感知,使我想到對事物的認識,不是鏡映式的機械的認識,而更多的是能動的反映。人的能動性才符合藝術認識的本來面貌,否則就不會有中國人說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也不會有英國人總結的“一千個讀者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如此看來,過分強調被動的和冷漠的審美感知顯然有其局限性,既不符合人的認識規律和事實,也不會使認識變得深刻。進一步而言,如果我們的音樂教師強行要求學生對同一首音樂作品產生相同的認識,或者要求學生在音樂表演中把樂譜的規定視為圣旨,不可越雷池一步,那就只會壓抑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藝術則不再是藝術,而是千篇一律的復制品。我們學過的哲學鮮明地反對僵化的形而上學,倡導人們在諸多事物之間尋求普遍的聯系,尤其要聯系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狀況,這有利于我們廣泛地認識一切事物真實而深層的意義,包括文化的、藝術的及民間的。
說到西歐古典音樂的欣賞,我覺得也不能遵從西方自律論美學的狹義教條,僅僅從孤立的曲式結構、節奏節拍、旋律特點、和聲進行等要素來認識音樂作品。音樂作品的本體特征,比如和聲的動與靜、旋律的張與弛、奏鳴曲式呈示部的主題沖突和再現部的沖突解決等矛盾及其帶來的運動,恰好反映了當時西歐古典哲學的對立、統一,也就是辯證運動,而西歐古典音樂的獨特與偉大就在于此。就音樂的情緒表達和體驗而言,當時歐洲音樂在和聲、旋法、曲式等方面的對立與統一構思,與人的情緒之間也存在“異質同構”的聯系。比如,旋律的升與降、和聲的動與靜,這些運動形態與人的情緒的漲落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使得我們可以把音樂的思維與音樂的情緒聯系在一起。音樂打動人心,音樂表達心聲,畢竟它以情感為要。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的高等音樂學府里,許多學生并不愿意靜下心來,深入思考西歐古典音樂與古典哲學之間、思維與情緒之間存在的這些深層聯系。這樣一來,音樂作品的思想性和情感性的育人價值就損失了許多,學生對西歐古典音樂的理解就只能流于聲音要素方面的表層技法,缺乏音樂思想方面的社會的和哲學的深度,以及情緒體驗的厚度。您在書中提出了“以樂育人”的理念,如果我們把音樂與社會背景割裂開來,那么音樂作品中單純的聲音要素怎么能夠實現廣義的育人目的呢?
我在您的書中還看到這樣的描寫,即以作品為中心及音樂要素論的審美哲學,這其實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更深一層的關系。您能否簡要地解釋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如何影響著這種自律論美學的形成?
戴:你在談論一個有水平的社會學、哲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的課題。我在這本書的第三章專門寫道:審美哲學的純藝術的自律觀點,恰恰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從理論家的思想來看,秉持純藝術觀點的審美思想,屬于對何為藝術這個問題上的哲學思考。這些思考“跳”不出歷史的局限,受制于啟蒙運動時期的經濟、法律、社會、政治、權力。我曾經借用伊格爾頓(Eagleton)的一段詮釋:藝術的審美哲學思想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也就是新興資產階級標榜的自由、和平等,張揚的是個體的自律和自強。英雄不問出處,封建社會的家族名望和物質遺產不值得張揚,社會的主流意識看重和推崇的是個人本身的價值。我在這本書里說得很清楚,在新時代到來之前,歐洲社會是在權貴階級的專制之下;進入新的時代后,整個社會傾向并崇尚個人的獨立性—個人的情感、品味、自律、自強得到了空前的尊重。我們可以想象,既然社會尊重的是自律的個體,自律的音樂作品也會得以格外的珍惜,其價值也就體現在作品本身的內在屬性,具體講就是音樂作品的結構與要素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伊格爾頓的話一語中的,資產階級的主體是自律的和自主的。與之相應,當時的美學看重的必然是音樂的自律的方面。我們不必把話講得過于直白,哲學的、社會的語言和思考要求我們深入體會和領悟,思想深邃的讀者自然能夠讀懂這里的意思。
我再次提醒一下音樂的含義,千萬不能僅限于西歐那個時代的短暫成就,而應囊括整個人類自古到今的所有音樂成就和千姿百態的社會音樂實踐活動。如果我們把音樂僅限于西方那個短暫時代的某些作品,我們談論的音樂就不符合歷史和現實,就會忽視不同民族的不同實踐。認識到這一點,最為要緊。
舒:這些故事真有意思。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在西歐古典音樂的內在要素和內在情趣中便可找到更豐富的內涵,難怪有的西方音樂史教師要求學生透過音樂看歷史、看社會,透過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來闡釋音樂和理解音樂。接下來,請您再從歷史的角度,講講看重音樂作品本身的西方審美哲學的往事今生。
戴:西方審美哲學是有局限性的,它是囿于彼時彼地的社會文化體制的思想產物,我們不能將它作為永恒的真理來認識、解釋世間各種音樂及其性質和價值。即便是對于西方古典音樂的解釋,審美哲學也難以囊括其所有活動和聆聽的方式。
從歷史淵源來看,啟蒙運動之前的音樂家思考問題的方式并非僅以音樂作品的創作為己任。他們的樂思并不僅僅停留在結構形態和音樂元素,而且后來的審美哲學的被動聆聽、冷漠觀賞的方式也不存在。當時的音樂人也沒有機會把音樂作為藝術、產品,動輒審美的高調在那個時候的歐洲是不存在的。如今,人們在音樂廳內遵守音樂欣賞的拘謹成規,已是被熟知的常識。然而,正如希金斯在《我們生活中的音樂》 (The Music of Our Lives)所說:“專心致志、別無旁顧,音樂廳聆聽環境的這個規矩,即使在西方也是近期的一種理想。”我們還要想到這樣一個事實,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廳的建設形成了人們在室內進行音樂欣賞的習慣,彼此之間規規矩矩、避免干擾,這種風俗在巴洛克時期之前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放眼世界,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人類音樂活動發生在民間的生活和生產之中,對于這些音樂活動西方審美哲學如何解釋?
舒:您問得好!比如,面對中國的山歌、小調、勞動歌曲,還有載歌載舞、鑼鼓喧天的節慶場面,西方審美哲學就難以“指手畫腳”。
戴:這本書的第三章提到“作品中心論”的一個肇端,是與樂譜作為商品流通及經濟利益牽連在一起的。這件史實我希望讀者留意,它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審美哲學的作品中心觀念并不完全取決于音樂本身,而是有著當時社會的經濟、商業、法律等方面的原因的。以作品為中心的音樂觀念,必定要求作品能以樂譜為載體進入商業化的市場流通,使樂譜成為音樂作品客體化的標志。我認為,雖然19世紀初“作品中心論”尚未成熟,但記譜法的發展和應用,使樂譜能像書籍那樣作為商品進行交易。我們也可以想見,音樂思想訴諸樂譜并得以印刷和流通,音樂家才可能在樂譜上審視構成音樂作品的要素。而理性的分析和解釋,必須依據樂譜這樣一件客觀的實物,這就為后來“作品中心論”的形成奠定了物態的基礎。
18世紀后期,樂譜進入印刷行業并作為商品進行流通。此間,英國曾發生音樂家與出版商的利益斗爭,出版商刊印樂譜,獲得“大頭”利益,作曲家開始維權。1777年,約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把出版商告上法庭,最終勝訴。之后,英國法律做出規定,作曲家的樂譜等同于作家的圖書,其權益歸音樂家所有。這件史實說明,樂譜的法律地位和商業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品中心論”的地位,因為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樂譜幾乎能與音樂作品劃等號,繼而等同于音樂。時至今日,很多教師仍然把樂譜奉為神明,教導學生如何根據樂譜復現作曲家本來的想法。問題是,這種觀念無法解釋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和民間的音樂活動,無法解釋世界各地口傳心授的音樂活動。據此,“作品中心論”的審美哲學對許多音樂和教育活動是無效的。
我們再來簡要敘述審美哲學的理論形成。“作品中心論”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鮑姆加通(Baumgarten)、康德(Kant)、漢斯立克(Hanslick)等人。1735年,鮑姆加通提出的“美學”(aesthetics)這一概念,旨在分析詩的形象,其方法是科學的邏輯推理。始于詩學研究,美學在18世紀到19世紀拓展到繪畫和音樂作品中,甚至包羅自然現象。在當時的美學看來,詩歌、繪畫、音樂與大自然之間有著美的共同規律,美學繼而成為研究美的學術領域。假如大自然的美不包含在內,研究詩歌、繪畫、音樂的美的學問就是藝術理論。到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美學得以被深究,成為藝術趣味的規范理論。漢斯立克則提出,“樂音的運動形式”就是音樂的本質。流傳至今的那些審美方式,是把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詩歌作品作為審美的客體(對象),音樂中的旋律、和聲、節奏、音色、力度、織體等是審美主體的抽象的沉思對象……
舒:審美對象一旦成為孤立的客體,就會脫離鮮活的社會實際,純粹的藝術作品根本是不存在的。到了今天,音樂教材和教法中仍然留有這些痕跡。
戴:音樂的審美哲學總是牽扯不通情理的普世性霸權,認為歐洲古典器樂作品是高雅的、嚴肅的、藝術的音樂。言下之意,其他的則是流行的、民族的、低俗的、娛樂的、大眾的音樂。此類認識是偏頗的。音樂人類學和許多學科的研究認為,世界各民族音樂文化的價值是平等的。
審美哲學的影響力不可低估。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末,這股思潮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不少音樂教育哲學家、教師在理論和實際教學中也在追隨音樂的審美哲學觀念。我們糾正這種思想,是因為人類在不同的社會實踐中的音樂活動根本無法套用這種普世和霸權的審美觀念。不過,當代音樂學術界在音樂及其價值的觀念上,傾向于人們的真實音樂需求和活動,審美哲學的地位開始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