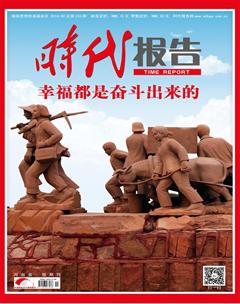紀念紅柯:騎手西去,文字長留
劉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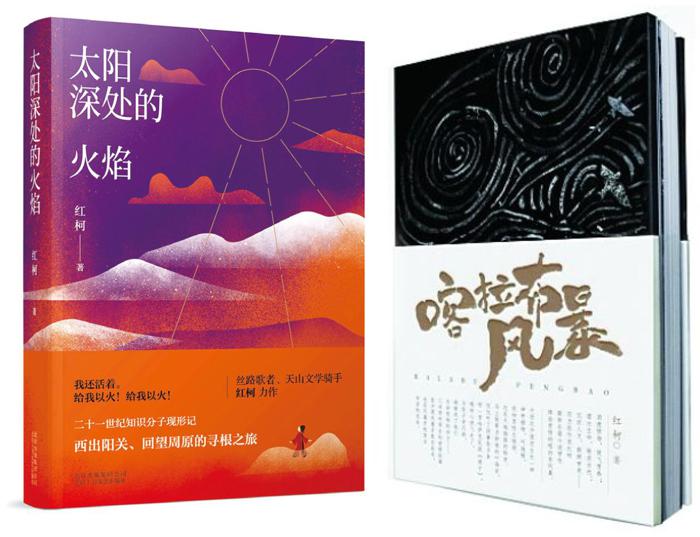

2月24日凌晨,陜西省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紅柯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56歲。
紅柯是西部文學的領軍人物,是橫跨中西部的一個作家,他生活在寶雞農業文明區,然后到新疆游牧文化區體驗生活,他把對中國西部的親身的體驗和了解,用西部浪漫的、詩性的手法寫出來,構成陜西乃至于中國文學的一個非常新穎獨特的現象。
紅柯,原名楊宏科,1962年生于陜西關中農村,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集《美麗奴羊》《躍馬天山》《黃金草原》《太陽發芽》《金色的阿爾泰》等,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大河》《烏爾禾》《生命樹》《喀拉布風暴》等,學術隨筆《敬畏蒼天》《手指間的大河》等,作品被翻譯為英文版、日文版等多種語言。紅柯曾先后榮獲首屆馮牧文學獎、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九屆莊重文文學獎、首屆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獎等多項大獎。長篇新作《太陽深處的火焰》于2018年1月出版,并獲得廣泛好評,進入多方年度排行榜。
紅柯是條漢子,認識他的人都有這感覺。
2004年2月,我們一個團去臺灣。當時選戰正酣,藍綠旗幟插遍了臺灣。在淡水漁人碼頭長廊,有一塊陳水扁所題“漁人碼頭”匾,游人紛紛在此留影。我們這個團的人在此進行了很多組合,與美麗的漁人碼頭景致合影,而那塊匾,則在有意無意中被遮蔽被忽略了,是無聲的,不動聲色的。偶有一兩個,則以戲謔口吻強調,要與扁(匾)合影留念。輪到紅柯了,只見他跨步上前,他偉大的臀恰巧擋住了匾。旁人提醒,他正色曰:我才不和這種人題的字合影呢!大家轟然大笑,紅柯這一舉動,也成為了我們那次臺灣行最牢固的記憶。行程之中,紅柯話并不多,只是他說話時語調與神情都特別的誠懇,讓你不自覺中就收起了游戲的心情。每每說話,還未開聲,倒弄得聽話的人先緊張了。行程之中玩笑不斷,但都不敢往紅柯身上引,因為他虔誠的表情,讓你覺得你只能與他探討一個個嚴肅認真的問題,哪怕是在臺北的霓虹里。但紅柯因此而成了我們那個團女性的最愛,他總是默默的,即使說話,話也不多;而敦實的外表、濃密的胡須(好像現在不留了),單單看上去就添了幾分威武。于是女性團員上街最喜歡叫上紅柯,哪怕是去便利店買包餅干。也算是狐假虎威了。
生命的尊嚴以及有神性的生命,一直是紅柯小說給我的最直接感受。
最早關注紅柯,是因為他的《西去的騎手》。好一個紅柯,徑直從西北大漠里拉出了一桿子人馬,虎虎有生氣。不僅是兒子娃娃馬仲英,還有盛世才、馬步芳們,讓浸泡在脂膩粉香中的人們感受到了呼啦啦撲面而來的生命氣息,感受到生命的原始的偉力和魅力。紅柯藉此一戰成名。
此后,紅柯轉戰筆墨間,《烏爾禾》《黃金草原》《阿斗》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太一樣的紅柯,但都沒有走出馬仲英的光芒。紅柯在尋找,紅柯在咂摸,這個期間,每每接到紅柯的電話,依然是那種真誠得讓你不敢忽視的語音和語調。在斷斷續續的信息中,我感受到了紅柯在文字的疆場里左沖右突的努力。
紅柯是很以他的家鄉為驕傲的。“我的家鄉中國陜西岐山,也就是古代的周原,至今還有姜原娘廟和后稷的神殿,中國原始農業的發源地,這是我作為陜西岐山人最值得驕傲的原因,也是我最喜歡希臘神話的大地之神蓋亞的原因。這些神話傳說告訴我們,人是有神性的,人在天之下、地之上,蓋亞是最早從混沌中分離出來的神,姜原是最早有母親意識的人類始祖,神性使人類擺脫了動物世界,第一批沐浴了文明曙光的人類把最初的人性視為神性是有道理的。”這是紅柯在今年希臘薩洛尼卡書展上的一個演講中的一段話。在另一個人類文明的發源地,紅柯盡管很尊重希臘文明帶給人類的曙光,卻同樣驕傲于他的家鄉——作為另一個文明的載體和記憶的岐山的最早的榮光。更讓他驕傲的是,那些從動物性中分離出來的人性,那些有著神啟意味的人性。《生命樹》里,神性是有生命的,神性通過人性而得到了彰顯。這部小說中的人與物都是負載著神性登場的,他們或忙碌或成功或平庸或奉獻的一生,都是為了印證神性的存在。有了這種高貴的神性,平凡的生命便放射出異樣的光輝,那光輝潔凈、溫暖,有著生命的溫度。如此,盡管馬燕紅正當花季(這個詞用在那個環境下的她身上也許有點不恰當)被強奸,盡管牛祿喜被弟弟算計盡了自己的20萬存款,盡管杜玉浦在徐莉莉的光環下一生委頓,他們的生命,卻都在神性的洗滌和照耀之下,活出了另一種意義和精彩。
生命是紅柯小說中神性的著陸點,沒有生命的體溫與血液的流灌,神性就只能是懸空的無根的。“大工業,高科技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使人類的生活與生命體從有機狀態淪落為無機狀態”,紅柯努力的,正是在他的小說里把無機狀態的生命還原為有機狀態。《生命樹》中有這么一段話:“馬來新沒有講那個藍幽幽的美麗女子,也沒講大洋芋閃射藍光時顯示出來的龜卵形狀。這是他與大地的秘密,他跟誰都不說,跟兒子孫子都不說。”紅柯借小說中人物馬來新的口說:人活著靠悟性,說破就沒意思了。可以說,人的這一點悟性,其實就是神性的靈光閃現。在紅柯的小說里,洋芋是有神性的,玉也是有神性的,人也是可以有神性的,前提是人必須恪守源自岐山的文明的規約。當然這種規約不是以條文的形式呈現,而是在口口相傳的民間故事里,在代代相傳的人心里。說白了,就是人之為人的禮義廉恥,就是真善美。
“植物、動物作為一種生命體,在文學史上一直作為人類的背景作為風景出現的。”紅柯認為,“小說的一大功能就是塑造人物。人物即人與物,物即環境、背景,包括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人自己的心理環境。人與物處于游離狀態處于無機狀態人就有危機感;人與物處于有機狀態,物我為一,發生化學反應,且壯大自己提升自己,這是人應該過的生活。這種狀態就是一種符合人性的生命狀態,即具有神性的狀態。神性是人性的上升,是人性的最高狀態。”這是紅柯面對著奧林匹亞山眾神,高聲宣揚自己對于人性和神性的理解。這種姿態感動了我。紅柯是一個何其認真何其低調的人,面對希臘廟堂上的眾神,闡述自己用生命的體驗和感悟獲得的識見,而且以如此自審然而絕不卑微的態度,在尊重之余不能不生出敬意。事實上,紅柯的小說中,的確是萬物有靈。他的這種萬物有靈,不是為了掩飾自己作為小說家在創作上的捉襟見肘或難以為繼而生出的敷衍伎倆,或是為拯救自己的才思不逮,而是紅柯努力做到一個有機的紅柯創造一個有機的文本的努力使然。
紅柯小說中讓物的神性喚醒人性是寫作以來一直的主題。《西去的騎手》中,當馬仲英的大灰馬從青海湖的湖水中冉冉升起的時候,馬的神性有如一柄利劍,剖開的是人性的陰暗和丑陋。紅柯曾說,“我生活過的中亞腹地的大沙漠,在那里,一棵樹、一棵草、一個泉眼都與人類息息相關,一只螞蟻一條蜥蜴都是人的朋友,一只土撥鼠的突然出現,會給人類帶來地球深處的聲音,你會感受到大地的心跳,你也會把頭頂的云看成上蒼的呼吸。天地人,共生共榮。”紅柯筆下人物的生活,哪怕卑微渺小,也充滿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在生態的完整中,成就一個個靈魂沒有缺失沒有遺憾的生命個體。
《生命樹》中兩個細節我非常喜歡。一是王懷禮埋牛和牛黃,一是舅舅埋玉。顯然,這兩處埋的動作,具有救贖的意味。它象征著人對自我的救贖,人對與生俱來的神性的救贖,它也意味著土地上的人對生命、對自然、對神性的敬畏。
敬畏而自審,粗糲而深情,這是紅柯的小說,也是紅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