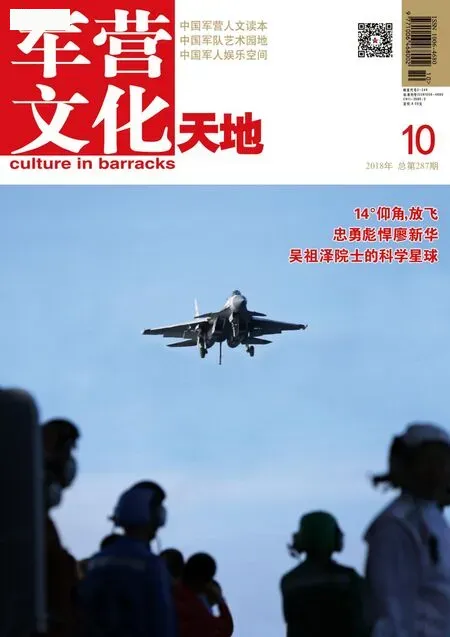瞄準心靈的靶標
文/徐 彤
采訪石天堯那天,是北京4月的意外飄雪后,開始回溫的第一日。當時陽光和煦又極富穿透力,仿佛可以一下子照進人最深不見底的精神內部,驅散所有暗自生長的灰霾。
站在實驗室的玻璃門前,記者看到石天堯的背影,他正在顯微鏡下聚精會神地進行神經元膜片鉗記錄實驗。那種專注就像一名端槍的戰士,此時此地,他全部注意力都聚焦于遠處圓環正中的那一個點。
2012年,在石天堯攻讀藥理學博士的第3年,他來到多倫多大學卓敏教授實驗室進行為期1年的科研交流。這段短暫的海外留學經歷,卻培養了他樂于從每個項目最簡單、最基礎工作做起的治學品格。“成果都是從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不必貪多,只要每天能夠認真解決一個科研問題,日積月累,在不經意間就會形成一份實驗報告、寫出一篇學術論文。34歲的石天堯身上潛藏著一股成熟的韌勁。從事藥理學研究以來,他先后主持和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5項,發表SCI論文12篇,被聘為北京藥理學會神經精神藥理專業委員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進入藥理學研究之前,石天堯還曾在化學領域做過長達7年的研究。談起轉行,他說考大學選擇化學專業是因化學研究的是最基礎的物質元素,也就為日后向其他專業發展去搭建平臺,更快地適應其他專業的語境。借由化學的積淀去認識更多領域,擴大自己的視野和知識面,直至找到真正能夠使自己樂在其中、執迷不悔的職業。“一個人終其一生,不就在逐漸擴大自己的視野,寬闊自己的心胸嗎?人的成長是一個不斷容納、積累的過程,你嘗試得越多,了解得越多,就越廣闊。這就是一個自我確定的過程”,石天堯說。
碩士期間,石天堯已經對藥理學表現出了濃厚興趣,但真正促使他由化學轉入藥理,還是因為他在做紅景天相關研究時遇到的一個問題。紅景天的主要作用是抗疲勞、抗缺氧。為了得到抗氧化能力更強的化合物,他嘗試了不同的結構改造方法,但結果都不理想。正當他屢試不成的關節點,藥理實驗室的一個老師提出了一種思路,他說紅景天苷的糖苷是葡萄糖苷,而人體內半乳糖受體分布更廣,如果把糖基由葡萄糖換成半乳糖效果會不會更好?石天堯馬上按照這種思路去試驗,才發現果然是半乳糖的糖苷的活性最高。他忽然意識到,一加一大于二,如果能將化學與藥理學結合起來,在突破難題時,可能就會出現一些靈光四射的思路和轉機。
從進入藥理學專業開始,石天堯的興趣就在于負性情感研究。他同時注意到,目前臨床采用的治療手段主要是心理治療(如認知療法)和藥物治療相結合,藥物治療更為常用。但是由于精神類疾病藥物長期使用引起的成癮性以及療效降低等,不能有效控制臨床癥狀。這是由于各類神經精神疾病如抑郁癥、焦慮癥、雙向情感障礙等,其作用機制都不明確。如何從藥物層入手,使藥物作用更有側重點、針對性,這是他進入藥理專業以來一直在探索的難題。
“我覺得自己像是個解謎者,謎底就是能夠找到精準對應每一種神經精神疾病的藥物靶點。這個很難,但我們一直在努力。”石天堯雙手交握,非常篤定。
為了使自己的研究目標定位更加精準、清晰,更好地切合臨床需求,在實驗室、辦公室之外,石天堯還高度關注醫院的臨床病例。他說:“我做藥理研究,做出的‘產品’,是不是真的為病人所需,這中間有個缺口。只有不斷地與醫生進行交流,了解他們的需求,并把這些轉化為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問題進行攻關,這個缺口才能填平。”
他至今仍清楚記得碩士期間到西京醫院實習,第一次走進心身科的感受——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其中有一個經歷車禍的患者,在車禍中親眼目睹自己的親人死亡,從此四肢健全的他執意認為自己失去了雙腿,喪失了行走能力,他終日坐在輪椅上,雙眼如暗夜一般沉寂。還有一個在火災中失去男朋友的女孩,最觸動他的是,這個女孩一見到石天堯,就斷定他是她男朋友,從此在神經科病區,她像影子一樣緊緊跟隨著他,一旦他下班離開,她就失去控制地歇斯底里。“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見這個看似平坦的世界中有一道巨大的鴻溝。有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精神心理壓力之下,過著難以想象的生活。”石天堯字字懇切。
正是基于這樣深沉的人文情懷,做實驗對他而言也就不再是單純的科學活動,而是包含了他對樣本背后患者的深刻體察和與他們靈魂深處的交流溝通。這是他的科研力里面非常獨特的部分。
采訪最后,筆者請石天堯簡單概括自己這幾年的科研歷程,和對未來的期許。他注視著不遠處光點閃爍的熒光顯微鏡想了一會兒,說:“人生需要理想,實現需要堅持。這是一條寂寥但充滿無限可能的路,失敗隨時會來,要敢于承擔。既然是為治愈精神心理疾病而努力的人,我自己的精神心理就得足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