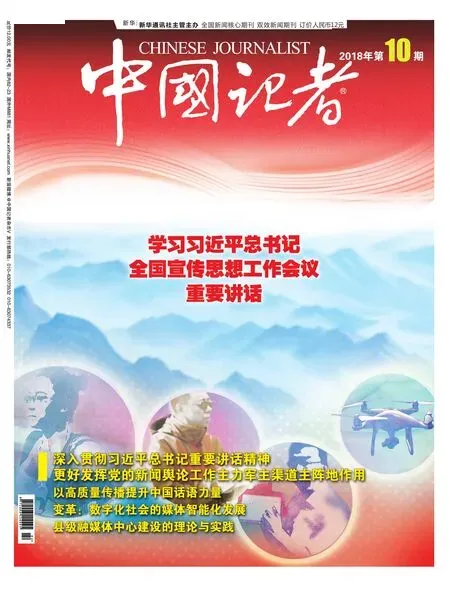從祁連山系列調研報道看輿論監督的正向推動力
□ 文/黃文新
內容提要 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報道,不僅能揭露問題,還能推動問題妥善解決,更能轉變群眾思想觀念,最終將思想統一到黨中央精神上來。新華社記者連續三年關注祁連山生態環境問題系列報道,就體現了這樣強大的正向推動力。
祁連山是西北地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其生態好壞直接關乎絲綢之路的安穩與存續。從2015年5月開始,筆者和領導及同事陸續15次探訪祁連山,用腳步丈量祁連山區的崇山峻嶺、河谷礦區,累計行程兩萬多公 里。
三年來,我們所采寫的稿件三次獲得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批示。中紀委、最高檢、生態環境部等多個中央部委介入調查,包括三名副省級干部在內的百名干部被問責,并引發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督查整改風暴。在祁連山系列調研報道中,作為媒體,輿論監督發揮了典型的正向推動力,不僅撬動了祁連山管理體制的重大變革,更重要的是地方黨委政府和干部群眾也從內心深刻認識到了破壞環境謀發展無異于飲鴆止渴,拒絕媒體監督相當于“包膿養瘡”,并從轉變發展思路中收獲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科學論斷的實踐效果。
一、三年進山15次 祁連山滿目瘡痍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人的悲歌,傳唱2100多年,道出了祁連山作為“母親山”無可替代的尊貴。
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處于甘青兩省交界,核心區海拔高、地勢險,冬有大雪封山無路可走,夏有山洪亂石泥濘難行。記得有次進山,我們在核心區外圍打轉,恰逢幾日連降大雪,與地方“線人”多次聯系得知,核心區道路不通,但要目擊探采礦對凍土等不可逆轉的破壞,核心區非闖不可。
山路曲折顛簸,積雪白得晃眼。多處路段被水流沖斷后覆著冰蓋,其下流水潺潺,不知深淺。為了減輕越野車的重量,大家不得不下車徒步“踩冰探路”。伴隨著腳下不斷發出的咯吱聲響,我們知道了什么叫“如履薄冰”,也終于在人跡罕至的核心區見證了大規模開山修路建廠的嚴重破壞行為,觸目驚心。
行至密林越深,霧鎖青山,一條路基5米左右、長度在50公里以上的山區道路穿越喬灌木林帶、草原和河谷,延伸至海拔3800多米時,道路兩旁有多處因修路被破壞的山坡,生長千年的草皮被揭,碎石裸露。
在東峰礦業開礦點,大量廢石掩埋了地表植被,山溝中建起了礦點管理人員居住的活動板房,挖掘機、推土機等重型機械停放在門外,離板房不遠處堆放著尚未運出的鐵礦石。“聽到檢查的風聲,采礦暫停了數月,老板讓我們在這里值班,看護設備和礦點。”守護人員介紹說。
無休止探礦采礦、“掠奪性”放牧、旅游開發項目未批先建、小水電項目陸續上馬等行為,讓脆弱的祁連山生態不堪重負,一些局部破壞已不可逆轉,背后暗藏巨大生態“黑洞”。
隨著氣候變暖,雪線上升、 冰川加速融化,下游地區的生存和發展面臨的危機已迫在眉睫。為了獲取第一手的冰川消融退縮對比素材,我們連續三年徒步攀登七一冰川。冰川常年高寒缺氧,山谷大風凌冽,寒氣刺骨。調研團隊到達山頂時,人人面色發青、嘴唇黑紫。目擊的場景也讓大家震驚——冰舌退縮明顯,記者的觀察與中科院研究報告得以互相印證。
三年下來,我們的采訪對象多達上百人,記錄了一千多分鐘的視頻資料,拍攝了近萬張圖片,所有人的材料和筆記摞在一起有一人多高。掌握了大量鮮活的一手素材,也通過不同利益攸關方的“眼睛”看到了樣貌各異的祁連山。最終,調研團隊以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為基本標尺,以文、圖、視融合的形式代入式地描摹和梳理了祁連山現狀和背后復雜矛盾的詳盡圖景。
二、與利益攸關方的博弈
在遭遇毀滅性破壞的核心區域、歷史遺留問題突出的農牧業地區、人身極易受到威脅甚至攻擊的開礦點等點位;在避重就輕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心存芥蒂的祁連山管理局負責人、保護區開礦的企業老板、生活在保護區的農牧民等上百名采訪對象的口中,我們看到了每個人眼中的祁連山。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行政區劃的分割性與綠色發展的整體性等矛盾遠比我們預想的要復雜得多。
“北緯37度44分47秒,東經101度38分4秒”——這是什么?這是一處坐標,它指向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內的一處礦點用房,也是客觀反映生態遭到破壞的直接事實和證據。
面對采訪初期發現的祁連山生態矛盾多樣性、復雜性,我們計劃以證據為抓手,進行后期的材料組織工作。
在獲取了30余處疑似生態破壞坐標點位后,我們與相關部門協商溝通,通過技術手段在衛星地圖軟件中獲取了這些坐標在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具體區域劃分。其中,17處坐標和相對應的圖片、視頻材料成為定性祁連山生態破壞問題嚴重性的直接證據。
祁連山的各方利益糾葛到底有多復雜,一些最簡單的事實就可見一斑:山丹馬場地跨甘青兩省4市州6縣,隸屬央企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管轄權與管理權不一,企業經營與生態保護矛盾突出;占地約4000平方公里的皇城鎮與甘青兩省4市州7縣區相鄰,行政區劃上屬于甘南裕固族自治縣,實則為一塊“飛地”,牽涉多方利益;小香溝、母虎溝流域行政區劃上屬甘肅省民樂縣,管理使用上又屬于山丹馬場,同時還是協議議定的青海省祁連縣與民樂縣、山丹馬場的共牧區……
生態環境矛盾有一個歷史積累過程,祁連山亦然。多輪開發,才造就了今天滿目瘡痍、局部受損嚴重的祁連山。然而對于利益攸關方而言,關停肅整的陣痛卻是現實而直接的,反映在我們身上,更嚴峻的考驗便來自暗藏的風 險。
由于對祁連山生態問題的采訪報道已經引起地方明顯的反彈情緒,為保證持續不斷進行有力監督,調研團隊運用“人煩我不躁、人推我不惱、人躲我主動”的方法。在采訪的過程中,一位知情的地方領導干部告訴記者,祁連山破壞最嚴重的時候,僅一個市就有700多個礦點,其中既有省里批的,也有市縣批的,甚至某縣的財政收入80%以上就是靠攫取礦產資源來支撐,當中的利益糾葛錯綜復雜。
2015年6月-7月,關于祁連山生態問題的三篇參考報道相繼刊發。2015年9月28日,針對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環保部與國家林業局在京聯合約談張掖市人民政府、甘肅省林業廳和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等部門主要負責人。
一些對記者個人不利的信息在這個時候也開始流傳,有些人也提醒記者,做事不要太認真,畢竟還要在這里繼續生活工作。甚至甘肅省一些領導干部還認為,新華社的工作是小題大做,是在“找麻煩”。
調研仍在持續,履職沒有停步。第二批稿件得到習近平總書記長篇批示后,時任甘肅省委主要領導仍然沒有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甚至聽聞其對新華社的持續關注報道不滿意。
面對各種壓力,新華社記者以錚錚鐵骨作出有力回應。黨的新聞媒體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始終不渝增強看齊意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017年6月,祁連山生態問題被全國通報,截至目前,包括三名副省級干部在內的上百名干部被問責。新華社的報道直接推動了祁連山生態破壞問題最嚴厲問責和最嚴格整改,撬動祁連山管理體制機制重大變革,對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綠色發展理念,促進生態文明建設起到了重要而獨特的作 用。
三、“挨了巴掌我們也記住了疼”
連續三年,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新華社記者持續關注祁連山生態問題,目睹由亂到治,也見證了沿線干部群眾努力化生態之“危”為轉型之“機”。媒體的監督也同時轉化為地方堅定走綠色發展之路的“推進劑”。
2017年底,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炭山嶺鎮。在千馬龍煤礦曾經的廠區上,當年新植的松柏整齊排列。天祝縣國土資源局局長趙明軍說,等到來年,經過管護撫育和自然恢復,這里的環境就基本能和周邊生態融為一體。炭山嶺,這個祁連山中因產煤得名的地方,自此揮別“靠山挖山”時代。
封堵探洞、回填礦坑、拆除建筑物、種草植樹……截至2018年8月底,包括千馬龍煤礦在內,祁連山保護區144宗持證礦業權、111宗歷史遺留無主礦業權的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基本完成;42座水電站全部完成分類處置;25個旅游項目完成整改和差別化整 治。
通報問責高壓之下,祁連山迎來半世紀未有之平靜,在中央支持下,多年來的生態欠賬、舊賬一起還。
“我們挨了最重的板子,也得到了最大的支持。”甘肅省張掖市市長黃澤元說。過去的一年,沿線地區獲得了祁連山生態保護歷史上一次性投資規模最大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的支持,今年6月底已完成投資近36億元。許多累積多年、想解決而沒能解決的困難矛盾得以化解。
“不可否認,在你們最初報道祁連山生態破壞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抵觸情緒是有的,多少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習慣了,你們的報道引發關注,我們就得打破以往的發展慣性,另尋出路。”張掖市一名干部告訴記者。
祁連山東西長一千多公里,80%在張掖市,這其中,又有八成以上屬于下轄的甘南裕固族自治縣。記者三年來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這里,經歷了媒體監督到強力整改,再由轉型發展到媒體助力這一轉變過程。
2017年7月25日,新華社發出《西北生態屏障祁連山:“史上最嚴”問責風暴帶來“綠色革命”》一稿,引發社會強烈反響。稿件中寫到:近日,記者驅車2000余公里,深入祁連山,實地踏訪生態破壞地帶,與沿線市縣干部座談交流,明顯感受到,督查帶來“猛擊一掌的警醒”,讓各地關停整肅態度更加堅決、綠色發展轉型目標愈加明確……
這篇稿件仍然出自新華社祁連山生態調研團隊之手。彼時,整改的高壓要求之下,祁連山沿線各市縣已經充分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的重大意義。從“遮遮掩掩”到“主動揭短”,從“能保就保”到“堅決關停”,從“湊合發展”到“杜絕污染”……記者在實地踏訪中,也看到了這樣的變化。
祁連山生態問題教訓深刻,其由亂到治,必將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樣本。這場“史上最嚴”問責風暴帶來的“綠色革命”,不僅需要“壯士斷腕”的決心,更要運用治理智慧,梳理矛盾、化解頑癥,完善綠色制度,樹立綠色導向,尋找綠色出路,實現綠色發展。

▲ 盛夏時節,位于祁連山北麓的民樂縣鄉村綠意盎然,美景如畫。(新華社記者 王將/攝)
整改一年來,祁連山沿線各市州更加受到媒體的關注。《祁連山:為野生動物“騰挪”生存空間》《研究發現:全球變暖導致祁連山東部和中部地區森林上線向上爬升》《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六成持證礦業權完成退出》等新華社多篇稿件的推出,為當地的祁連山生態整改工作加油鼓勁,為綠色制度、綠色導向、綠色出路、綠色發展的進一步成型創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四、媒體監督的正向推動助力地方涅槃重生
“我們在保護區少砍一棵樹、少放一群羊、少建一座水電站,我們發展旅游,展現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一樣可以讓老百姓過上富足幸福的生活。”這是張掖市市長黃澤元在今年8月份錄制新華社甘肅分社融媒體訪談欄目《共話隴原》時說的一句話。
有人說他現在是“網紅市長”其實包含有兩層意思,在中央關于祁連山生態破壞的通報里黃澤元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在這之后不久,他就走進了電視臺的演播間,以慷慨激昂又飽含感情的一段演講來闡述生態之美的意義,推介張掖市的旅游資源。
一組數據更加印證了張掖市走綠色發展之路所帶來的“真金白銀”。2017年,張掖旅游人次突破2500萬,旅游綜合收入達到了157億元,而截至2018年8月底,今年張掖旅游人次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甚至出現部分景區進行游客限流。
與此同時,媒體一方面依舊對祁連山生態整改進行監督報道,刊發了《中國學者啟動第二次青藏高原祁連山綜合考察》《祁連山保護區核心區農牧民:從索取到保護》《“像眼睛一樣保護祁連山”》等稿件。另一方面通過《第五屆綠色有機產品(張掖)交易會將舉辦》《探訪千年皇家馬場 第一任“場長”名叫霍去病》《草原、森林、丹霞、大漠、冰川、濕地……除了海洋,你要的全有!》等全媒體融合報道的形式為綠色發展提供媒體推介平臺。
如今,綠色,正更多地彌漫在祁連山間。綠色發展的共鳴,正回響在祁連山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