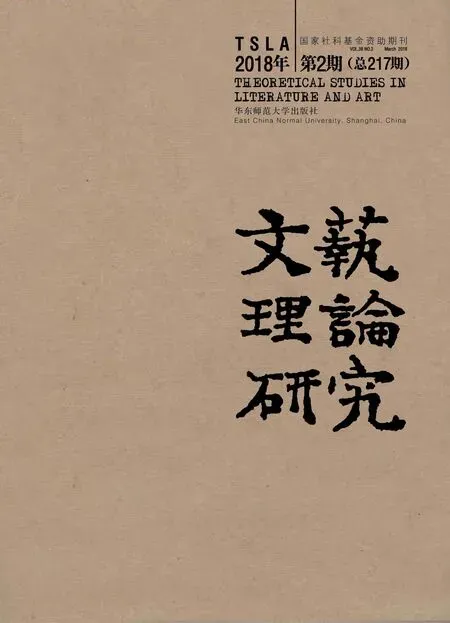姿態的詩學: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評
支運波
在《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的“前言”,阿甘本列出了他所關注的一些重要主題“姿態”(Gesture,或譯為姿勢,在遵從引文出處的譯法外,本文均譯為姿態)赫然在列;在收入《潛能》的《科莫雷爾,或論姿勢》一文中,阿甘本甚至把姿態作為衡量杰出藝術與偉大作家與否的唯一標尺。毫無疑問,在從亞里士多德到尼采,從海德格爾途經本雅明、福柯、德勒茲,一直到南希的西方著名姿態論者中,沒有哪一位理論家能像阿甘本那樣,將姿態作為其批評思想中的一個極其關鍵的要素與核心內容(Colilli 165),更沒有哪一位理論家將姿態作為批評的最高標尺(《潛能》251)。阿甘本關于姿態的卓越論述使其一躍成為西方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姿態論者。他的姿態論不僅橫跨電影、文學、美學、倫理與政治等等多個學科領域,且貢獻卓著。甚至在某些領域內堪稱“現代理論的一個重大事件”(Gustafsson and Gr?nstad 121),或者首次廓清了困擾學界許久的批評難題。在前者,如在近代電影理論史上;在后者,如對阿倫特提出的“本雅明身份難題”上(《啟迪》23)。不僅如此,姿態論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開啟了本雅明與阿甘本從美學批評邁向生命政治批評的重大轉向,并為“后理論”(after theory)時代的文學批評貢獻了一個新的詩學批評理論范式。
一、作為空無與純粹媒介的姿態
阿甘本有關姿態的論述見于《赤裸生命》《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褻瀆》《沒有內容的人》《潛能》以及《未來共同體》等諸多著作,而尤其集中于《關于姿態的筆記》(1978年)、《科莫雷爾,或論姿勢》(1991年)以及《作為姿態的作者》(2005年)這三篇重要文獻。阿甘本主要是通過闡釋與糅合前人有關姿態的論述而綜合發展了自己具有生命政治意涵的獨特姿態說的。概括地說,他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瓦羅(Varro)的空無姿態說,科莫雷爾的純粹姿態說,德勒茲的運動—影像說,福柯的“作者的缺席”說,德波的景觀理論,以及本雅明的“情節中斷”說,等等。特別是本雅明的思想,一直是阿甘本理論最為重要的潛在對話對象和闡釋對象,本雅明許多有關姿態的論說都或明或暗地點名了后來阿甘本所論述的內容。
“姿態”(Gesture)這個詞最初來自拉丁語gestura,意為“承受”(bearing),“執行方式”(way of carrying),或“行為方式”(mode of action),它的動詞不定式形式gerere,意為“執行、行為、自我承擔、掌控、表演或完成”等(Kendon 44—62)。 阿甘本也曾在不同地方多次對什么是姿態,或者,確切地說什么是文學的姿態做過解釋。而他的這些涉及到文學姿態的解釋也都或多或少地遺留著姿態詞源學上的痕跡。比如,《作為姿態的作者》中,他追隨福柯指出:“我們把在每個表達行動中的未得到表達之物稱作‘姿態’”(《褻瀆》65);《關于姿態的筆記》中,他服膺瓦羅認為姿態是“持續和維持著”的某種行止領域(《無目的的手段》76);而在《科莫雷爾,或論姿勢》中,阿甘本又贊成科莫雷爾而主張姿勢乃是內置于語言中的沉默部分(《潛能》252)。通過考察阿甘本不同文獻中對姿態的論述,我們可以簡要地將他的姿態說概括為“啞口”“空無”和“純粹媒介”三方面的內容。
《科莫雷爾,或論姿勢》中,阿甘本考察并闡釋了科莫雷爾的姿態說,認為姿態是一種內置于語言中的無言,它先于言語而在語言中存在。阿甘本認為科莫雷爾的姿態不是一個非語言的元素,而是一種在語言中存在的,一種比概念的表達更為古老的在場。或者,更為準確地說,言語是姿態,姿態是無言,它們共同屬于語言的兩面。即,姿態所意指的“是內在于人類語言能力中的喑啞,是它(語言)寓居在語言中的無言”(《褻瀆》253)。 這種“無言”常常以“謎”(R?tsel)、“秘密”(Geheimnis)和“神秘”(Mysterium)三種方式“確立”或“填補”人的存在。阿甘本將語言中的“無言”(或啞口、塞口)歸結到“本性的姿態”(或語言姿勢)范疇,把克制的性格掩蓋在形象之中的舉止歸結到“靈魂的姿勢”,但他最看重的卻是從姿態的語言關系中窺視到的,只是作為交流之可能性的而無任何訴求的純粹媒介性,即“純粹的姿勢”。這也是阿甘本姿態論的最大貢獻所在。
“姿態是無言”表明姿態既是“無”,也是“言”,是關于“無”或傳達“無”的溝通方式。所以,阿甘本反對將姿態界定為一種“目的”,也反對將姿態界定為一種“手段”。相反,阿甘本認為它類似于康德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一種“無目的的手段”,是一種“無”與“有”的辯證統一體。姿態是一種“交流”,這種交流所展示的是作為“在-語言中—存在”的人的“不可言傳性”:那些“無法說出”、失語、失憶,以及無需言說和拒絕言說的部分。在福柯那里稱之為“空無”。在《作為姿態的作者》中,阿甘本根據他的姿態論,在福柯“作者的缺席”的基礎上提出在作品中,作者并不再現、表征、重塑或訴求什么,他僅僅是作品敘述成為可能的中介而在場的。作者是“傳奇的空無,從如此空無中書寫與發出話語”(《褻瀆》69),通過作者這種姿態,即“通過在這個表達內部建立表達中心的空無(a central emptiness,中空)來使表達成為可能的”(65)。進而,他認為詩的發生既不是來自于作者,也不是來自于讀者,“它在于作者和讀者在文本中借以把自身置入游戲并在同時,無限地從游戲中抽身而退的那個姿態”(71)。
無論如何,姿態的意義,從根本上說,都要回撤到語言中,在作為“更普遍的溝通”(Murray 81)意義上去認識它。在《關于姿態的筆記》中阿甘本談到了“塞口”和交流性的問題,并從科莫雷爾那里借用了“純粹姿態”概念來指稱語言內部和置于語言結構中的,但卻從來不能用語言完全表達的那種東西。弗萊明通過考察認為,科莫雷爾提出的第三個姿態:純粹姿態(the pure gesture),它是一種全然不同于靈魂姿態和自然狀況下的語言的姿態,“它位于自然姿態與靈魂姿態上層的某個部分,作為純粹姿態,它是其他所有姿態的起源”。純粹姿態乃是一種與外部世界無關、與當代無關,卻只是與未來社會相關的無限時刻。它只與自身相關。“純粹姿態不是表達、說出某物的形式;它沒有在內部與外部之間、特殊與普遍之間、能指與所指之間建立任何關系。純粹姿態根本就是不一個符號。它不屬于符號秩序本身,因為它只是‘言說自身的純粹可能性’。純粹姿態不是語言言說某物,毋寧說,它就是言說的可能性。即是說,純粹姿態存在,它置于語言內部,但不能靠語言完成表達”(Paul Fleming 519—43)。純粹姿態展現了阿甘本姿態說的根本特性,即“在于在其中既無東西被產出,也無東西被演作,而毋寧說,是某種東西在其中持續和維持著。換言之,姿態打開了行止(ethos)的領域,這個領域是人之為人更為本己的領域”(“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 76)。
姿態敞開了一個“行止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既不“做”(facere),也不“作”(agree),而只是“持續或維持著”某種狀態。這是阿甘本從亞里士多德關于制造(poiesis)和實踐(praxis)的區分,特別是古羅馬作家瓦羅提出的行動的第三個類型:“持”(greit)的階段所獲得的啟發。阿甘本認為姿態在這個意義層面上突破了“制造”——“相對于目的而言的手段”——和“行動”——“無手段的目的”——之間在手段和目的上的“二決一”的難題。而且,更加突出了手段,又不忽視“無目的”的“純粹媒介”性。對此,阿甘本援引瓦羅的話說道,詩人創造但不表演,藝術家表演但不創造,而一個國家的國王既不創造國家、也不執行(perform)什么,而僅僅承擔某種責任和履行職責。這意味著姿態具有鮮明而激進的政治意涵,也是人們借此進入政治共同體的美學途徑。
姿態是語言中無言的部分,也是為彌補無言的、中斷的部分,以及單純地在無言中存在的部分。阿甘本說文學本質上是姿態的,這是一個綜合命題。至少,它包括從文學作為藝術而言,它是對人類姿態的記錄、書寫和揭示,并通過它自身獨有的方式試圖挽回人類的本己性;從作者方面而言,作者是以姿態保證作品的生命的。作者的姿態乃是將一個現實生命被獻出并在作品中被置入游戲,同時在保持作品對該狀態處于“空無”中以言說的方式打斷情節,并持續地揭露它;從讀者方面而言,讀者的姿態就是去辨識作品中作者的姿態,敞開作者構筑的“空無的場所”,安放經過在作品中被證實的那個一度被作者空缺下來不可表達的思想和情感的姿態;而文學就是發生在作者與讀者被置入作品的同時又抽離離去的那個姿態中;從文學的作用而言,它是以純粹的中介性為讀者提供諸如愉快等情感,以及作為純粹媒介性將展示為“在—媒介中—存在”;就文學的構成而言,姿態又是內置于語言中的無言;就文學批評而言,“批評就是把作品化約到純粹姿態的領域”(《潛能》257)。最后,姿態既是人類行為,也是人類存在的方式和最為本己的居所。所以,文學的意義只有在姿態中才能真正地獲得。
文學本質上是姿態,文學批評本質上也是姿態的批評。阿甘本稱它是超越了其他一切領域和闡釋方式(如心理學的、美學的)的最高的批評。它既疏離于文學的歷史,也拒斥其他關于文體的理論,而是保持著“現實與虛幻、生活與藝術、個體與種屬之間的”恰當關系,借此展示一種“記憶的缺乏”和無可挽回的“無言的塞口”。對阿甘本而言,“姿態是當所有確定的界定——生命與藝術、文本與實踐、現實與虛幻、權力與行動、個人事跡與客觀事件——都被懸置時所發生的東西。在這種敞開中,出現,或起作用的是姿態。阿甘本認為,姿態是一種特殊的行為,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屬于第三種行為概念,把它描述為執行(carrying)、承擔(enduring)和支撐(supporting)。它是既不同于任何先驗定義(如生命或藝術),也不同于任何終極定義(telos),包括一切美學定義(如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實踐’(pure praxis)”(Murray and Whyt 79)。 簡言之,作為姿態的文學批評的根本作用就如同“國王的行事”一般,乃是懸置一切既往法則從而重新協商、勘定與平衡邊界的特殊行為。
遵照阿甘本的理解,批評作為文學姿態,它應被理解為既拒絕成為達到文學目的的方法或手段,也拒絕成為文學目的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姿態重新協調并勘定了新的批評邊界,也在另一方面劃定了批評的一個新的獨特領域。這種新的批評邊界至少由三個方面所決定。一個是作品作為對喪失姿態的記錄和挽回,它書寫的乃是人在現代社會淪為命運姿態的必然趨勢。這其中蘊含著人的內在性喪失,未知力量的逼迫,自然生命淪為技術裝置等幾種情況。它們共同肢解了身體并促使其朝向神圣化以便于為獻祭鋪平道路;第二個是作者開始由再現、表征和重塑的角色轉換為“缺席者角色”,借助作者這種“外邊思維”的優勢將那些無名者的生命置入作品的游戲中以揭示各方的姿態;第三個是姿態屬于一個“無目的的”純粹手段領域,而且在現代景觀社會,人類成了真正“在—媒介中—存在”的動物。這個“潛能和現實,本真和矯飾、偶然和必然變得不可區分”的重要領域正是姿態的樂土。人是媒介的動物同時聯系于一種倫理的觀念,而姿態不“做”也不“不做”,而只是持續著、“維持著”,阿甘本認為,它“別無他名”乃是“人類最完整的、絕對的姿勢性領域”,即“政治”(《潛能》 265)。
表面上看,似乎德勒茲(還有瓦羅)、科莫雷爾和福柯都居于阿甘本三篇姿態論文獻的顯耀位置。但事實上,阿甘本姿態論卻是多方面參考了本雅明,甚至“更多地是屬于本雅明的”(Weber 65—83)。 《關于姿態的筆記》,其實可以看作是關于“本雅明的筆記”;《作為姿態的作者》多是本雅明的發展,而《科莫雷爾,或論姿勢》則將本雅明推為20世紀最偉大的批評家之列。此外,阿甘本姿態的空無與中斷,溝通與媒介說都潛在地呼應了本雅明寫于1916年的《論語言本質與人的語言》,以及著名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本雅明在前者中追問語言交流的本質問題,并“試圖在語言中找尋‘無詞語的領域’,希望能喚醒人們對詞語所不能表達的東西的興趣”(萊斯利 33)。這多少可以瞥見阿甘本“純粹姿態”的影子,而在后者中,更是點明了很多后來阿甘本所進一步明確化的東西。
二、作為傳統中斷的本雅明的姿態
在本雅明的批評思想是什么的問題上,本雅明的憂郁氣質一定傳染了那些從事本雅明批評思想研究的學者們,并將他們折磨得不輕。因為,人們熟知,本雅明在文學批評上志向甚高。他不僅立志要做“最偉大的德國文學批評家”,而且決計要“開創一種批評樣式”(萊斯利 108)。可本雅明的研究者們最終發現,甚至連“批評家”的稱號恐怕都難以安置在本雅明頭上。即使偶爾有人對其稱頌有加(如詹姆遜,阿多諾等),但有更多的人卻站到了他們的對立面。直到對本雅明思想最為杰出的闡釋者——阿甘本的出現,才徹底扭轉了這一境況。阿甘本在“姿態論”的最高標準上首次將本雅明推舉到“20世紀德國毋庸置疑的最偉大的批判家”之列,才最終解決了本雅明的批評地位問題,并第一次解答了何謂本雅明的批評思想,這個困擾本雅明研究界多年的根本性疑問。
眾所周知,本雅明受到歌德、德國浪漫派及悲劇理論,19世紀的愛倫·坡、波德萊爾,以及克勞斯、卡夫卡、布萊希特、普魯斯特、布勒東等當代作家的廣泛影響。本雅明與很多作家也都交往甚密,更寫過不少文學批評文章。而且,他認為批評家與以往藝術時代的闡釋者無關,相反,是文學政治中的戰略家。波特萊爾、卡夫卡、普倫斯特以及布萊希特可謂是本雅明批評最多、受到影響最大或交往最密的四位作家。在如何界定這些作家的問題上,本雅明認為波德萊爾的抒情詩既不表現詩人自己,也不與他的讀者之間保持一種親密關系,而是保持一種疏離關系,并且明確地指出波德萊爾的“典型特征是語言姿態”(《波德萊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102);而普魯斯特呢,本雅明說他既不再現生活,也不強調人的日常經驗。相反,普魯斯特的小說是以“讓敘說者將自己的生活嵌入到事件中,以便把它作為經驗一同傳達給聽者”(《波德萊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11)。或者說是以“意愿回憶和非意愿回憶”糾和在一起所形成的特殊姿態而聞名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本雅明更是發現了姿態元素,并得出卡夫卡“全部作品構成了姿態的符碼”(《開箱整理我的藏書:本雅明讀書隨筆》87)的經典論斷;另外還有一位,既是好友又是對他影響至深的布萊希特。據說,還曾因本雅明美學思想中的布萊希特色彩而招致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的不滿。在姿態論上,他受布萊希特的啟發最大。在《什么是史詩劇》中,本雅明提出“史詩劇的本質是姿態”的觀點,這既使得“史詩劇”成為一種戲劇概念,也使得“姿態”成為一個批評概念;此外,在《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鯨〉》中本雅明鄭重告誡文學批評應該持有怎樣的姿態,并將中國戲劇界定為“姿態戲劇”;他還關注拱廊,閑逛者的姿態,及這些姿態者背后的命運問題;他對新藝術中展現的姿態美學也興趣盎然……至此,已經很清楚無誤地表明:姿態而非任何其他概念——比如寓言——才是本雅明在進行批評時所依據的根本思想。而且,我們知道,本雅明終其一生思考的都是基于現代性與政治救贖的兩個鮮明背景下進行的,而姿態范疇恰恰是本雅明貫穿這兩個維度進行批評探索最為主要的思想工具。
30年代,本雅明在他有關卡夫卡的文本和布萊希特的戲劇中發展了自己的姿態理論。這主要集中在《弗蘭茨·卡夫卡》《論卡夫卡》和《什么是史詩劇?》中。《什么是史詩劇?》中,本雅明追隨布萊希特,首先將史詩劇定位于有別于“敘述性作品”的一種需要觀眾參與美學表態的藝術形式。為了滿足這兩個要求,本雅明贊成了史詩劇以傳統歷史事件作為素材的觀點以降低觀眾參與的門檻,以“非悲劇性人物”為主角以迎合觀眾藝術批評的層次。歷史事件的舞臺展現傾向于以事件為中心的場景、狀況的揭示從而在觀眾那里形成“錯愕”與“震驚”,這種美學效果的達成則是通過“中斷情節發展”和“可援引的動作”來實現的(《啟迪》161)。而“中斷情節”和“可援引的動作”的根本目的則在于生產姿態,這便形成了本雅明所說的戲劇是姿態的觀點。就此,本雅明認為姿態是史詩劇的原材料,史詩劇的任務就是這種原材料的合理使用。此外,他還賦予姿態兩個優點:一個是姿態只要達到一定程度上,它才是可以證偽的,姿態越是稀疏平常,它就越難被篡改;一個是不像人們的行動和企圖那樣,它有一個確定的開始與結束。本雅明認為姿態來自于現實,這些嚴格的、框架性的、每個時刻封閉的特質是作為生活狀態之流的整體,是姿態基本辯證的特征之一。這形成了一個重要結論:我們越是頻繁地打斷某人行動中的行為,我們就獲得了越多的姿態。因此,行動的中斷是史詩劇的一個主要關注點(Understanding Brecht 4)。“可援引的動作”是要將某個社會情境離析、孤立出來,甚至是為了突出某個寓有矛盾性質的單一動作,要解離其語境,重新檢視它,并反復操演它,在不同的環境中引用它,剝離它原有的自發性與自然狀態,終至將它引入嶄新的洞察眼光之下。“可援引的動作”,即“引用姿態”,也就是中斷戲劇中的歷史傳統、劇情整體性和情節連續性。姿態還中斷了主體的有目的的行為和行為、情節以及故事的指向結局的運動,而且它本身也是一個行為。于是,本雅明說:“情節的中斷是最重要的”(Weber 65—83)。本雅明所理解的中斷類型乃是從一開始就是非靜止的類型。因此,姿態的生成明顯依賴于運動干預,特別是行為干預(Ruprecht 23—42)。外部行為的介入使得姿態產生一種陌生化,尤其是這里的戲劇姿態不再被視為一種精神活動或美學行為了。可以說,本雅明以姿態及其中斷評論戲劇,在戲劇批評上開啟了戲劇姿態理論范式的轉向(Ruprecht 23—42)。本雅明試圖要“創造一種新樣式”的構想,看來并非是夸夸其談,更不是他對于個人思想事業的某種憂郁的牢騷。這里可以套用他評價布萊希特的話,姿態論戲劇也具有與亞里士多德的“陶冶”悲劇戲劇范式“分庭抗禮”的地位。
本雅明對卡夫卡的闡釋也常常是結合戲劇來討論的。本雅明認為卡夫卡的大多數作品都可以扮演成戲劇,而且只有扮演成姿態的戲劇時,才能充分地廓清卡夫卡的作品。所以,本雅明說:“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構成了一套姿勢的符碼”(《啟迪》129)。這是說,卡夫卡的作品由姿態構成,理解卡夫卡的作品也就必須從姿態開始。姿態可以說是卡夫卡作品意義的樞紐。卡夫卡通過過濾日常生活場景和剝離傳統歷史的支持重組成一種由事件所筑造的謎一般的姿態。卡夫卡作品作為姿態符碼所隱含的是他基于傳統社會的神秘體驗和現代都市的無名體驗。在其中,本雅明看到了作為景觀的姿態(如《弒兄案》《變形記》),作為事件的姿態(如《審判》),作為純粹的姿態(如那些像動物似的姿態),作為命運的姿態(如《在法律面前》《城堡》),作為靈魂的姿態(如《駝背小人》),乞丐“一件襯衫”的愿望姿態,以及桑丘·潘沙極富正義的姿態等等,多種景觀。本雅明認為卡夫卡的世界就是人世的劇場,這個劇場上演的是他的姿態構筑的寓言式戲劇。從中,卡夫卡的姿態敞開了多重美學魅力:“每一個姿勢后面撕開一片天空”,每一個姿態后面都“提供一個令人尋思不盡的命題”,并且,每一個姿態都關乎靈魂的姿態(《啟迪》 130、144)。
在卡夫卡的小說以及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中,本雅明敏銳地覺察到了技術所帶來的疏離關系,也覺察到了自身及其存在的種種命運問題。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對于演員在電影鏡頭前的表演及其后果的深重擔憂做了創造性的姿態闡釋,本雅明指明了演員被懸置的姿態,而非影像本身才是電影藝術的本質所在。另外,本雅明在《對廣播的反思》中也說道:“廣播這種組織機構最重要的過錯是從根本上把演員和受眾永久地分隔開了”(本雅明,“瓦爾特·本雅明論廣播”)。大眾既可輕而易舉地被帶到麥克風前,大眾也同樣輕而易舉地被拋在一邊,成為遲鈍而無言的存在。本雅明在其中看到了演員主體性、藝術靈光以及經驗的斷裂,“關于人類活動和運動的連貫感,一種具化感和可交流感”(穆雷126—27)的消逝。演員在熒幕上看到的是陌生化的自己,那些姿態與他自身的經驗是那么地毫無關系。這時候,本雅明非常清楚地宣布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人們已經失去了姿態。原有的復數的姿態轉變為單數的姿態,一種純粹的姿態,并超越了美學而進入到倫理學、政治學領域。同時,也進入了包括本雅明說的一切都被納入由技術所引發和形塑的生命政治學領域。
三、作為生命政治批評的姿態
本雅明的姿態說具有鮮明的現代政治背景,而他的繼承者與闡釋者——阿甘本,在這方面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更激進。阿甘本三篇姿態論文獻中,有兩篇均以幾乎完全一樣的話語——“政治是人類絕對而完整的姿態性領域”——結束。而另一篇文獻的結尾部分,也只不過是改用了闡述性的話語說了同樣的意思。但令人非常詫異的是,阿甘本都無一例外地拒絕在這些文章中對此做進一步的解釋。結果,姿態何以屬于政治、倫理領域的面貌,本雅明沒有明說,阿甘本更沒有說明。但阿甘本卻是用他的批評實踐實際地展現著姿態何以是倫理與生命政治的問題。可是,這方面的研究在國內鮮有提及,在國外同樣缺乏必要的研究(Dicknson 952—61)。因此,澄清姿態論的倫理政治和生命政治批評維度,顯得至關重要。
文學的生命政治批評的根據,其實,本雅明在他的思想中已經隱晦地做了澄清。例如,本雅明曾強調生命并不僅限于肉體生命,也不完全由“自然來決定”,而“只有當我們將生命賦予一切擁有自己的歷史而非僅僅構成歷史場景的事物,我們才算是對生命的概念有了一個交代”(《啟迪》83)。這就廓清了藝術作為生命及其形式的合法性問題。后來,包括朗西埃、阿甘本等不少當代西方理論家都繼承了本雅明關于藝術是一種生命形式的看法。而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的生命不僅易于辨認,而且是永生的。本雅明已經在他的時代將研究的重點從文學的封閉研究、靜態研究轉向了更加關注文本、社會、事件以及大眾、作家的“變換流轉的語境和組合”以獲得其在實踐層面所具有的復合性意涵的屬于文學“后理論”時代的新階段。本雅明說,文學中的每一個姿態“都是一個事件”,而“每一個姿態后面(都可)撕開一片天空”(《啟迪》129—30)。他把文學從“獨自看書的讀者”狀態帶領進了“作為集體出現”又各自息息相通且具有“參與性”的共同體階段。姿態提供了一個扎根傳統,又疏離傳統,還面向未來的“令人尋思不盡的命題”。通過這種混淆形成一種短暫的、變化無常的組合,進而持續制造出新的事物和事件來。這個歷史維度便是本雅明對姿態所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定。
根據阿甘本的看法,“任何思考生命的思想都與權力共享其對象,并必然會面對權力的策略”(《潛能》423)。那么,姿態作為一種有關人類生命和身體行為方式的理論,自然與政治權力共屬一體。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呈現了姿態在語意上的政治關聯。不管是就單個的生命體而言,還是就作為共同體的“被治理者”而言,抑或是那個僅僅承擔“持續著、維持著”的國王角色,“啞口”與否并無本質的區別。因為,他們的姿態涉及的無非是一種沒有形式的生命類型與生命形式,這種生命形式允許一種沒有確定身份、功能和排他性的社會。此外,博思(Renéten Bos)在他的一篇論文中還指出了姿態在起源上與政治的天然關系。據他考察:在古羅馬帝國時期,政治總是關于姿態的。在議政廳或圓形露天場所的政治演講并不能使聲音有效地傳遞到聽眾那里,因此,杰出的演說家都知道他們并不能被眾人所理解。但當你知道你不能完全依靠你聲音的力量時,姿態便成了你政治表演的最好方式了(Bos 26—44)。與此頗有幾分類似,呂克·南希也展示了具有敘述能力(或權力)的人如何利用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將眾人匯聚起來,進而形成共同體政治的歷程。南希高明地展現了敘述何以發展為文學,文學又何以構成了敘述者的政治地位進而締造成共同體的辯證關系。最終,南希得出了“文學的本質只是一個姿態(geste)”(南希 166)的文學本質主義結論。事實上,姿態作為純粹政治、倫理領域的一個典型例子,可以在當代社會中的諸如靜坐、絕食一類的民眾運動中得以說明。他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申訴,僅僅是靜坐、絕食,既不申訴政治需求,也不游行吶喊,但確是實實在在的一種政治、倫理行為。
說文學是姿態也就將文學置于身體之內,從而與生命政治建立起了關聯。沿著本雅明的經驗匱乏的路徑,阿甘本提出西方現代社會資產階級的姿態喪失。這是阿甘本姿態論的第一個邏輯起點。阿甘本說的人類的姿態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隨著現代技術、科技理性以及權力規訓和道德倫理的發展與滲透而徹底把人作為自然生命的身體姿態消滅掉了這一現實。在阿甘本看來,對于一個失去自身姿態的時代,人們也就越發地執迷于它。而對于失去自身姿態的人們來說,亦即失去了其之所以為人的那些最為本己的東西,也就是說,姿態成為了人類的命運。我們不得不承認迫使姿態失去的乃是某種“未知力量”與無法挽回的歷史趨勢,但結果卻造成了生命的實存便越發地難以解讀與辨認。經驗丟失、靈魂失卻以及人的本己要素的斷裂使得人的日常姿態淪為程式化的模式,即日常的姿態淪為人作為動物性物種的自然動作的他者和相異物。于是,阿甘本說:“人——他的身體的存在已經變得神圣,就它使自己變得不可穿透而言——就為大屠殺做好了準備”(《潛能》262)。姿態的丟失所表明的不僅僅是主客體的分離,它還表明了主體自身的分離。主體的實際經驗、身體感受、姿態行為與理性觀念之間處于一種分離的狀態。身體的表象不再是身體感受的表達了,身體姿態與主體意識處于一種松散關系中。這也就意味著基于日常經驗的自然生命(或者說生物生命,zoē)開始轉向由主體之外的力量、因素(如政治、權力、技術、意識、觀念等)所管控的非主體的生命狀況(bios)中。這樣,姿態潛在地起到了勘定生命的赤裸生存現實與社會/精神生命現實、自由生命與管治生命、真實與虛幻之間邊界的作用。而每一種的界定都同時表明了一種新的身份確立。姿態的生命政治便聯系于一整套的與姿態相關的裝置系統:影像的、情緒的、倫理的、權力的以及觀念系統的。它模糊了各種無差別的身體,并使生物生命與生命政治間的“例外狀態”得以隨時發生。它可以使處于某一狀態的身體驟停、延續或者在不知不覺中變化動作:真實的、表演的、病態的、生產性的、實踐的,如此等等。
為了記錄、保存以及挽回人類的自然姿態防止其“在不可見的權力運作下”(“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68)丟失殆盡,阿甘本賦予現代電影(之前是文學)以“彌撒亞”的角色。這是姿態批評的邏輯過程。它包括電影以記錄姿態的方式試圖挽救姿態的喪失,但電影的記錄不是作為靜態的影像而是作為傳統中斷的“某個姿態的片段”而運動的,最終電影的中心是純粹的中介,它屬于倫理與政治領域而非簡單地審美領域。阿甘本作為姿態的電影理論,一方面從本質上奠定了藝術(電影)屬于倫理與政治領域的合法性;一方面宣告了其中存在著“兩個生命的生命政治生產過程……作為空間中受調查的身體以及運作中的懲戒身體”(Harbord 13—30),即它所關注的乃是在生命政治征用與美學救贖之間被捕獲的人類身體(Clemens 204);最后,它在另一維度也開啟了“從生命政治向生命詩學(Biopoetics)的轉向:展示了運動中人類身體的純粹媒介性,拉開了生命政治關聯,并且捕捉到了赤裸生命的潛能”(Gustafsson and Gr?nstad 8)。 “純粹媒介”是阿甘本姿態論最為本質的特征,也是阿甘本所謂的政治是“人類之絕對而完全的姿態性領域”的另一層意思。因為,政治也是一種無目的的行動、單純的不作為的“行為”與持續、一種沒有依存的舉動。僅僅作為中介性而已,即一種“無目的之手段”。在《未來共同體》中,阿甘本認為倫理是沒有本質、歷史或精神的職業以及沒有人類必須實現的生物學命運。如果人類必須是這種或那種物質的話,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倫理經驗。人類只有“做”的任務。所以,阿甘本說姿態范疇就是倫理范疇。
“人類—在媒介中—存在”的思想敞開了人類在現代社會中的倫理維度。2016年4月在劍橋大學召開的以“邁向姿勢的倫理學”(Towards an Ethics of Gesture)為主題的研討會就是以阿甘本的這個基本觀點作為出發點的。阿甘本所認為的倫理學是沒有內容的,它既不關于生產,也不關于實踐,而僅僅是一種手段而已。阿甘本說:“姿態被生命權力征用[……]姿態提供了一種朝向未來的敞開,提供了一種作為無政治、無科技、無身份政治實現的未來共同體的敞開,它是作為純粹媒介的政治、無目的的手段”(“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194)。因此,“姿勢[……]只在必須被用作重新思考倫理與政治之奠基的那個門檻上出現。姿勢因此也就起到了不作為的作用”(穆雷 131)。
在《作為姿態的作者》中,阿甘本通過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鯨》中菲利波芙娜的人物命運,指出了作品中的姿態如何通過懸置道德法則而被置入生命的游戲中并最終才是倫理的。他說道:
菲利波芙娜把她的生命置入了游戲,或者說,也許,她允許這個生命被梅什金、被羅戈任以及,本質上,被她自己的狂想置入游戲。這就是為什么她的行為無法解釋;這就是為什么她在她所有的行動依然保持完美的不可進入、不可理解的狀態。不是在生命服從于道德法則之時,而是在它接受于它的姿態中把自身不可逆轉且毫無保留地置入游戲之時——甚至冒著這樣的風險:它的幸福或它的恥辱一次性地被決定——生命才是倫理的。(《褻瀆》69)
阿甘本指出,作者的價值就在于在作品中貢獻一個獻出的生命并被游戲,而不是被表達或被完成。作者通過設置的這種“空無”或“缺席”,“不被滿足和不被言說的狀態”,才使“確保了作品的生命”,確保了批評的空間。
將人(污名的人)的實存的生活與文學綁定在一起,并不是再現/表征或重塑的關系,而是更為本質的東西。按照阿甘本的說法,乃是姿態。阿甘本借助福柯論述道,“污名者”的“真實的生命被‘游戲’”涵蓋了多重意味:第一是誰將他們置于游戲之中,并蓄意保持他們的無名狀態;第二污名的人是否徹底放棄過自己,而把自己交付給其他東西(如,某種生活狀況,或事件);第三污名者的生命應由造成其結果的權力及其要件(如機構或權力者)負責,還是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命運。對此,阿甘本聲稱:“污名的生活只是被游戲;它從未被占有,從未得到再現/表征,也從未得到言說——而這就是為什么它是某種倫理的,和某種生命之形式的,但同時又唯一可能的是空無的場所”(《褻瀆》67)。阿甘本認為把生命置入游戲,既拒絕讓生命服從于道德法則,也拒斥生命匍匐于權力的腳下,“而是在接受它的姿態中把自身不可逆轉且毫不保留地置入游戲之時——甚至冒著這樣的風險:它的幸福或它的恥辱將一次性地被決定——生命才是倫理的”(69)。這種毫無任何目的的純粹手段,即將“一個生命被獻出并在作品中被游戲。被獻出且被游戲,而不是被表達或被完成。”作者在一種“空缺的狀態”發出話語,如果小丑的滑稽動作不斷打斷舞臺上延續的情節并持續揭露情節一樣,作者就是借助這種姿態“通過某個不可表達的外部邊緣不可還原的在場,才確保了作品的生命”。
如果從阿甘本的電影始于人類失去自身姿態的那一刻的觀點來看,文學也同樣可以這么認為。而且,失去姿態同時意味著內部交流的失去,顯然這對以內部情感溝通為主的文學而言也是致命的。這一看法,一方面部分解答目前人們所憂慮與不滿的文學脫離現實的重大疑問,另一方面也宣告了文學作為外部裝置的誕生和生命政治文學批評方式的開始。對此,阿甘本暢想了姿態批評的美好愿景:作品的批評“被賦予其最高的姿勢后,作品繼續活下去,像沐浴在末日之光中,在其形式的服飾和概念的意義毀滅之后幸存下來的造物”(《潛能》157)。但是,我們既要看到姿態“對主體性崩潰和美學崩潰的駕馭(harnessing)”(穆雷 131),也要看到文學淪為“一道筆畫——一個切口和/或一次銘寫”(南希 166)的危險,看到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把對寫作者的漠然視為“當代寫作的一個根本倫理原則”,寫作呈現為一種游戲、一種空間創造,一種抵抗死亡的活動的當下現實。從另一方面來說,姿態的文學批評與生命政治的關聯,還可從福柯的這一觀點中得以理解。他說“寫作開始和獻祭、甚至和犧牲生命相聯系:它現在是代表一種自愿的毀滅,自我已經不需要再現在書中了,因為它已經被帶入了作者的存在之中”(Foucalt 117)。所以,姿態并非是要尋求一個拯救的主體或者革命主體,它僅僅是我們所生活的扁平化,社會的癥候,并且在其中尋求超越的潛能。這是姿態的生命政治批評所需要明白的。
姿態批評給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進入政治與倫理的開始,并將文學置入生命政治理論視域之內。它把文學關注的重心從有關于作品的結構、布局以及內部關系及其相互間的互動等美學研究轉向了有關于身體行動、實踐、行為以及國家治理層面上了。這既不同于西方形式主義、語言論、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方式,也有別于馬克思的社會歷史和階級分析法。姿態論范式的提出標志了文學批評從美學領域轉向了生命政治批評領域(Gustafsson and Gr?nstad 2),“姿態轉向”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管治技術的層面上思考了生命何以更幸福、更美好地存在,這么一個根本性的“后理論”(after theory)的批評范式。
結 語
阿甘本與本雅明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沉思了人類、藝術在現代性之后的命運問題,其不同之處在于本雅明在現代性中以他憂郁的氣質于消逝中看到了革命性,而阿甘本則更多的顯現出激進的政治意涵。他們分別都以各自獨特的姿態呈現了不同現實中藝術與人類(主要是生命政治理論中的人民問題)淪為景觀、形式、姿態與空無的經驗遭受到某種否定與毀滅的未來面向。如果說本雅明以姿態論史詩劇引入了戲劇姿態理論轉向和新的戲劇理論范式的話(Ruprecht 23—41),那么,他和阿甘本的姿態論可以說在文學批評中也完成了同樣的事情。現代有關姿態的論述涉及本雅明、海德格爾、福柯、梅洛-龐蒂、南希、阿甘本、巴特勒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理論家,并且橫跨從文學、視覺以及表演藝術,到人類學、神學、哲學以及媒介研究的廣大領域,其在身體與世界、自我與他者、靜止與運動、持續的行為、普遍與特殊之間有著巨大的運用空間。不僅如此,姿態論對于解答文學的本質問題,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以及生命政治批評是否是一種美學批評問題的理論質疑都提供了一條有益的思考路徑。然而,作為一種后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理論,姿態論所引領的批評范式轉向以及所開拓的批評領域,相對于中國文學理論的批評實踐來說,其革命性的意義尚未被揭開。
引用作品[Work Cited]
Agamben, Giorgio.Means Without End.Trans.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吉奧喬·阿甘本:《褻瀆》,王立秋譯,芬雷校。潑先生書籍,2012 年。
[---.Profanations.Trans.Wang Liqiu.Pulsasir, 2012.]
——:《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
[---.Means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Trans.Zhao Wen.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潛能》,王立秋等譯,沙明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Trans.Wang Liqiu, et al..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2014.]
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
[ Arendt, Hannah, ed.Illuminations: Selected Works of Walter Benjamin.Trans.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Benjamin, Walter. Understanding Brecht. Trans. Anna Bostock.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瓦爾特·本雅明:《波德萊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王涌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Trans.Wang Yong.Nanjing: Yilin Press,2014.]
——:《開箱整理我的藏書:本雅明讀書隨筆》,張佐臣等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
[---.Unpacking My Library.Trans.Zhang Zuochen, et al..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4.]
——:“瓦爾特·本雅明論廣播”,庫岑譯。《熱風學術網刊》1(2016): 73-79。
[---.“Radio Benjamin.” Trans.Ku Cen.HotWind Forum 1(2016): 73-79.
Bos, Renéten. “ On the Possibility of Formless Life:Agamben's Politics of the Gesture.”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5.1(2005): 26-44.
Colilli, Paul. Agamben and the Signature of Astrology:Spheres of Potentiality.New York: Lexington Books,2015.
Dicknson, Colby.“Beyond Violence, Beyond the Text: The Role of Gesture in Walter Benjamin and Giorgio Agamben, and Its Affinity with the Work of René Girard.” The Heythrop Journal 52.6(2011): 952-61.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Trans.D.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Fleming, Paul.“The Crisis of Art: Max Kommerell and Jean Paul's Gestures.” MLN 115.3(2000): 519-43.
Gustafsson, Henrik, and Asbj?rn Gr?nstad.Cinema and Agamben: Ethics, Biopolitics and the Moving Image.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Harbord, Janet.“Agamben's Cinema: Psychology Versus an Ethical Form of Life.”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4.2(2015): 13-30.
Kendon, Adam.“The Study of Gesture: Some Observations on Its History.” Semiotic Inquiry 2.1(1982): 44-62.
伊斯特·萊斯利:《本雅明》,陳永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Leslie, Esther.Benjamin.Trans.Chen Yongguo.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Murray, Alex, and Jessica Whyte.The Agamben Dictionary.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艾利克斯·穆雷:《論阿甘本》,王立秋譯,芬雷校。潑先生書籍,2012年。
[ Murray, Alex.Giorgio Agamben.Trans. Wang Liqiu.Pulsasir, 2012.]
Clemens, Justin, Nicholas Heron, and Alex Murray.The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Law, Literature, Life.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讓-呂克·南希:《無用的共同體》,郭建玲等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Nancy, Jean-Luc.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Trans.Guo Jianling, et al..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Ruprecht, Lucia. “ Gesture, Interruption, Vibration:Rethinking Early Twentieth-Century Gestur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alter Benjamin, Rudolf von Laban, and Mary Wigman.” Dance Research Journal 47.2(2015):23-42.
Weber, Samue.“Going Along for the Ride: Violence and Gesture:Agamben Reading Benjamin Reading Kafka Reading Cervantes.” The Germanic Review: Literature,Culture, Theory 81.1(2006): 6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