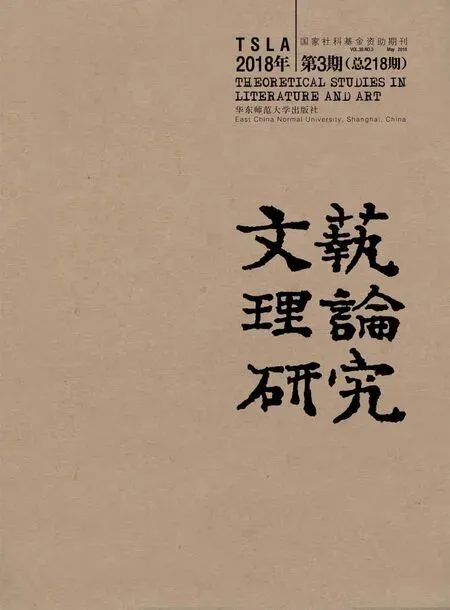《詩大序》的“后結構主義”詩論
——兼談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化
顧明棟
中國文論源遠流長,但因其鮮明的特征而被認為與現代詩學是方枘圓鑿,因此中國文論的現狀是,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恰似兩股道上跑的車,各走各的道,基本上互不搭界。這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治學路徑不僅使得傳統文論和現代文論喪失了對話的機會,也遮蔽了古代文論的精辟思想和啟示。以古代《詩經》詮釋傳統的綱領性文獻《詩大序》為例,這篇看似與現代詩學相去甚遠的古典文論,不僅在思想內容上與現代詩學相關,而且在書寫形式和論證方法上也與后結構主義詩學有著不為人們輕易覺察到的異曲同工之處,有意義的是,其相同之處正是來自我們一般認為與現代詩學風馬牛不相及的小學或叫做文字學(philology)研究。本文擬從后結構主義話語理論的視角重新細讀《詩大序》的文字表述、思路演進和總體結構,采用傳統小學與后結構主義理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達到四個目的:一是要證明以傳統小學為根基的古代文論與后結構主義詩論并沒有無法逾越的鴻溝;二是歷史上至今為止對《詩大序》存在著這樣的誤解,即《詩大序》非有意為之的詩論,缺乏內在的統一性和連貫性,并由于在流傳過程中出現“文本變質”,因而是一篇結構混亂,主旨無法一以貫之的文論。本文通過破除歷史上的誤讀,以達到為《詩大序》的價值重新正名的目的;三是通過從后結構主義的視角對《詩大序》重新細讀,并將其與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相比較,搞清楚《詩大序》究竟是什么性質的詩論;四是試圖給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化提供一點啟發。
《詩大序》在歷史上的誤讀
《詩大序》雖然只有區區幾百字,但其對中國古典詩學的貢獻一直得到歷代學者的承論,被譽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第一個里程碑,提出了中國文學理論的一些原創思想。其非凡的洞見不僅對詩歌的起源、本質、功能、批評和創作實踐等核心問題做了探討,而且也為中國詩學理論奠定了基礎。因此,作為中國文學思想的基礎文本,《詩大序》不僅對《詩經》詮釋具有特殊意義,而且對中國詩歌和詩學也具有普遍意義。作為專論中國詩學的第一篇論文,《詩大序》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已經得到充分評價,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其特殊的來源和種種所謂“缺憾”而受到苛責和批評,并未被視為中國傳統第一篇有意為之而首尾一致的文論。首篇自覺文論的殊榮一直由曹丕(187年—226年)的《典論·論文》所擁有。筆者認為,《詩大序》的價值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里并沒有得到充分而又公正的評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學術評價只聚焦于兩個表層。一個是它始終被視為漢代以前對《詩經》進行闡釋的儒家闡釋的綜合(蔡鐘翔等85)。另一個則強調其作為狹義文學理論即《詩經》評論的意義。在這個層面,它始終被視為只是一篇專門探討詩歌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文章。這兩方面實際上都只是涉及該文獻的內容,而對于《詩大序》的整體性和形式美學意義幾乎沒有觸及,更無人注意到其在形式創作方面所隱含的可與后結構主義詩學相媲美的詩學意義。
回顧歷史上的評價,《詩大序》被誤認為令人遺憾的問題中最受詬病的缺陷就是其缺乏內在的統一性和連貫性。由于這個缺陷,學者們感到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理解,對《詩大序》各節重新編排,并將新排的劃分重新分配給《詩經》中的不同詩篇。歷史上,最徹底的重新排序為宋代儒學集大成者朱熹所為。他打亂整篇文章,把開頭和結尾劃入“小序”,分屬《詩經》的第一首詩,即“關雎”。在當代研究中,學者們對《詩大序》的內容和形式也不乏批評。在內容上,批評主要集中在政教層面,認為《詩大序》秉承儒家的意識形態,宣揚封建主義教化,為統治者奴役人民服務。時至今日,這種過于政治化的批評已經沒有多少價值。在形式上,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雖然高度評價《詩大序》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地位,但對其構思和篇章結構并不看好,認為不過是歷代出自不同來源的注疏材料的松散綜合(Owen 38)。宇文所安的一個學生斯蒂芬·范左倫順著老師的路徑,對《詩大序》的結構提出了可以說是最為尖銳的批評,他聲稱:《詩大序》“大起大落和暗示的論證特點,突兀地從一個主題跳向另一個主題,在最不需要的地方使用連接詞,這是一個連最富同情心的讀者也會感到無可奈何的文本”(Van Zoeren 97)。與歷史上其他學者一樣,他認為《詩大序》是根據傳承下來的小學材料而建構的多層次復合文本,其中不存在著內在的統一性和連貫性,甚至認為它的特征就是由于流傳過程中“文本變質”而導致的“混亂”。顯然,他和歷代學者包括他的老師一樣并沒有認識到《詩大序》獨特的組織結構,更沒有認識到其繼承小學注疏傳統所隱含的后結構主義的書寫方式。
后結構主義與傳統小學及《詩大序》的相關性
《詩大序》真的如歷代學者所批評的那樣結構混亂,主旨無法一以貫之嗎?也許完全從傳統小學的視角研讀可能會得出這樣的印象,但將傳統小學的方法和后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相結合,就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在此,筆者根據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方法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詩大序》是主旨鮮明,構思精巧,論證連貫的詩論,其獨特的結構和論證形式恰恰建立在看似過時的小學(文字學)基礎之上。其表現方式與其內容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加持,含有隱性的閱讀和書寫模式,也許可以稱之為古代后結構主義的詩論,這是因為其意指結構與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說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和德里達所說的“撒播”(dissemination)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互文性”是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的一個后結構主義的概念,在論述文本的本質時,她認為:“一個文本是眾多文本的交匯,人們至少可以從中讀出另一個文本來。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Kristeva Reader 37)。在論述解構主義的意指理論時,德里達使用“撒播”一詞來描述文字本來所具有的能力,并認為是構成文本和意義的方式。他認為,文本的表意方式就像農人在播種時的情形那樣,因為意指活動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文本的意義就像撒出去的種子那樣,既沒有中心,也沒有確定的能指,而是在不斷變化,因此,文本不是一個封閉而又一層不變的言語結構,而是一個文字自由流動的詮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文字就像播撒出去的種子,自由地生長。德里達所說的“散播”是文字充滿能量和創造力的自我擴散運動,這種擴撒既沒有主體,也不受人的控制(Derrida,Dissemination xxix-xxxii;26)。顯然,德里達的思想與海德格爾所說的不是人決定語言的意義,而是語言決定了人的思想一脈相承(Heidegger 210)。筆者雖然對過于強調語言文字的能動性表示保留意見,但不得不說,互文散播的書寫理論剛好與《詩大序》來源、文章結構和意指活動如出一轍。也就是說,《詩大序》創造了古代的互文散播的讀寫范式,這個范式不僅確立了閱讀《詩經》的路徑,而且影響了中國傳統的詮釋學發展。本文中,筆者不想探討這個閱讀范式如何影響了其他經典作品的詮釋這個復雜問題,只是試圖把討論局限于《詩大序》成書的總體結構,以及它如何隱含地提出了一個開放范式,并預示了當代閱讀和書寫理論的開放詩學。
從歷史上的評價來看,《詩大序》無疑給人一種松散隨意的印象。關于《詩序》的作者,歷來眾說紛紜,言人人殊,漢代鄭玄說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六朝范曄認為是東漢的衛宏所作,唐代認為是子夏、毛亨合作,宋代王安石則認為是詩人自作,鄭樵更認為是村野粗人所作,程頤甚至認為是孔子原作。自宋代起,朱熹、姚際恒、崔述、皮錫瑞等都認為是衛宏所作。但也有學者認為,《詩大序》非出自一人之手,從孔子到無名詩人都可能有所貢獻,衛宏可能是集錄歷代文獻最后寫定者。究竟其作者是何人,至今尚無定論。不管作者是誰,初讀此文,給人的印象是,此人似乎在進行一次無拘無束的思想旅行,隨心所欲地朝著他選擇的方向行進。對《詩大序》松散隨意印象的一個解釋是,作者不得不對與他的主題相關的現存資料進行綜合,而這些資料如此松散多樣,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它們串聯起來。然而,筆者認為,細讀此文,可以發現,作者并不是隨心所欲,跟著感覺走,而是事先有一個主導思想和一個設計好的結構,在徹底消化了現存資料之后,他根據這個主導思想和設計建構了他的論文。其主導思想就是政治批評和道德規訓,而形式呈現的設計就是歷史悠久的訓詁方法,也就是處理中國古代文獻的體系復雜的文字學(philology)研究方法。筆者認為,訓詁原本是一種詮釋方法,但《詩大序》的作者卻把它發展成了閱讀和寫作的方法。
時至今日,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研究文學的文字學方法似乎已經過時。然而,筆者認為文字學研究方法與后結構主義方法并不像有人所認為的那樣大相徑庭。作為歷史悠久的學問分支,中國文本的文字學研究與西方文學的文字學研究在某些根本方面是相通的。這種研究的復雜性筆者在此難以概括,有興趣者不妨查閱訓詁與訓詁學方面的著述,這里筆者只想嘗試尋找中國文字學研究與當代批評范式之間的共同點。中國文字學與現代文學研究之間的一個明顯接觸點就是關注文學文本的創作條件:即撰寫文本所用的物質材料,即文字。中國文字學有一些基本的詮釋原則。其中兩條是“以形索義”和“以聲索義”(陸宗達 王寧 56—134)。如筆者在《周易》和《詩經》詮釋研究中所展示的,文字學研究的這兩條基本原則是造成各種不同矛盾解讀的原因(Gu Mingdong 257-82;顧明棟 1—14)。 在《詩大序》的創作中,作者把這兩條基本原則變成了我們編織理論文本的經緯,據此開創了一種獨特的寫作原則,與現代和后現代關于符號之物質性的觀念具有某種相融性。根據后現代文本研究,話語的物質性稱作文本性,這個術語是說文本是由詞語而非抽象概念構成的物質實體。筆者冒昧地提出,中國文字學中廣泛應用的技術在某些方面與西方后現代文本研究是相一致的。文本性(textuality)與文字學(philology)的區別在于,前者公開承認語言不是簡單生產對外部世界的指涉,而是在寫作和閱讀過程中生產多樣性的潛能,即不同的、矛盾的甚至對立的意指流動的潛能。基于這樣的構想,后現代文本研究就與封閉的再現和闡釋相對立,而拒斥把文本視為自治、有自身目的、具有明確原始意圖的文本觀念。
中國文字學與文本研究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可比之處。克里斯蒂娃把文本視為包含許多符號系統的一個網絡,并與其他意指實踐系統相互糾纏。她把互文性描寫為在文本層級化的符號實踐內部的“文本排序”,是在歷史和社會語境內排列不同文本層面的類型學(Revolution 59-60)。在某種意義上,《詩大序》恰恰就是以這樣一種觀念構思的。在文學的文字學研究中,一位傳統學者會集中精力尋找最早出現的文本因素及其源出,然后基于這種起源研究闡釋文本。這與嚴格的互文性研究異曲同工,只不過后者的核心是不同文本之間的關系。然而,文本研究的文字學風格不涉及影響追溯,這是互文性研究試圖取代的一種傾向。因此,克里斯蒂娃喜歡用“換位”而非“互文性”,因為“從一個意指系統向另一意指系統的過渡要求一種新的表達——即表達和指稱的位置性”(Revolution 60)。此外,對起源和暗指的偏執式關注極少問及起源是如何應用或改造的。所以,文字學研究常常錯失諷刺、戲仿和曲解在闡釋中的文本效果。與文字學文本研究相去最遠的是無限制的符號學或撒播的觀念,即文本作為組織、“組織學”或蜘蛛編網的概念(Barthes 64),以及解構的觀念或所有話語都存在著互文性的觀念,因為每一個文本都是一次編織或“能指的編織”,其所指在定義上是由其他話語互文地確定的(Derrida,Positions 15-36;Writing 196-231)。
《詩大序》的后結構主義文本細讀
文本細讀是新批評理論的核心,新批評理論雖然已經過時,但文本細讀的方法卻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的文學批評,經過后結構主義話語理論的洗禮以后,新批評的細讀方法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新批評的細讀方法主要用來分析文學文本,筆者認為經過后結構主義理論改造過的新批評細讀方法可以用于一切文本,包括文字文本,圖象文本,甚至文化實物和文化現象。在本節中,筆者擬使用后結構主義的細讀方法分析《詩大序》的文本,為公正客觀地估算其價值提供有力的論證和文本支撐。具體來說,筆者將進行一種重讀,以證明中國詩學的洞見何以最初見于《詩大序》?它所承載的批評思想何以能超越傳統小學?其構思為何展示了一種后結構主義的閱讀和寫作范式?其結構為何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精心安排?其總體上為何是一篇主旨鮮明,構思精巧,論證連貫,見解獨到的詩論。為此目的,筆者需要一字一句地分析整篇《詩大序》。我們且從第一段開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大序》的第一段以《詩經》的第一首詩為切入點,并以“風”這一關鍵詞為整篇文章的結構奠定了“互文撒播”的結構原則。開篇伊始,就總結了《詩經》中第一首詩“關雎”的公認主題。“關雎”也是《國風》中的第一首詩,《詩大序》則稱之為“風之始”。在接下來的論述中,“風”即刻就成為一個多價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現在“風”已經不是一個名詞了,而成為動詞,意即“搖動”或“影響”。以此內涵,該詞便與孔子的話相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十三經注疏》2504)。強風之下搖動的草,這個比喻生動地說明了道德教化的力量。由這一互文起源,《詩大序》將“風”定義為“風也,教也。”這個定義是同一詞的重復,表示了該詞的兩層意思:一個字面意義,另一個喻義。字面義涉及自然風的自然力;喻義指美德的教化力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第二段從對一首詩的分析轉向對詩歌生成起源的思考: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這一段不僅論及詩歌,而且涉及音樂舞蹈,因而不僅是文學起源論,而且是藝術起源論。與西方文論相比,無論是柏拉圖的著述中,還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中,都找不到與之相似的觀點。柏拉圖的“迷狂說”好像與之有相似之處,但仔細分析,兩者是很不相同的。“迷狂說”聲稱詩人因神靈附體而詩興大發,從理性的角度看其實就是無意識創作論。而《詩大序》文藝起源說是指情感郁積于胸,不能自已,情不自禁地以詩歌、音樂、舞蹈等形式抒發胸襟。這種抒情表現的詩論,與英國著名浪漫派詩人華茲華斯對詩的定義“詩歌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西方直到18世紀浪漫主義興起才流行開來。《詩大序》的詩歌起源說奠定了中國古典文論的抒情表現的核心思想,這一思想是通過“風”的多種形式而得到表現的。
從行文結構上看,《詩大序》的第一段到第二段的過渡看似有點突兀,但其內在邏輯上從“風”的涵義來看是自然而又清晰的,這內在的邏輯就是修辭學的提喻(metonymy),即用具體指代一般的修辭方式。“關雎”作為一首具體的詩歌起著二重提喻的作用,一是指代《國風》,二是進一步指代一般詩歌。通過二重提喻,對具體的一首詩歌的評論就過渡到對一般詩歌起源的思考。因此在結構上,第二段自然要進入關于“詩”的討論。這里“詩”也有兩個意思:指特殊的《詩經》和普遍的詩歌。關于詩的定義是一種語義重復:“詩言志。”有些學者以文字學研究指出“詩”與“志”是同源詞(Chou Tse-tsung 151-209)。 《詩大序》肯定了二者的象征關系,指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一論斷以互文形式與前述詩歌起源聯系起來,即《尚書》中的“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131)。《詩大序》進一步探討詩歌的起源,發現其源頭是情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這一探討擴大了“志”的范圍,預示了陸機(261年—303年)提出的新的詩歌觀念:“詩緣情而綺靡”(陸機225)。第二段的其余部分討論情,以及情通過不同媒介、詞語、聲音和狀態而發生的變化。這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前述的互文響應;事實上,是對《禮記》中兩段話的重構(《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1527—45)。關于詩歌起源“情”的分析自然開啟了第三段的文字:
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第三段繼續討論“情”及其變化,其力量和影響。該段援引各種功能以證明詩具有最高形式的說服力。這番論述再次重構前述起源,并在《禮記》(《十三經注疏》 1527)和荀子(約公元前300—230年)“樂論”(荀子 332—42)中找到回應。但是這段話的創新之處是不可低估的。首先,它從前述關于音樂的論述不經意地過渡到詩歌的討論。其次,它使用有力的修辭使關于詩的道德和功利觀聽起來自然而然。接著,重點又轉向對詩歌的檢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關于詩的定義和功能的討論導向第四段中對其顯在形式和再現模式的討論:詩有六個意義范疇:風、賦、比、興、雅、頌。六義的概念再次觸及一種互文關系,因為它源自《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796)《周禮》列出六種詩,《詩大序》提出六義的范疇。從六詩向六義的變化意味著作者意識到這六個術語不僅指六種詩歌,還代表了六種不同的分類形式。雖然《詩大序》并未把六個術語據其功能分成兩個獨特組合,但的確隱含一種分類,孔穎達在其《毛詩正義》中予以了更加清楚的闡釋(《十三經注疏》271)。在這六個術語中,風、雅、頌涉及《詩經》的三個部分;賦、比、興乃是三種再現方式。一旦仔細檢驗這段話,我們必然發現,其劃分并不像孔穎達劃分得那么清晰。“風”當然相當于《國風》,但在《詩大序》中,它卻并未完全指個國別之詩歌,作者依然專注于“風”的文字游戲以使其一語雙關。第四段在繼續把玩“風”之游戲。“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基于雙關或同音,“風”的一個新義在此出現了,即諷刺之“諷”。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國政和道德的衰落致使“風”改變其原始功能。故此出現了“變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這番陳述所強調的是如何修飾抗議的言辭以便使批評變得間接、順耳、容易接受。“風”依然是一種表達形式。“變風”和“變雅”則更關注內容。因此都直接與《詩經》中風、雅相關。
由于賦、比、興三種表達方式只在《詩大序》中略微提及,有些學者質疑其在《詩大序》中的恰當性。筆者認為,由于《詩大序》集中討論詩之緣起、本質和功能的政治和道德問題,這三種再現方式并不是所指內容,因此只是順便提及,在其余篇幅中再未出現過。而“風”是一個多價詞,既是所指內容又是含蓄形式,所以它既能完成詩的政治、倫理和實用功能,同時又能滿足直接表達和間接批評的形式需要。所以,“風”依然是討論的重點:
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有別于“變風”的是不變之風或曰盛德:“雅者,正也。”現在,通過互文暗指和詞語游戲,《詩大序》把《雅》中的詩歌與政事聯系起來。首先,這里暗指《論語》中的一段話:“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2504)。《詩大序》接著對“政”字玩起了文字游戲。通過同音關系,“正”(禮儀)演變成“政”(管理)和“王政”(統治者的政府)。正如政府有其主要形式和次要形式,于是就有了“大雅”和“小雅”。盛德和正當管理必須歌頌,并報告給神靈。于是就有了《頌》。有些學者發現“頌”與“容”是二詞同根。其緊密關系可見于相同的韻母“ong”。事實上,歌頌某人就是用詩歌語言描寫他的美德。詞語游戲再次被用于詮釋和寫作。
該段以稱“風”“大雅”“小雅”和“頌”為“四始”結束。對這四部分的討論圍繞“志”或《詩經》的內容進行。這種以內容為指向的討論不僅表明對賦、比、興只給予少量關注的合理性,而且暗示這三個術語指代三種表達方式,因此不在作者所論《詩經》之功利性考慮范圍之內。最后,討論回歸開篇的主題,即對一些詩的批評實踐: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這段提及《麟趾》《鵲巢》《騶虞》和“二南”等詩,不僅使得朱熹的重新分段顯示出了問題,而且毫無疑問地表明作者關注的是一般的文學批評。因此,最后一段回歸《詩大序》開篇提出的主題。它仍然通過“風”而與正文相關。“風”包括“二南”和十五國之風。就仿佛作者在期待未來各代人的質疑:此“二南”何以未被題名“國風”?作者答曰:二南亦風。一是王者之風,另一是諸侯之風。《詩大序》以對“關雎”的主旨分析結束,這一收尾做法與開篇的討論相呼應,構成了一個三明治式的結構框架。
《詩大序》僅以區區幾百字的篇幅,探討了一般詩歌以及特定的《詩經》之起源、本質、功能和形式。就其評論的對象《詩經》而言,它通過重點解讀“關雎”一詩,將其與可能的社會、政治和道德語境聯系起來,收到了窺一斑可見全豹的效果。現代學者雖然可以批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曲解了“關雎”的內容,但它不僅對詩歌的概念性問題做了基礎性的探索,而且還對詩歌批評提供了一種有趣的閱讀范式,其一些見解甚至預見了當代開放性詩學的洞見。
這篇論文的獨具匠心之處是對“風”這一多義關鍵詞的巧妙運用,圍繞這一關鍵詞,作者創造了一種別具一格的書寫模式,它基于文本性,近于互文性,強調相似于互文撒播的能指交織。它甚至展示出一種解構傾向。文中“風”的撒播產生出眾多意義:自然之風、道德影響、習俗禮儀、諷刺之諷、不變之風、變風、四面來風、王者之風、諸侯之風。在所有這些不同意義之中,有些是相互融洽的,有些是不兼容的,有些是相互對立的。比如,不變之風與變風對立,這是其內涵意義所隱含的。不變之風相關于不變的政府、倫理德性和正面價值。變風產生于社會混亂、道德墮落和反面話題。不變之風意為歌功頌德。變風意為批評。就社會關系而言,“風”或指統治階級有說服力的影響,或指被統治階級的大眾情緒。如果影響是道義的,那么“風”就是兩個對立階級的橋梁。如果影響是墮落的,那么“風”就是揭示了兩個沖突階級的隔閡。從整體意義上來說,《詩大序》是以“風”這一核心概念為中心、以互文散播為構思布局和展開論述的方法、以“風”所演繹生成的詞語為建筑材料而構建的一篇具有后結構主義性質的詩論。
歷史上學者們的誤讀始于沒有看出《詩大序》中對總體結構所做的自覺而細致的努力。朱熹對文本的重新分段不僅妨礙了我們的閱讀,而且蒙住了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不到其隱含的寫作范式,而本文從事的細讀則可以使其本來的面目清晰可見。根據上述重新細讀,筆者得出這樣不同于現有結論的看法:《詩大序》獨具匠心,構思嚴密,技巧嫻熟。它既適合于作序,又把整部《詩經》作為其研究目標。但同時并沒有對更大目標視而不見:即一篇論詩之道德和實用功能的論文。作者無論是誰,都承擔了三重角色:理論家、批評家和學者。應運而生的結果就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的綜合。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產生于需要對現存資料的重新思考,因此也可以看作是集處于雛形階段的元理論、元批評和元學術研究于一體的詩論。歷代研究大多注重《詩大序》開創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政治倫理批評傳統,而忽視了其注疏式分析方法帶有詮釋學、修辭學、形式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洞見。《詩大序》這一方面的思想傾向在后世沒有得到發揚光大實在是令人可惜的事。
結語:古代的“后結構主義”詩論
中國早期文學思想一直被視為缺乏自覺性和系統性,是各種直覺感悟與印象式評點相結合而獲得的知識堆積,甚至是傳統小學的注疏考證的副產品,尚未上升到現代文論那樣體大思精,見解深刻,自覺寫就的詩學。《詩大序》亦未逃脫如此評價。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雖然對《詩大序》在中國文論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關于中國傳統詩歌之本質和功能的最權威論述”(Owen 37)。但他在其闡釋《詩大序》的研究中,把《詩大序》與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相對照,認為其帶有中國傳統序跋的鮮明特色,松散的注疏式結構尚不能使其稱為有意而為的詩論。但是,筆者前面的細讀可以表明,《詩大序》作者建立詩論的方法與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方法其實并無根本不同,走的都是通過分析作品予以歸納而得出文藝思想的路徑。亞氏是以分析古希臘的史詩戲劇而構建其詩學,而《詩大序》作者是在分析了《詩經》的風雅頌詩篇以后概括而得出的詩論。不同的地方是,亞氏的詩學是鴻篇巨制,《詩大序》的詩論短小精悍。亞氏的《詩學》以詩的模仿說為核心,而《詩大序》作者則以抒情表現的“風”論為核心,兩者開創了中西文論截然不同的主流文藝思潮:西方直到18世紀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的是模仿再現論,而中國直到近代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是抒情表現說。亞氏的《詩學》因其長篇大論對模仿技藝的分析精細入微而體大思精,《詩大序》作者因其短小的篇幅只能提綱契領地闡述“風”的抒情表現觀點,使人覺得有言猶未盡之感。在體量上,《詩大序》的確無法與亞氏的《詩學》相比,但《詩大序》構思和論證的方法頗有后結構主義詩論的意味。
學者們通常認為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中國傳統第一篇自覺且系統的文學理論。筆者的分析以充分的理由說明,這個公認觀點應該予以修正。《詩大序》作為有意為之的詩論可以從其評論的文本《詩經》的宏觀構架方面得到證明。《詩經》由三大部分組成:《風》《雅》《頌》。《風》有《十五國風》,《雅》有《小雅》和《大雅》,《頌》有《周頌》《魯頌》和《商頌》。無論是《十五國風》,還是《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和《商頌》,其實都是不同國別、不同形式和不同功用的歌謠,也就是不同性質的“風”,即現代人常說的采風之“風”。《詩大序》把《詩經》中的各種詩歌性質和功用都討論到了,說明作者在撰寫《詩大序》時并非隨心所欲,而是對各種詩歌都了然于胸然后才下筆撰寫,文章以談論《關雎》的主題開始,中間以與《關雎》相關的一般詩歌問題而展開概念性探討,最后以對《關雎》的結論而結束,首尾相顧,渾然一氣,《關雎》之所以能起穿針引線的構建作用,只因其是《國風》之首篇,乃萬風之始,《詩經》中眾詩之靈魂。
《詩大序》不僅有自覺的構思、連貫的結構,而且是建立在系統綜合和變革創新之上。總體而言,《詩大序》完全符合后結構主義的文本概念,是真正用字詞、話語和段落精心編織而成的紡織品,其中有些來自作者的匠心,有些來自前人的文本,有些來自其他源泉。《詩大序》不是中國文學思想的任意拼貼,而是最后的寫定者(很可能是東漢的衛宏)在綜合了傳統材料以后重新構思組織而寫出的主題明確、首尾一致的文論,因而應被視為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由于它不僅重視詩歌的起源、性質、功能、評論等思想內容,也極其重視話語的意指和表征機制,因此也可視為雖十分簡略、但卻具有一定系統性的詩學,支撐其意指和表征功能的基本原則就是多維度的符號學和互文性撒播書寫。筆者的結論是:《詩大序》堪稱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后結構主義”詩論,其從傳統小學的注疏汲取源泉的創作方式與后結構主義的文本構思并無天壤之別。本文的分析研究不僅是為了給《詩大序》的價值正名,也可為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化提供一點啟發。
注釋[Notes]
①有關《詩大序》的來龍去脈,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的《詩序》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和清代崔述所著《讀風偶識》中的《通論詩序》篇(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
②本文中涉及《詩大序》的中文文字全部引自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冊,第63—64頁。引文原為繁體字,為統一起見,改為簡體字。文中的段落劃分,前幾段遵照原文次序,后半部為了便于分析,將長段分為數段。
③ 參見孔穎達:《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第272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thes,Roland.The Pleasure of the Text.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
蔡鐘翔等:《中國文學理論史》(5卷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
Cai,Zhongxiang,et al..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5 vols).Beijing: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87].
Chou,Tse-tsung.“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Wen-lin: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8.151-209.
崔述:《讀風偶識》,《崔東壁遺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
[Cui,Shu.Random Thoughts on Reading the Book of Songs.Writings of Cui Dongbi.Shanghai:Yadong Library,1936.]
Derrida,Jacques.Dissemination.Trans.Barbara John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Positions.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Writing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65.]
顧明棟:“周易明象與語言哲學及詮釋學”,《中山大學學報》4(2009):1—14。
[Gu,Mingdong.“Elucidation of Images in the Zhouyi and Language Philosophy/Hermeneutics.”Journal of Dr.Sun Yat-sen University 4(2009):1-14.]
Gu,Mingdong.“The Book of Changes as an Open Classic:A Semiotic Analysis of Its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Philosophy East&West55.2(2005):257-82.
Heidegger,Martin.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Harper-Row,1971.
Kristeva,Julia.Kristeva Reader.Ed.Toril Mo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Lu,Zongda,and Wang Ning.Philology and the Study of Philology.Taiyuan:Shanxi Education Press,1994.]
Owen,Steph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2.
《十三經注疏》(兩卷本),阮元校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Annotated Thirteen Classics(2 vols).Ed.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
蕭統編:《文選》。臺北:啟明書局,1950年。
[Xiao,Tong,ed.Selections of Refined Writings.Taipei:Qiming Book Company,1950.]
荀子:《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Xun,Zi.Annotated Writings of Xunzi Newly.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78.]
Van Zoeren,Stephen.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朱熹:“詩序辯”,《朱子遺書》。臺北:藝文出版社,1969年。
[Zhu,Xi.“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Great Preface to the Mao Edi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Writings of Zhu Xi.Taipei:Yiwen Publishing House,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