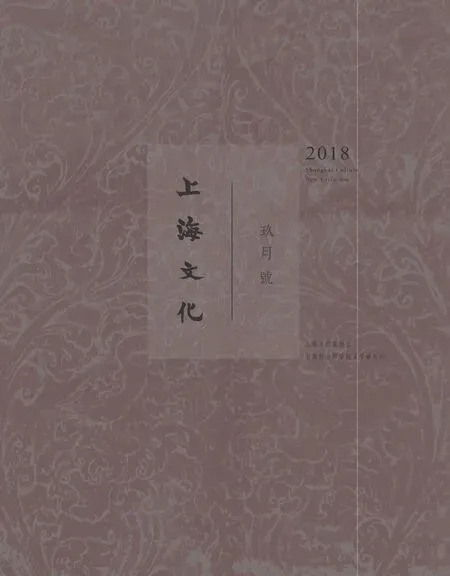糾纏不休的兩個人影像札記之四
康 赫
一旦進入暴力場景,他便是天才,一旦離開適合展示運動鏡頭的大場面,進入明星統治的兩人空間關系,他就是個平庸之輩
馬丁·斯克賽斯是一個典型的好萊塢電影體制下的分裂導演。他看清了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全部優勢與弊端,但并沒有像希區柯克那樣找到一條既可以避免與好萊塢體制對抗又能完好地貼上自己風格標簽的電影之路,他也不像霍華德·霍克斯那樣甘愿游走于各種類型電影,以求相對的自由創作空間,他只依托于一種類型電影,暴力電影。大部分時間里,他是個靠華麗的運動鏡頭和高密度旁白加歌劇片段來嘩眾取寵的花花公子,不過不時地,他也反叛。因而,他執導的電影是怪胎電影。一旦進入暴力場景,他便是天才,一旦離開適合展示運動鏡頭的大場面,進入明星統治的兩人空間關系,他就是個平庸之輩,只會讓人坐著或站著從頭至尾干巴巴地來回給正反打。他導演的《出租車司機》便是這樣一部怪里怪氣的電影。
一個出租車司機鼓足勇氣走進總統候選人拉票辦公室,去跟自己覬覦多時的漂亮姑娘說話,這是愛情。這樣的愛情是無法用一個滑軌加一長串規矩工整的正反打來傳遞給觀眾的。馬丁·斯克賽斯還加了一只俯拍的羅伯特·德尼羅的手,在女孩面前劃出一道弧線,很漂亮,但只是一個小花招,一個小裝飾。出租司機與眾不同的求愛只能以與眾不同的影像語言來表達,馬丁·斯克賽斯卻只有好萊塢三鏡頭法。接下去兩人在咖啡店見面,斜側相對而坐,一段更長更呆板的正反打。出租車司機與小雛妓那場快餐店的戲,還是兩人斜側相對而坐,還是一個正反打加另一個正反打。兩人從頭至尾都一動不動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這些戲看上去并不那么乏味。男女主角羅伯特·德尼羅和朱迪·福斯特演技出眾,女配角也非常善于以玉女色相挑逗觀眾。這也是好萊塢電影的長項,事實上就是電影票房長項。大部分觀眾只在乎故事和表演,根本不在意你的影像語言如何。于是,影像的表演完全讓渡于演員的表演,并有效地讓觀眾忽略了語言的貧乏。但貧乏是一種傳統,一種體制的傳統。因而生機,只能出現在體制無法插手的地方。最后那場槍戰,妓院走廊照度之低根本不夠好萊塢電影的最低標準,空間之小、運動之迅捷完全沒有給出華麗的運動鏡頭和像樣的正反打的余地,而這場戲分量之重又讓再蠻橫的電影公司也難以革舍,于是電影體制對影像的管制徹底退出,導演的天才得以淋漓盡至地展示。整場戲,哪怕只有一個羅伯特·德尼羅槍指妓院看守、在滿屋血腥中踩著小步舞緩緩退上樓梯口一個鏡頭,也足以驚世駭俗。
但這是一條死胡同。如果馬丁·斯克賽斯不愿死在死胡同里,他就必須投降。向魔法電影創始人梅里愛致敬的《雨果》便是一面投降的白旗。只有投降,他才能贏得大獎。
作為影像藝術,美國電影提前死亡,而歐洲人仍在繼續探索,繼續突破,直至1970年代結束。
1969年上映的《該詛咒的人》,維斯康蒂只用了兩個房間,三個角色,兩場戲,便說清楚了納粹時期整個德國社會的欲望運動、權力爭斗和資源掠奪的慘烈狀況。用小小的臥室戲來書寫大歷史,這才是大師該有的風范。
納粹需要錢需要鋼鐵,它必須鎖定這兩樣東西目前的擁有者,找出它的族群機體的致命弱點,不斷給予打擊,以瓦解其內部凝合力,同時從中選擇并培育出一名自己的代理人,為其注入能量,最終徹底侵吞其財富。如果它瞄準的正好是一個家族,便會在父女、情侶與母子之間制造出驚心動魄背叛與殺戮。
剛被謀害不久的鋼鐵大王的女兒索菲坐在臥榻上,面對鏡頭占據前景,房間深處,弗瑞奇坐在椅子上,同樣面對鏡頭。他在說話,對著索非的后背說話。索菲是鋼鐵大王的最大繼承人,但并不是唯一繼承人。她的肉體資源和她的鋼鐵資源一樣可觀,不過需要爭取。弗瑞奇應當通過占有她的肉體來占有她家族的姓氏,才能最終成為這個德國鋼鐵巨頭的大股東。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開場。兩人目標一致,但暫時,相距遙遠,索菲只給了自己的情人一個冷冰冰的后背。她需要從弗瑞奇那里看到一樣東西,野心。弗瑞奇表達了他對于目前自己處所的人際局勢的分析與判斷,家族中的納粹表親表示愿意站在他這一邊,并奉勸他及時把握住機會。弗瑞奇邊說邊起身向前,但并沒有走向索菲,而是走向了右側窗前,因為他還沒有展露索菲需要的野心。鏡頭很快追上他,給了他一個近景,與開始時給索菲的景別一樣。兩人目前處在同一平面,因而他現在是側著身子跟索菲說話。當他說出“機會”兩個字的時候,他那家野心家的面孔在光陰交替中趨近索菲。輕微的弦樂就在這時候響起。索菲再次出現在畫面中的時候已經斜倚臥榻,處于弗瑞奇下方。她還是不說話,但張著嘴。弗瑞奇沒有俯下身去,而是走到了臥榻另一側。“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嗎?”他笑問道。索菲露出笑容,主動但緩慢優雅地將手臂伸給弗瑞奇。后者握住這只手,坐到她身邊,吻它。來不及像好萊塢導演那樣給出索菲視角的雙人反打,弗瑞奇已經起身離開,他需要一個演說來宣告了自己的野心和信心:不是任何其他人,而是“我將發布命令,我將做出決定”,然后手指索菲強調聯盟意愿:“你和我,索菲。”他說完回到了自己最開始坐著的椅子的位置,背對著攝影機,也背對著索菲,并且站著。索菲這時迅速起身,走上前去,摟住他的雙肩親他。如果這場戲開頭的那個運動是正,男人面對鏡頭走向背對著他的女人,這個運動就是反,女人背對著鏡頭走向背對著她的男人。弗瑞奇向后伸出雙臂,摟住索菲的腰。“你要做出什么樣的決定?”索菲問道。弗瑞奇轉過身來。特寫接吻。一個標準的過肩正打,接一個同景別的過肩反打。“繼續繼續,沖到極巔。”女人急促地發出一串長長的指令來刺激男人。兩人緊緊相擁。再一次正反打,再一次展示兩人各自的正面與背面關系。身體與身體,欲望與野心完成交融。然后,在短暫的合的鏡頭之后,便到了女人表達自己的行動力的時刻,她離開男人,走到妝鏡前面。現在弗瑞奇再次對著索菲的后背,不過,這次多了一個索菲正面的鏡中映像。她轉過身來,抹著唇膏說出了對于兒子馬丁的判決:“把他當誘餌扔出去,這事我來處理。”鏡頭在她這驚人的表決中快速貼面她的臉,她將唇膏咬勻于緊閉的雙唇,露出殺機……
維斯康蒂擁有一種奇特的但丁式的融解力,讓他能從容不迫游走于普通人急欲掩面而過的視覺禁忌,又不至像帕索里尼那樣因過度渲染犯禁之樂而自身陷于迷狂
如果我們撇開影像,只是把兩個人當成兩個欲望球體來看,便很容易看清楚這場戲中的欲望運動的線條、離合關系及其建筑結構。與此相對應的是另一個房間的另一場兩人戲,成為這一欲望運動的反向運動,這一建筑結構的反向結構,或者說瓦解風暴:馬丁是家族的笑柄,索菲以為可以輕松搞定,但納粹看中的正是他滿身的怨恨:“你給了他一切,所有本屬于我的一切,我的工廠,我的錢,我的房子,一片接一片,甚至我的姓,還有你的愛。你是最壞的。”兒子馬丁聲淚俱下控訴自己的母親。納粹及時將馬丁收入麾下,成為自己的棋子,為他注入力量,去摧毀他母親,和附體于他母親的野心家。
從來沒有哪位導演敢于如此大膽直率地注視母子之間的黑暗空間。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毀滅之戰中,母子倆的主動與被動關系一次次反轉,直至馬丁邊脫光自己的衣服邊在納粹氣質的進行曲中宣告:“我要毀滅你,母親。”他撕下母親的衣服,實施亂倫。小納粹睡著了。索菲撫著他的腦袋,滿臉淚水。身邊這個怪胎是她的孩子,是她自己,也是她的時代。維斯康蒂在這一段落里比在上一段落采用了更多的正反打,但很少出現對稱結構,而是一次次用影像的失衡與顛覆緊隨母子間肉體與精神關系的一次次顛倒。在一些兩人臉部同處一個畫面的時刻,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母子之間的影像關系,而是戀人之間表達愛欲的影像關系。維斯康蒂比我們所能想象的大膽更加大膽,比我們所能想象的直接更加直接。當攝影機棄絕一切窺視欲,直接注視它面前的一切時,罪惡便離開它定義的狹小意義空間,還原為令人感慨萬千的奔騰不息的現象之流。
在這兩場戲里,攝影機反復動蕩于肉體與肉體,情欲、物欲與權欲的分合之間,讓每一個影像運動都攜帶著與之相應的欲望運動。因而,在現象之流之下,還流淌著一條隱喻之河。它不構成倫理解釋,而是構成另一種直觀,對不可見精神運動的直觀。
維斯康蒂擁有一種奇特的但丁式的融解力,讓他能從容不迫地游走于普通人急欲掩面而過的視覺禁忌,又不至像帕索里尼那樣因過度渲染犯禁之樂而自身陷于迷狂。1971年上映的《威尼斯之死》呈現的是愛與死、美與污的混合圖景。攝影機一樣直率地注視兩位主角,作曲家阿申巴赫和男孩塔齊奧,接受一切表面差異絕非冷漠的第三方旁觀:
海邊涼廊,長焦壓縮景深,將縱深的藍灰色廊柱壓成平面的林立木樁。紅色海魂背心少年塔齊奧看著作曲家阿申巴赫,如蝴蝶一般,在細長的木樁間輕盈旋轉。作曲家身不由己跟在后頭。當少年離去,作曲家不得不手扶廊柱才不至于跌倒在地。他需要喘息,需要休息,鏡頭從遠處邊跟搖邊推近這位體面盡失的中年男人,陪伴著他在一排海灘小屋后面趔趄前行,直到他靠上其中一間小屋,才跟著停下,耐心地等著他大口喘完氣,然后再度,緩緩推近他疲倦的身體。
霍亂流行的老巷深處,少年塔齊奧駐足,等作曲家現身。鏡頭越過霍亂時期煙霧迷漫的小巷,從遠處推近少年,一個叉腰而立的側身造型,接家人在街巷另一側喊叫少年的大全景,忽然,出人意料地切入少年向鏡頭緩緩轉動的臉部大特寫,舞臺頭像,致命的美。家人過來找少年,看到巷子深處作曲家倉皇閃退,心里明白了大致。
在清晨的海灘,用濃妝掩蓋病容的作曲家將要死去。他歪倒在躺椅上,目光追隨著與同伴在海灘上翻滾的少年塔齊奧,混合著染發劑的黑色汗液順著抹了厚厚一層白粉的面頰滑下。少年塔齊奧甩開同伴,悶悶不樂地走向大海,融入粼粼波光。作曲家雙臂垂掛,一口口咽著氣,黑色的汗液沖花了臉。遠處,少年緩緩往海里走,前景是一臺靜靜立在海灘上的照相機(維爾托夫傳統)。少年停下,向鏡頭轉過身來。昏然欲死的作曲家睜開眼睛,努力舉起腦袋,露出微笑。少年轉回身去,右手叉腰,伸直左臂緩緩抬高,指向大海與天空的連接處,用海神波塞冬的造型,為將死的作曲家做最后的表演。作曲家掙扎著挺起半個身體,伸出手去,試圖抓住逆光中少年細小的影子。少年繼續走向大海,作曲家猝然死去。攝影機凝視著少年的美,仿佛這致命的美吸干了作曲家的整個軀體,直至只留下一堆殘渣。攝影機也以同樣的熱忱凝視作曲家一點一點耗盡生命,走向丑陋的死亡。它全力維護著這愛情的均衡:他有多么奪目我就有多狂熱。
我們必須來說一說伯格曼。1953的《少女莫妮卡》中,伯格曼用兩個景別、運動、光影結構都幾乎完全一樣的面部特寫,確切地表達了歐洲導演難于啟齒的男人對于女人背叛的怨恨(除了戈達爾,不會有其他文明的歐洲導演會讓背叛的女人直接去撞車死掉)。這兩個鏡頭如果放在一起,就是嚴格意義上的正反打,情感傾向截然相反但影像地位完全對等。鏡頭從音樂歡快的娛樂空間中持續推近抽煙的女人,女人轉過頭來盯著攝影機,攝影機不急不慢,繼續推近她的臉,至特寫,四周漸漸暗下,只留下一張毫無表情的冷漠的臉。男人懷抱新生兒湊近街邊一面鏡子,低頭看著鏡中的孩子。鏡頭持續推近鏡中男人至特寫。男人覺察到自己存在,一個沉思的片刻,四周漸漸黑下,憂傷甜美的小提琴,一個突然覺醒的片刻。男人微微轉頭,注視自己的鏡像,一張漸漸疊入波光閃爍的大海的臉。這一正一反兩個鏡頭,中間隔了整整十二分鐘其他劇情。伯格曼的處理匪夷所思,卻令人叫絕:這是怨恨,男人對女人的怨恨,但經過特寫的轉移與舞臺化的抽離,經過漫長的十二分鐘世俗生活影像的稀釋,怨恨返回到怨恨的表面,成為一個無害的表象。
它全力維護著這愛情的均衡:他有多么奪目我就有多狂熱
1972年上映的《呼喊與細語》是伯格曼的杰作,電影走到這里已經無可超越,也無需超越。伯格曼在這部電影里處理了四人關系,三姐妹和保姆安娜。局部地,他沒有完全摒棄正反打,而是像維斯康蒂那樣,將正反打泛化為正反關系,并將其揉入更復雜精微的影像運動與聲音結構之中,使之不著痕跡。在這部電影里,兩人關系需要在四人關系中得到定義,而四人關系,除了借助與弦樂四重奏的對位關系來編織,又在總體上對位于更簡明的人聲正反關系——呼喊與細語。伯格曼融合正反打、蒙太奇、音樂對位、反射、隱喻、攝影機運動等電影史最重要的技術手段來幫助自己抵達影像直覺的極限。沒有正確的影像,唯有影像是正確的。《呼喊與細語》中的一切影像運動都不再有明確可界定的影像語法或電影法則。當愛森斯坦無法用他一貫的理性的方法論來說明他的剪輯階段的蒙太奇生產的奧秘的時候,他提出了“泛音”。這時候,這位理性主義者事實上已經走向神秘的直覺。那么在豐富嫻熟的影像技法之外,是什么讓《呼喊與細語》不同于所有其他電影,也不同于伯格曼自己的其他所有電影?組織《呼喊與細語》的神秘“泛音”是什么?是“凝視”,意大利人的“凝視”,羅西里尼、維斯康蒂和但丁的“凝視”。有“凝視”才會有“涌動”,有“涌動”才會有“波浪”,有“波浪”才會有詩,才會有人世內在的音樂性,才會有對位與反射,才會要求召喚最精妙的語言,讓影像以其自身內部動力說出它自己的話。
有“凝視”才會有“涌動”,有“涌動”才會有“波浪”,有“波浪”才會有詩,才會有人世內在的音樂性,才會有對位與反射,才會要求召喚最精妙的語言,讓影像以其自身內部動力說出它自己的話
《呼喊與細語》中有兩段影像,伯格曼處理得絕對,但是自由。
姐姐艾格尼斯已經過世。大姐卡琳的丈夫來了。夫妻倆已很久沒在一起。卡琳在吃飯時候故意打碎酒杯,并取走了一塊碎玻璃。
大特寫的手,將一片帶雙V口的玻璃片放入銀鏡盤內。鏡頭跟著手抬起至,特寫摘戒指。一個出人意料的近景,三頁妝鏡前兩個女人三個鏡像連成一排。仆人安娜靜立卡琳身后,注視著她的鏡中映像。卡琳抬起頭來,看到安娜在注視她。兩人通過鏡子長久對視。“不要看我。”卡琳命令道。鏡頭迅速反打,兩張女人的臉一前一后一實一虛。后面的安娜低下頭去。卡琳剛摘珍珠項鏈,安娜又在后面緩緩抬起頭來看著她。迅速扭轉的卡琳側面大特寫:“不要那樣看我,你聽到嗎?”突然飛速抬手,鏡頭同時飛速平移至挨了耳光后猛然弓起半身的安娜,并跟上驚恐中的她慢慢向墻邊退縮。卡琳更大的特寫的斜側臉,思量后抬眼:“對不起。”特寫反打墻前含淚的安娜,使勁搖了幾下頭。特寫正打卡琳,兩次欲言又止,然后加重了請求:“原諒我。”反打安娜更劇烈地搖頭后低下腦袋。正打卡琳特寫,思量,欲言又止,神色重新變得嚴肅:“給我解衣!”然后轉身向右去妝鏡。鏡頭跳軸,安娜從墻邊上前,向左前行,攝影機跟搖,卡琳特寫的臉入畫。兩個女人一主一仆,再次一前一后一實一虛,鏡頭稍做停留很快又出人意料地向縱深處推至后面仆人安娜的臉至特寫,安娜為卡琳解外衣。中景,另一個方位的妝鏡內外,再次五個人像連成一排,安娜繼續為主人解黑色晚餐禮服,然后白色內襯,然后白色內衣,直至裸體,腹部深深的刀痕,切至半身近景,又很快退回全景,一個靜止的長鏡頭:卡琳裸身坐到凳子上,開始變形的中年身體,腦袋上頂著一圈又高又圓的鬟盤。安娜收起所有衣服出畫,拿來睡衣入畫,站在卡琳前面,安靜地等她脫完絲襪,幫她穿上睡衣,再披一件睡袍。卡琳坐下,等安娜來解發。特寫,從安娜的臉下搖至卡琳的臉,稍頓,順著她的目光,沿她的手臂下搖并推近手,至大特寫,它輕輕撥動著銀鏡盤上的那塊帶雙V口的玻璃片。一個特寫的連續鏡頭,一根辮子和安娜編辮子的手,順著辮子搖向卡琳側臉,“你可以走了,”卡琳說著舉起手里的玻璃片,安娜從后景過,略停,鏡頭如同波浪輕輕拉開,給出兩人關系,待她出畫后又重新推近,卡琳拿手指試著玻璃鋒刃,并自語:“除了一堆謊言什么也不是……”稍后,她將把這塊碎玻璃片刺進自己的生殖器,偽裝生理期,以避免與丈夫做愛。
這段影像對話缺失,全景缺失。通常導演會選擇用中景最多近景處理的運動,伯格曼在特寫和大特寫中處理,因而,在聲畫的巨量空缺中,特寫的運動影像以空前的能量爆炸開來。
阿格尼斯就要下葬,家里的財產已分割完畢。大姐卡琳和小妹瑪麗亞仍受困于各自暗疾,彼此隔絕。卡琳在紅墻前發出大聲尖叫。小妹瑪麗亞也許無法忍受這瘆人叫聲,從自己房間沖向客廳,急欲逃離。卡琳叫住瑪麗亞。瑪麗亞止步,轉頭。后景是她們共用的紅色大客廳,一個充滿虛假交流氛圍的世俗場所,更遠處是阿格尼斯的房間,虛焦,但仍能看清門開著,白色的尸體躺在床上。鏡頭長時間注視這位生性淫蕩的妹妹,眼中掛著淚水,聽著姐姐畫外的訴說:“原諒我,也許你是對的,也許你只是想要更好地理解我。我親愛的瑪麗亞,原諒我,剛才我只是在胡言亂語。”瑪麗亞掉過頭去。卡琳必須把妹妹從世俗生活場景中,從阿格尼斯死亡的陰影中拉出來,拉回到自己身邊,于是繼續從外畫發出哀求:“不,那也不是真的。瑪麗亞,看著我。瑪麗亞,看著我。”卡琳說到這里才舉著雙手入畫,捧起了妹妹的臉。瑪麗亞也哭著撫摸了姐姐的臉。巴赫的弦樂作為牽引的動機提前進入。卡琳摟著妹妹的雙肩將她從客廳牽引到她剛才獨自尖叫的紅墻前坐下。巴赫的弦樂突起為前景,姐妹對話的語音退化為背景的喃喃細語。一個非同尋常的對著充滿整個畫面的兩人側面特寫的往返平移,波浪一般來回輕撫著這兩張受痛苦煎熬的面孔。姐妹倆在這舒緩的弦樂與影像的波浪中露出笑容,不停地互相訴說,親吻。鏡頭退回近景,姐妹倆仍在彼此撫摸披此訴說。切回瑪麗亞的斜側面特寫,帶著姐姐卡琳的小半個側臉,一個有歐洲繪畫傳統熏陶的電影導演才會給出的畫面。繼續無聲訴說,繼續彼此撫摸。接著一個反打,姐姐卡琳的斜側面,前景帶著瑪麗亞的小半個側臉。繼續無聲訴說,繼續彼此撫摸。然后再次,像開頭那樣,對著充滿整個畫面的兩人側面特寫往返平移。姐妹和解,鏡頭抬高,從一片紅墻融入三姐妹的精神寄托,保姆安娜的臉部特寫……影像糾纏著影像,影像推動著影像,影像融解著影像。電影在這里走到了自己的極限,語言的,詩性的。
1970年代之后,除了伯格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幾位巨匠偶爾有佳作問世,電影世界不再生產新的影像語言,但好萊塢的說服力卻一如既往,在影響整個世界的電影形態,包括不由好萊塢發明卻由好萊塢命名的“好萊塢三鏡頭法”。到這時候,好萊塢三鏡頭法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影像句法問題,它是關于平等與民主的最新表達習俗影響下的句法(事實如何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們或許還遠沒有創造出民主社會,但至少已經創造出了話語中的民主社會),是經長久培育成熟并固化的好萊塢電影明星制度束縛下的句法,也是電影工業權力傾軋和各方權利平衡的逼迫下的被動句法。今天,好萊塢三鏡頭法幾乎成了全世界導演的拍攝本能,甚至包括像文德斯這樣通常被認為樂于標新立異的導演。
那個世界不只有他一人了解愛情來臨之迅捷,但也許只有這位老人知道如何以影像之傾斜追上愛情之迅捷
1995年,安東尼奧尼拍攝以他的短篇小說為故事底本的《云上的日子》。因為中風不能說話,一直視他為偶像的文德斯成為執行導演。文德斯為此寫了日記,像個小姑娘一樣訴說自己期間遭受的種種委屈。天才之火必然要清算平庸。安東尼奧尼一次次否決他的提議,要把他的痕跡從自己的影像世界中清除出去。
該片的第一部分在安東尼奧尼的家鄉費拉拉拍攝。薄霧中,一條長長的券門走廊,透過券門能看到外側的細石子路。女主角從長廊深處騎車過來,男主角從左側石子路開車過來。他們要因為問路而相遇,并立刻相愛。文德斯發現安東尼奧尼只給女主角特寫,沒給男主角相應的特寫。按三鏡頭法原則(盡管文德斯沒這么說,但只有這個原則能支持他之后的建議)這里缺兩個給男孩的反打,一個越肩近景,一個特寫。由于給男孩的近景反打可以由,給女孩的越肩近景正打中男孩轉頭的側臉勉強替代,文德斯就建議安東尼奧尼補一個男主角的特寫反打。盡管說不了話,安東尼奧尼以手勢和不耐煩的表情生硬地拒絕了他的建議。文德斯找安東尼奧尼助手去勸說老人,可以先補上這個鏡頭,后期如果安東尼奧尼覺得不需要,可以不剪進去。老人以同樣的方式再次拒絕。文德斯事后怪老人眼里只有女人,沒有男人。這一年安東尼奧尼八十三歲,那個世界不只有他一人了解愛情來臨之迅捷,但也許只有這位老人知道如何以影像之傾斜追上愛情之迅捷。女孩注視男孩的特寫已經發出信號,必須電光火石間木已成舟,再給一個男孩接受這信號的反打特寫只能說明這不是愛情,只是對等交易。影像的交易自然也會反射為情感的交易。安東尼奧尼非常清楚,沒有雙方在這里的影像上的失衡,之后兩人在旅店餐廳再次相遇時,男孩屈身仰面欲吻的動作就會變得輕浮,變成一個蓄意之舉,而不再會是它現在的動人面目。安東尼奧尼必須讓男孩蒙受的影像的缺失變成觀眾觀感的缺失,讓他們暗中為男孩不平,并對他充滿期待。唯有如此,男孩那個屈身欲吻的動作才會變成一波不由自主的潮汐運動,仿佛女孩剛才在長廊盡頭那特寫的一瞥仍在他心里引起一陣陣震顫。
人物空間的正反糾纏是物理糾纏也是精神糾纏。在影像世界里,人與人并非從一開始就如此糾纏,但無疑將一直糾纏下去,并不斷演化其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