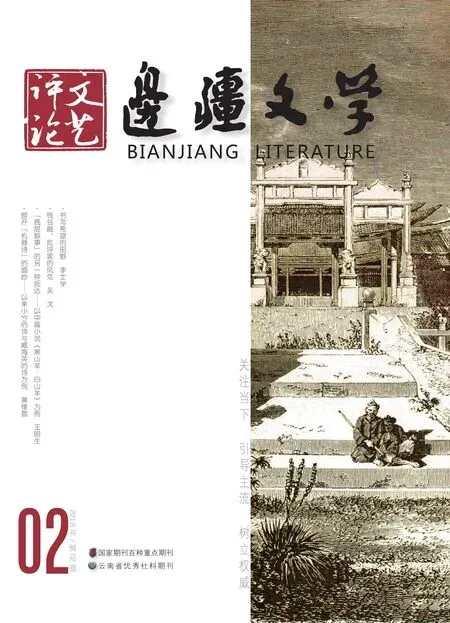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chuàng)作出真正接地氣的現實主義佳作
胡性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chuàng)造。我以為,這應該是廣大的文學工作者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行動指南。早在2015年,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就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2017年5月,根據錢小芊書記在中國作協九次代表大會提出的:要把加強對基層作協工作的指導和服務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加強對基層作協工作的支持的精神,我到了云南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昭通市掛職任文聯副主席,對總書記提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深入生活,在生活中汲取創(chuàng)作的源泉,這一創(chuàng)作的鐵律,我在掛職前的認識是模糊的,總認為自己本身就在生活之中,每一天無時無刻不在生活著。掛職以后我才認識到,我雖然置身于生活中,但并沒有真正抵達生活的“終端”,深入生活的“深入”,就是一個要無限度靠近生活終端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作為人民的一員,感受生活本身所蘊藏的內在動力,接好地氣,從而獲得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造力。
在昭通掛職期間,我對昭通和重慶奉節(jié)的入殮師的生活進行了深入了解,這是一個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很少涉及到的群體。尤其是在奉節(jié)的采訪,感觸很深。一開始,我是抱著好奇的心理去了解收尸人生活的,我總覺得他們干那一行,一定會經歷過不少靈異事件。可到了奉節(jié),真正走近那些陰陽兩地的擺渡者,才發(fā)現沒有一個人經歷過。后來我想,真要是有人經歷了難以解釋的靈異事件,那收殮尸體的這個工作,可能做起來就有心理障礙了。談到從事這一行業(yè)有沒有被嚇到,團隊的劉老大講了這么一個故事:他們的工作室就設在醫(yī)院的太平間,里面的冰棺中冷凍著一些尸體,主要是官司未了的。一天夜里,值班的邱二接到劉老大打來的電話,要他送幾百塊錢到殯儀館去,劉老大在那兒打麻將輸錢了。邱二把錢送去以后,返回醫(yī)院太平間時,月亮懸于高天,很明亮。他就在太平間外坐了一會兒。可是,他突然聽到屋子里面有人叫稍息、立正,這讓邱二感到很狐疑。他又坐了一會,進了太平間,發(fā)現有一具尸體靠在墻上,他先是懷疑有人來偷尸體,就走過去,心里有些發(fā)毛。正當他經過一具冰棺時,突然里面?zhèn)鱽硪粋€聲音:太冷嘍,加床被子嘛,邱二一聽,頭皮一炸,返身就走,沒想到腳下絆到墻上連接到冰棺的電線,那具站著的尸體倒了下來,就向撲向邱二一樣。邱二嚇得從太平間里逃出來,問題是冰棺里的那人跳了出來,追著邱二喊:太冷了,加床被子嘛!把個邱二嚇得魂飛魄散。逃到廣場,身后的僵尸被聯防隊員攔住,他還在委屈地喊,加床被子嘛,太冷嘍。原來是醫(yī)院附近的精神病院,有一患者在邱二送錢給劉老大時跑了出來,看到太平間的燈光,就趕了過來,把冰棺里的尸體搬出,自己躺了進去,很冷,就讓加一床被子,這下可把邱二嚇得不輕。
剛見到劉老大的時候,印象很深。從事了幾十年的收尸工作,他在奉節(jié)實在太有名,許多人家嚇唬不聽話的小孩,說的都是“劉老大來了!”許多熟人碰到劉老大,都是繞道走。我還記得,見面的那天上午,當我伸手出去與劉老大握手時,他遲疑了,慌忙把手在褲縫那兒擦了擦,才伸出來。握住他手的那一瞬間,我能從他手上傳遞出來的力度上,感覺到他的信任與輕微的感激。作為那座縣城家喻戶曉的收尸人,人們對他敬而遠之,以至于他都快忘記,握手是中國人最常見的禮節(jié)。之后,他把我當成了朋友,在奉節(jié)時,他每天都打電話來,要請我們去吃火鍋。直到現在,他還會偶爾打個電話來問候。
劉老大的團隊一共十人,好幾個都是刑釋人員,可每一單活計做完,入殮師都會把收到的錢如數上交,劉老大私下查證過多次,從來沒有人隱瞞。另外,業(yè)務有難易、有遠近,從來沒有人講價還價。我想,一定是每天與尸體打交道,看透了生死,方才這樣不計較,超脫。
小說的主人公劉老大曾有過三次婚姻,前兩任都是因為他從事的職業(yè),離開了他。第三任是個盲人,據說能做一手不錯的菜,與劉老大相依為命,感情不錯,劉老大還把她的名字紋在了身上。在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發(fā)現那些收尸人,如果不是在那個特殊的環(huán)境里見到,你不會相信他們從事的是收殮尸體的工作,因為從外表看上去,他們長得慈眉善目,一臉福相。我猜是從事入殮工作之后,因為悲憫而漸漸讓他們原本堅硬的面孔,變得越來越柔軟。有個小細節(jié)可以說一下,劉老大每天的工作,是查房。許多患者,彌留之際,希望落氣在家中,這樣就需要他們用車護送回去。如果送回去活著的話,他們就收680元,如果患者在車上落了氣,就要收1380元。有時,患者的家屬為了省幾百塊錢,明知患者已落氣,卻不告之,還裝作與患者交流,他們也不揭穿。
在昭通和奉節(jié)兩地對入殮師進行采訪后,我創(chuàng)作了中篇小說《生死課》,發(fā)在今年《十月》雜志第五期的頭條。在小說中,我在結尾虛構劉老大患上了絕癥,為了讓自己的盲妻能夠看到這個世界,他把眼角膜給捐了。繼而他擔心到另外那個世界成為盲人,干脆把自己的整個肉身都捐給了華西醫(yī)科大學作解剖用,一個曾經把無數亡靈送到彼岸的擺渡者,為了盲妻,最終成為一個沒有歸途的人。
個人短短的掛職經歷,讓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性。但云南作協是小作協,人員少,工作量大,而云南的一線作家,大多在文聯系統內,很難抽出時間深入到生活的一線。建議將無編制無經費的云南省文學院,辦成作家流動站。有創(chuàng)作計劃并經認證的作家,可進入流動站,三年一個周期,從而保證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和創(chuàng)作的時間。創(chuàng)作周期結束以后,可以回到原崗位工作,也可根據創(chuàng)作實際再次申請進入作家流動站,用這種方式來解決云南沒有專業(yè)作家編制的困境。如果省文聯成立文學院作家流動站,各州市也成立類似的作家流動站,那就能保證一些有創(chuàng)作計劃并經認證的作家,有時間抵達生活的終端,創(chuàng)作出真正接地氣的優(yōu)秀的現實主義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