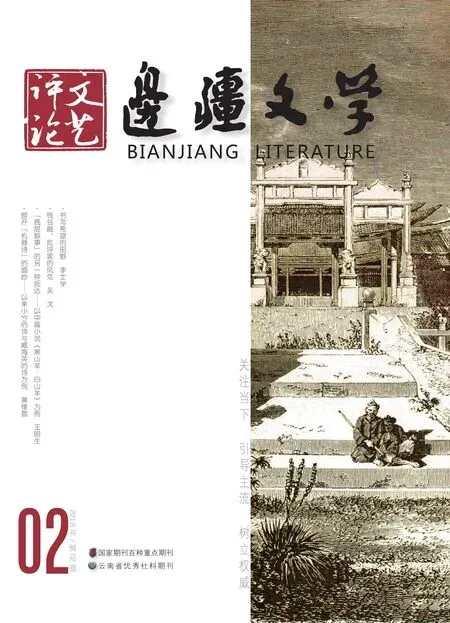異域、存在與先鋒
——論段愛松的中短篇小說
唐詩奇
在云南作家中,段愛松是一個異數。他既不偏重于“邊地與民族”的書寫,也不虛化地域,專注于發現“城市與現代”,而是把二者結合起來,以鮮明的文學地理學的理念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文學王國,致力于在云南這一“異域之境”中寫出“不一樣的小說”。毫無疑問,段愛松是先鋒的。他深知一個真正的先鋒作家,不僅僅應當成為一個技術先鋒,更重要的成為存在的先鋒或精神的先鋒。一方面,他承接著先鋒寫作形式主義的探索,在文本中重新召喚敘事與語言,把“文字煉金術”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他又在廣闊的時空中追問存在,在尋找“自我歷史”的起源中,向形而上的層面進行開掘,拓展了小說的精神版圖。在當今以故事、趣味、經驗為主的文本的重重包圍中,段愛松開辟出一條回歸文學自性的道路。
一
段愛松是一個造夢者,讀他的小說如臨夢境。他曾經說過,“世界上最好的一首詩歌,就是一所絕世獨立的房子;而最好的一部小說,則是一座宏偉壯闊的宮殿。”作為一個跨界寫作者,他攜帶著詩歌浪漫、瑰麗、綿長的基因,為他的小說宮殿添磚加瓦、雕梁畫棟。在這座年久歲長的宮殿里,因在底下黑暗漫長的時光而顯得陰暗、古質、繁復,在時間世界的神秘力量的指引下,段愛松以鮮明的文學地理學概念,用時間的秘匙打開了時光之門,締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學王國。
段愛松的神話王國位于昆明西南部的一個縣,環繞滇池,延伸入海的棧道襯著云貴高原湛藍的天空,被人們戲稱為“小馬爾代夫”。這是史前古滇國文明的遺址所在,也因盛產磷礦而聞名,現在是昆明主要高新技術開發區與生產區。這是段愛松的家鄉,他生于斯,長于斯,耳濡目染的都是那些神奇詭秘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這個既古老又現代的小城讓他充滿無限追念與想象,成為他筆下源源不絕的靈感源泉。他以自己的故鄉晉寧為據點,打通時空界限,把史前古滇國文明與當代社會連接起來,構建出“晉虛城”的文學概念。在云南,確實很少有作家像他這樣擁有明確地對城市有文學地理學的概念,并如此堅定地付諸實踐。在段愛松那里,時間的秩序就是心的秩序。隨著前世戰爭片段的不斷閃現,人物的身份之謎逐漸浮出水面。
段愛松在小說中不止一次提示我們古滇國與我們當代的關聯——“作為某一歷史時期的中心,盡管古滇國泯滅,卻必然會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得以輪回。”在文學晉虛城中,人物皆為古滇國亡靈在當代的重新復活,這是一種“定勢的命運”,每一個人無法擺脫,亦無從改變。我們很容易注意到,段愛松筆下的人物都是天賦異稟,卻又因與生俱來的殘缺與社會格格不入。在這些短篇系列中,小說之間的互文性讓我們知曉人物的身份與關聯,“我”是古滇王國曾經的統治者;把一是我出生入死、并肩作戰的好兄弟,也是我最忠誠的仆人;小滴曾是古滇國的將領,英勇無畏,為保衛家國戰死沙場;老飛曾是古滇國的著名樂師,在音符中創造生命的奇跡;背果是曾經背叛過族群的罪人,今生的殘疾是為他曾犯下的背叛之罪的深度救贖;巫奈是曾經背叛過族群的陰師,而這種背叛也“無聲無息地落在了他現世的身上”,他最終被半人半狗的詛咒所懲罰。當我們把幾個文本放置在一起時就會發現,背叛過“我”的人在今生將面臨因果報應的懲罰,而他們唯有在這種懲罰中才能得到救贖,其命運終將在“非凡與丑陋的怪異結合中繼續前進”。這種宿命論或者說輪回觀念在段愛松的小說中無處不在地主宰著人物的命運,讓小說自始至終都彌漫著一種神秘、鬼魅、驚心動魄的懸疑氛圍。
值得注意的是,前世如此輝煌顯赫的戰爭記憶,到了今生,卻變得卑微、輕飄、雞毛蒜皮。從前世到今生,關乎家國生死的戰爭背景變成了平凡的縣城街頭,國家的統治者、將領、巫師、樂師皆變為無所事事的街頭少年:把一憑借著超人的天賦進行賭博,成為戰無不勝的賭王;曾為保衛家國戰死沙場的小滴,今生卻變得膽小、瘦弱,利用自己的靈敏身型優勢去糕點廠偷盜;宮廷的靈魂樂師老飛卻在倒賣車票、監控室和炸洋芋中消耗著自己的生命……段愛松用這樣的巨大反差似乎意在說明:一個宏大敘事的時代已經消亡,而在當今時代只剩下“一地雞毛”。晉虛城,實際上成為個體在當代社會中難以尋求身份認同,而通過歷史途經尋求寄托的精神家園,這個烏托邦不僅僅是個體的避難所,段愛松還意圖把其構造成一個民族文化史詩性的寓言。在千百年浩渺的時空之中,古滇國與當代社會形成了一種隱性的對話,可以看出其構建當代民族文化寓言的野心。
二
段愛松所汲取靈感的古滇國,除了在博物館中展示的青銅貯貝器等出土文物,甚至鮮有文字記載,實際上更像出于作者的一種想象。所以當段愛松對于“文化記憶”或者說“自我歷史”進行尋根之時,這種尋根并非建立于民族集體無意識之上(因為民眾對古滇國的認同非常有限,這種歷史文化對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潛意識并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而是個人化、私密化的個人體驗的集合。所以,段愛松對“晉虛城”的建構與對“我”的自我身份的探尋,與其說是尋根,不如說是對“自我歷史”的重新建構。因為他所要尋找的并非廣義上的民族之根,而是自我之源。
“自我”是這些小說中不斷重復著的主題。尋找生命本體的真相,這個千百年來被無數人思考過的哲學命題被段愛松再次提起——“現在的我,究竟是誰?”段愛松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之中,更衍生出了一套時間哲學,在時間世界里,晉虛城古今相通,只要掌握“時間的密匙”就能打通時空,尋找到生命的本源。段愛松不斷追問,敘述者“我”不斷從他身邊的每一個人身上尋找前世的印記,從宗教的普世關照中尋找身份之謎。然而“我”永遠無法找到存在的真相,正如“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預知的晉虛城”與“遙遠時期突然莫名消失的古滇王國”,“不可預知”與“莫名消失”直接指向了存在的虛無。段愛松在《罪贖》的結尾處寫道:“我在自己即將劈裂的身份中,并沒有忘記我在尋找的真相。我突然有了某種大悲苦,不是源于自己此刻承受的罪過,而是因為那些我苦苦尋找的東西。”這個“大悲苦”即來自于虛無,所有的追問在死亡的瞬間都回到了原點。他本想在宗教中獲得救贖,但無論是清真寺的誦經聲,基督教堂的贊美詩,還是盤龍寺的晚鐘聲都無法讓“我”尋找到存在的真相,三個宗教的混亂交織,正體現出了當代人的無信仰狀態,或許這即是罪的根源所在。
在這套時間哲學的背后,實際上是一個當代社會中個體的身份建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段愛松的小說中,“父親”形象是缺失的。父親形象在我們傳統文化中一直被看作“父權”的象征,自五四以來,對“父親”的反抗在一定意義上被視為對“傳統”、“權利”“制度”“權威”的宣戰與摧毀。在先鋒傳統中,也一度以“遺忘父親”為敘事的先決條件。而段愛松的小說中卻充斥著“無父的焦慮”, 《小滴》中的小滴和《西門旅社》中的店主都在等待父親的歸來,小說人物等待尋找父親的過程,其實也是對自我斷裂的歷史、對自我起源的一種尋找。與尋根文學那一批作家不同,70后出生的段愛松無法實現自我歷史與現實的高度統一,只能在想象的歷史中去尋找“自我歷史”。然而,無論是對父親的等待還是追尋,都是徒勞,這種徒勞的等待讓人想到等待戈多到來的兩個流浪漢,不同的是,段愛松小說中的等待因有明確目的性——追尋“自我歷史”的可能——而被賦予了等待的意義與力量。
“和幾千年前的大戰不同,這次我的敵人,并不在我們之外,也不在我們之中,而在于我,在我逐漸被某個自己牢牢掌控的過程中,深感命運的沉重。就像那次和小劍在巫奈家灶房里,遇著巫奈奶奶的小腳和繡花鞋,兀自離地懸在半空中。遠遠看去,是那么漂亮,湊到跟前,卻一無所依。”(《巫奈》)這段話可以代表段愛松小說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尋找自我的旅途中,自我的敵人恰恰是自我的存在。這成為一個悖論,在經歷漫長的等待和追尋之后,最終還是指向了虛無。
在這個現實社會失范、意識形態消解、精神世界失落的時代,段愛松把形式主義策略當作與現實對話的唯一途徑。通過這種方式,他一方面向歷史的縱深挺進,一方面又向形而上的存在進行追問,試圖通過這種美學實踐完成個體在當代社會的“自我救贖”。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尋找,盡管他一無所獲。正如與魔鬼締約卻得到救贖的浮士德一樣,重要的不是所謂的“真相”,追尋本身已經獲得了超越時間世界的力量。這或許就是段愛松悲劇精神的所在。
三
毫無疑問,段愛松是先鋒的。正如安徽年度文學獎給予段愛松的授獎詞中所說,“詩意的構思與非線性的敘事依然堅持和捍衛著先鋒寫作形式上的榮譽”。敘事和語言在段愛松這里被重新重視起來,多角度敘事則成為其形式主義探索下最基本的敘事結構。無論是《罪贖》中以亡靈的身體器官的視角分別敘事,還是《葬歌》《通靈街》以眾多的家人視角敘事,或者是《西門旅社》以店主與小艮的視角交替敘事,這種敘事都分別以自身立場不斷補充和再現故事的細節與真相,把一個故事不斷拆分,再由讀者進行重新整合。這種有意加大敘事難度的文學實踐,讓文本在敘事中重獲新生。
其次,段愛松跨界寫作的嘗試,讓語言獲得了解放。這種敘述語言的功能不僅僅在于講述或者抒情,而在于營造一種意境或氛圍,因而常常會造成文本之間的某種“斷裂”。那些古老神話傳說的講述、血腥與暴力的渲染、無邊無際的想象與回憶,其實與故事進程并無事實上的關聯,而是作為一種“言語的烏托邦”,成為個人言說欲望的表達。段愛松通過敘述語言的變換與堆砌,以非凡的想象力構建幽暗、古遠、神秘的異域之境,進一步帶來感官與感情的解放,重獲一種詩性小說的審美體驗。所以,在閱讀段愛松小說的時候,要求讀者對固有的被簡化或被“養成”的思維模式進行轉換,才能獲得打開段愛松小說藝術空間的密匙。
當我們在確認段愛松的先鋒性之后,或許隨即會產生這樣的質疑:這種形式主義的探索早在20世紀80年代“那個叫馬原的漢人”那里就已經登峰造極,段愛松的先鋒寫作究竟意義何在?我想說的是,段愛松的“先鋒”不僅于此。在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浪潮沉寂之后,陳曉明發出“文學頹敗”的斷言。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文學死亡”“先鋒消亡”“理想主義的終結”之類的聲音不絕于耳,正如謝有順所擔憂的那樣:一方面,對存在的追問、人性的深刻剖析、人的處境的深切體察以及虛無對人精神的戕害等在文學中長久缺席。另一方面,“講故事”文本大行其道,敘述和語言退場。這個時代更加青睞那些善于講故事的人,而非專注于怎樣敘事的人。在這一片眾聲喧嘩之中,每年數以千計的長篇小說得以出版,故事的版圖在極具擴張。然而看似文學繁榮的背后,實質上空空如也。先鋒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實驗性的語言游戲和敘事迷宮,而更應該注重先鋒所體現的核心精神——反抗和自由。無論是反抗體制或意識形態,還是反抗舊的藝術傳統,先鋒精神在于自由地展示自我審美理想,表達對人類存在困境的思考和詰問。從本質上來說,一切精神上與創造性、反叛性、實驗性、前瞻性相關的寫作都可以歸入先鋒主義的范疇。
在先鋒沉寂后,段愛松仍然堅持先鋒寫作,可以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先鋒派之所以受到質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過于重視形式主義的探索,而忽略了精神層面的開掘。但段愛松的小說實踐不僅保持了先鋒寫作的“形式上的榮譽”,更拓展了先鋒敘事的精神圖景,對“自我歷史”的追問與“自我救贖”的尋找使得小說具有形而上的張力。這種探索曾在張承志那里出現過,段愛松的追問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段愛松這一代個體的“心靈史”。所以當我們在談論段愛松的先鋒性的時候,不能僅僅從他的形式主義探索入手,而更應當關注段愛松站在時代前列時對人的存在、人性以及對歷史發展衍生出來的虛無的關注和承擔,并在作品中形成的獨立話語空間來承載這種非凡的藝術感知能力。如果說80年代的敘事革命是為了消解文本意識形態話語的話,那么段愛松先鋒的再出發,則是為了對日常和經驗敘事所帶來的庸常的反抗,對關乎存在與精神的那種充滿力量的小說的重現。
段愛松的小說令人驚喜,但后現代語境下的先鋒寫作仍然面臨著“無邊的挑戰”。如何在晉虛城的與當代社會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而不至于陷入固有的敘事套路?如何在歷史關照下更有效地切入當代經驗,反映當代個體的生存困境?如何在存在的虛無中重建“自我歷史”,探尋生命的來路與歸途?有效解決這些困境將成為段愛松小說能否走得更遠的前提。無論如何,段愛松的小說讓我看到文學回歸自性的希望,他的創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