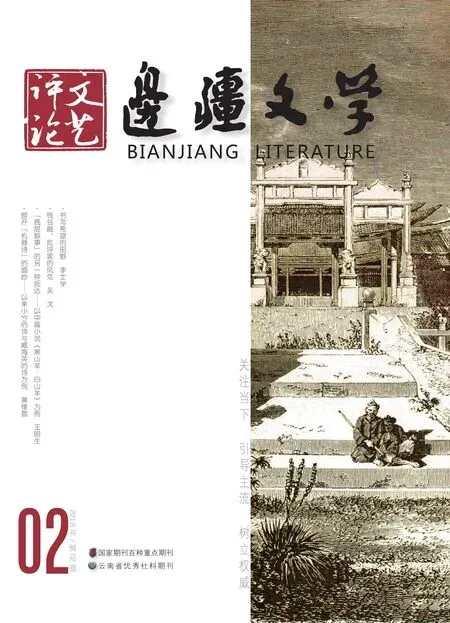異域之境下的先鋒文學
——評段愛松小說
趙靖宏
昆明作家段愛松以詩歌寫作步入文壇,十一歲時就開始發表詩作,現已出版詩集《巫辭》《弦上月光》《在漫長的旅途中》,其才華有目共睹。生活中的段愛松是一個多面手,除了詩歌,他還涉獵書法、音樂,擅長吉他彈唱,博客里自稱 “抱著吉他唱唱詩”,雖素未謀面,但其灑脫、隨性的詩人氣質可見一斑。近年來段愛松“跨界”到小說領域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他的小說以詩化的寫作,先鋒的姿態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他以史前古滇國為背景,建構了一個神秘、巫邪的小說世界。他的小說作品數量雖不多,但極具個人特色,像是一朵奇葩在秘境中開放。
一、異域之境:古滇國、晉虛城
兩千多年前,段愛松的故鄉昆明晉寧曾出現過盛極一時又突然消失的古滇國,它真實存在于歷史中,如果不是青銅器的偶然發現,古滇國以及這段燦爛的古代文明或許還將長埋地底。無疑,青銅是開啟這段塵封歷史的一把鑰匙。古滇國的命運與青銅及其冶煉術休戚相關,古老的冶煉術在段愛松的小說里被賦予了神秘色彩與巫邪之氣,正如他在《青銅魘》里的敘述“銅族和林木,經過古滇冶煉術鑄造融合之后,上升的部分,成為青銅器。它記載了巫術之源解析下,古滇大地的生息繁衍;下降的部分,則是毫不起眼的灰燼,它是巫術之源被省略的部分,也是古滇大地生息繁衍中,保持不變的、一種被遺棄的定勢”。在段愛松小說里,除了兩千多年前這個真實的古滇國,還有一個史前時期虛幻的古滇國,段愛松將其稱為“夢中常常出現的更遠的故鄉”,他通過文字探尋古滇國的秘密,他穿梭于真實與虛幻,歷史與當下,在夢境與現實中尋蹤覓跡這“更遠的故鄉”。在命運的定勢下,古滇國何等的輝煌終究在時間的齒輪下磨剩一些蛛絲馬跡,那人類以及滄海一粟的個體的命運又當如何?
神秘的古滇國深埋于段愛松的故鄉晉城鎮的土地下,這段久遠的歷史遺跡給段愛松的故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他從小就聽老人們講述關于小城的種種神奇傳說, 耳濡目染之下難免對故土心存敬畏。當段愛松開始寫小說時,他便在他的一系列小說里構建了“晉虛城”。顧名思義,“晉虛城”的原型晉城鎮,但又不是現實中的晉城,“虛”暗示著這個城的虛幻,是他小說里構建的另一個故鄉。小說《罪贖》里穿插了晉虛城上空一直躲著古滇神獸之首“蓋莽”的傳說以及小男孩下睫毛變成的花妖貓屙的屎會變成青銅扣飾,小孩子的屁變成邪惡的毒物的故事;《巫奈》中敘述了巫奈奶奶的小腳和繡花鞋離地懸空,巫奈在某個風雨之夜變成一只野狗,諸如此類晦暗詭異之事在段愛松小說世界里的“巫邪之城”成為一種常態。
正如“約克納帕塔法縣”之于威廉·福克納,“阿拉卡塔爾小鎮”之于加西亞·馬爾克斯,“山東高密”之于莫言,段愛松的小說均發生在他虛構的“晉虛城”里,“晉虛城”是他小說創作的根脈。因為植根于具有民族和鄉土特色的高密東北鄉,莫言成為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不是拙劣的馬爾克斯模仿者,莫言曾經幽默的談到是童年的饑餓經歷激發了他無限的想象力,而段愛松的想象力則是來自于云南獨特的風土人文,這片相對封閉、有著多元文化又神秘的土地,孕育出他小說里那魔幻和詭異的故事,他依托于這異域之境,將遠古的古滇國與巫邪的晉虛城寫得魔幻無比。對云南作家而言,強行追隨外界的寫作趨勢并非明智之舉,因而大多數云南作家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更愿意寫自己熟悉的故鄉,比如藏族作家永基卓瑪,德昂族詩人艾傈木諾,傣族作家禾素。但段愛松又與之有不同之處,他不是單純地寫對故鄉的深情,在他文字的煉金術下,故鄉的每一寸土地,石寨上的地下宮殿、南玄村、上西街等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他的小說明顯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形成一種既本土,又現代的文學風格,這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更多的解讀層次。
二、敘事和藝術的探索
段愛松說: “有自己獨到的異域之境,就應該寫出不一樣的小說” 。只要讀過他的小說,都能明顯感覺到他寫小說并非傳統的寫作方式,習慣于傳統閱讀思維的讀者可以說是很難理解他的小說。不過,寫作本就不該循規蹈矩,寫作應該是頑皮的,就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你讓他往東,他偏往西,你讓他往左,他偏往右,如此一來,才能別具一格,千篇一律的寫法很難讓有“野心”的作家產生寫作的快感。
20世紀80年代,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問世,很多中國作家驚訝地發現,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與此同時,中國文壇也出現了充滿實驗性、超現實主義、帶有荒誕色彩的先鋒文學,先鋒作家們以語言到形式的狂歡刺激了文壇。80年代的先鋒文學已經留在了文學史上,而以敘事革命為軸心,徹底顛覆既有文學傳統的先鋒文學及其精神卻沒有間斷,這才是80年代先鋒文學最大的貢獻。先鋒,是一種精神,它不是要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而是保持作家創作的獨立性和探索力,為文學創作提供多種可能性。段愛松的小說是先鋒的,他不斷進行著小說寫作實踐,他不是那種以故事情節吸引人的小說家,他熱衷于敘事策略的探索,在他為數不多的小說里,你實驗著盡可能多的敘事方式。
段愛松善于通過多種敘述視角來寫小說,中篇小說《西門旅社》里從“店主”和“小艮”兩個主人公的視角交替敘述,就像一個人在和自己的影子對話;《青銅魘》以“巫術之源”提問,“青銅器”的“巫術”回答的形式構成小說里的重要篇幅;《通靈街》更是將敘述視角的多面性發揮到淋漓盡致,通過死者的兒子、兄弟、老母親、老父親、奶奶、前妻、姐姐、嫂子、朋友的視角,從不同的側面還原死者的原貌,而對于死者的死因,依然是謎一般的存在;《罪贖》也是從多個視角敘述殺人案,但卻采用了非人的視角,將敘述的話語權交給被兇手殘忍肢解的器官:腦、眼、耳、鼻、足、血、經、骨和影子,這實為非常大膽的寫法。因而,讀段愛松的小說,你會發現他的故事呈現出一種撲朔迷離的狀態,他無意于編一個完整的故事給讀者,他也不熱衷于把故事寫得高潮迭起,引人入勝,他更看重的是敘事的策略,通過形式的創新營造一個迷宮,這個迷宮充斥著各種幻覺、夢境、死亡、巫術,他以文字為通道,讓讀者自行解讀小說文字背后的秘密,文學的秘密。
詩歌的寫作經驗對段愛松的小說創作影響很大,我們知道詩歌的寫作思維是跳躍的、抽象的,段愛松小說的敘事也是跳躍的、非線性的。此外,通過對段愛松的采訪了解到,他欣賞的作家有喬伊斯、普魯斯特、布魯諾·舒爾茨、克勞德·西蒙、歌德等,他的閱讀經驗直接影響到他善于運用西方文學寫作技巧。在小說《把一》里,作者在醫院重癥監護室、晉虛城的土基廁所、李榮家館子等幾個場景中交叉敘事,他采用意識流的寫法,由醫院的來蘇味回憶起把一和“我”在晉虛城的土基廁所里“捻安門”,由李榮家館子的鹵雞蛋顏色回到小學二年級的某一堂語文課,由炎熱的午后聯想到上西街廠房旁邊的大堂里,把一和淘七、老媉的巔峰對決。2012年,一個來自晉寧縣晉城鎮南門村的兇徒犯下了一場震驚全國的變態連環殺人案,段愛松以此為素材寫下了他的中篇小說《罪贖》。作為一個小說家,段愛松并沒有以交代前因后果或以時間為序等線性方式來敘述殺人案,他不僅充分發揮他天馬行空的想象,也運用他先鋒的敘事、詩化的文字,將一個現實發生的新聞事件重構。他在該小說每一部分開頭都引用《古蘭經》《圣經》或《壇經》里的一段,并在敘述殺人案時將宗教與古滇王國的秘境融入其中,賦予這個故事新的生命。
詩意構思和詩化的語言是段愛松小說創作重要的藝術特色,他的中篇小說《青銅魘》《葬歌》《罪贖》體現得尤為鮮明。閱讀這幾篇小說能很直觀地看到他喜歡在小說每部分的開頭引入詩歌,起到某種暗示的作用,或是與下文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除此之外,他的小說語言也具有詩歌語言的美感和高度的情感化,可見長期的詩歌寫作潛移默對他小說寫作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詩歌寫作,似乎可以說成是其他文體寫作的有效語言訓練,或者說成是其他文體詩性美學的某種終極指向。” 小說和詩歌同是文學的重要體裁,他們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都能很好地將詩歌與小說融合,達到令人迷醉和驚嘆的效果。段愛松小說里的很多語言,完全可以當作詩歌來欣賞,比如:
“時間世界,在時間的流動下趨于不朽。即使是死亡,也未能避免和阻止這種對不朽的孜孜追求。世間諸多秘密,就這樣被置于時間不朽的流動中,盡管它們從沒有被人識破過。” (《葬歌》)
“它凝視過我的眼睛,要么充盈淚水,要么射出仇恨,要么驚異萬分,要么遍布追憶,要么寫滿貪婪,要么灌注喜悅……無數的人間表情,在我的外形與質地的引領下,暴露無遺。” (《青銅魘》)
“我是眼,無所不在的眼。我看過我,在母親深紅色的子宮中,醞釀成形;我看過我,出生之后,許多陌生的眼淚,伴隨著我的哭喊;我還看過一場葬禮,在我最初的夢中,成為漫天的流星雨……”(《罪贖》)
諸如此類的語言在這幾篇小說中比比皆是,這不就是沒有分行的詩歌嗎?雖然先鋒作家如孫甘露、余華等在小說寫作中對詩化語言已有嘗試,但段愛松的詩人身份使他的詩化小說語言特色鮮明,而且詩歌語言的凝練、跳躍、隱晦也契合了他小說所營造出來的神秘、巫邪、幽暗的氛圍,這令段愛松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韻味。但筆者認為,小說語言的詩化要有一個度,過度的詩化會大大增加小說閱讀的難度,有時甚至顯得晦澀,好的文學作品要能夠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而不是曲高和寡。段愛松在小說寫作上的多種嘗試能看出他的勇氣與先鋒,但也顯露出不盡成熟之處。
三、人物形象
段愛松的短篇小說以人物命名,雖是各自獨立的篇目,卻又相互聯系,因為小說里的人物和“我”一樣都來自晉虛城。無論是身在異鄉,還是守在城里,他們都被一股神秘力量牽引,把一、小滴、巫奈、背果、老飛以及“我”都有一個現實生活里的自己和古滇國遠古時期的影子,他們都曾在某個瞬間,因為一個聲音,一個氣味,或是一個場景突然被帶入幻覺中,看到夢里的那個自己。作者有意制造幻境,讓小說里的人物穿梭在兩個世界里,就像鎳幣的正反兩面一樣,每個人物都有兩個自己。這些人物在現實世界里或被時代拋棄,或重復著無意義的生活,他們的存在是虛無的,而在另一個世界,夢境當中,那個史前的古滇國里,他們馳騁戰場,活得轟轟烈烈。上文提到,段愛松將虛構的古滇國稱為“更遠的故鄉”,這才是段愛松小說里的人物魂牽夢縈的地方。現實世界里,把一憑借“捻安門”這項特殊能力獲得肯定,這是他的價值所在,但他知道這項特異性來自于神秘力量,即使在重癥監護室里危在旦夕,把一依然等待他背后的那個人帶他回去,“他經常夢見那些奇妙的幻象,那些意象叢生的植物和動物,那些古老原始的肥沃土地,讓他多么魂牽夢縈……”(《把一》);小滴赤裸狂奔追趕紅色轎車里的父親,那是他生的希望,但他終沒有看到父親的影子,唯有在幻覺當中他看到曾經的自己躺在母親懷里吮吸乳汁才感到世界的幸福和快慰;老飛在離鄉的日子里頻繁地更換職業,每一份職業里他都能看到那個遙不可及的夢的碎片,透過這些碎片,他重新尋找在另一個城市迷失掉的歸鄉之路。相比現實世界里的自己,那個幻覺世界的自己似乎更真實。也許我們每個現代人都生活在“晉虛城”,我們自以為的現實世界才是荒誕的,而夢境里的那個世界才是我們真正的故鄉。
段愛松小說里的人物形象是虛化的,他的短篇雖然看似是以人物為中心,但閱讀之后讀者的腦海里并沒有把一、小滴、巫奈、背果、老飛這些人物的清晰輪廓。他的中篇小說,如《罪贖》《青銅魘》等,人物形象更為虛化,作者并不著力塑造人物的外貌、性格,人物在作者筆下僅僅是一個個的符號,沒有個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不重視人物,只不過作者看重的不是刻畫某個人,也不是人的表層特征,而是人本質的、內在的東西,這也是先鋒小說塑造人物常用的方式。
2016年的安徽文學年度獎對段愛松的頒獎詞中這樣說道:“當一個作家無法控制現實和把握人性的時候,穿越中的想象就成為了破譯現實和抵達人性的另一種可能”,段愛松在他的小說里極盡想象力向讀者展現神秘的異域之境,他通過史前的古滇國、巫邪的晉虛城以及發生其中的一切人和事,于現實與夢幻的切換中營造出神秘、詭異、模糊、幽暗的氛圍,這是段愛松探究現實和人的另一種途徑。
何平,段愛松.訪談:有自己獨到的異域之境,就應該寫出不一樣的小說[J]. 花城,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