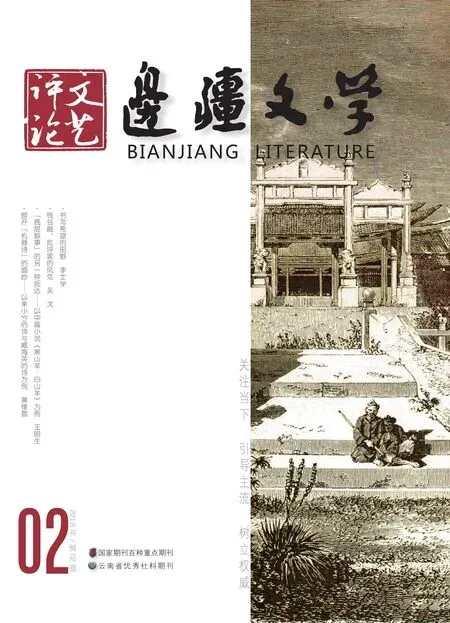后現代戲劇的敘事視角與不確定性
嚴程瑩
如果說我們把戲劇性理解為觀眾興趣的建立與保持,那么,傳統戲劇的戲劇性主要是以懸念為表征的沖突論,現代派戲劇是以變形為表征的怪誕論,那么,后現代派戲劇的戲劇性則是以含混為表征的不確定論。同樣屬于后現代派戲劇,荒誕派戲劇的不確定性是由非邏輯化的表達引起的,劇作家參與其中的痕跡較重,是劇作家故意不交代或自我否定式的交代。敘事戲劇在表達上是邏輯化的,不確定性主要依托敘事人的身份特點和視角差異來形成,是由人物引發的,與作者基本無關。一般情況下,后現代戲劇利用敘事人在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來制造不確定,形成戲劇性。
一、病態人物造成的不確定性
病態人物擔任敘事人物,有可能將情節和意義引向一種不確定狀態。情人眼里出西施,因為他們的偏執、瘋狂,他們眼中的世界也相應地呈現出病態特征,從而完成他們對這個世界的體驗性表達。謝弗《馬》中的狄薩特、《上帝的寵兒》中薩利埃里都是不正常的人,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他們視角之下的世界必然扭曲變形。狄薩特由于缺乏艾倫那樣的勇氣,因此他對這個少年充滿了好奇和同情,甚至還有一絲崇拜。薩利埃里是一個心有妒忌之火的小人,在他眼中,莫扎特當然處處顯示出不落俗套的出格之舉。
這里還可以提到德國劇作家魏斯的劇作。1963年魏斯創作了全名為《由馬爾基德薩德導演的夏郎東瘋人院病人上演的迫害與殘殺馬拉》,也選取了一群病態人物作為敘述人。馬拉與薩德歷史上確有其人,馬拉是個激進的革命者,薩德是個虛無主義者。薩德是馬拉葬禮的主持者,此人喜歡寫一些散文和戲劇,后來他被關進了夏郎東瘋人院,在那里他給一些病人排戲。薩德的這段經歷啟發了魏斯,薩德如果排演馬拉被刺是什么效果呢。于是,一出別出心裁的新戲劇就這樣誕生了。《馬拉/薩德》表現的是1808年在巴黎近郊的夏亨頓精神病院里,一群瘋子在演出。戲里的故事講的是發生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中的一起政治謀殺,即馬拉被刺。在這部戲劇中,薩德出面邀請瘋人院的瘋子排演馬拉之死的故事,他自己充當導演。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馬拉由瘋子扮演,馬拉的革命言論成了瘋言瘋語,薩德觀點與此針鋒相對,卻是在排戲,薩德是在想象中與馬拉進行思想交鋒。馬拉的話被瘋人說著,觀眾如何能信,薩德振振有詞,卻是對著一群瘋子大發感慨,言語的有效性何在。
瘋子的語匯使導演擁有了一種特殊的自由,因此布魯克在導演這出戲時認為,“在這樣一種環境里,你實際上說什么都可以。在瘋人之中,你獲得了完全的自由。你可以說極為危險和瘋癲的事。總之,可以說一切的事,而同時你又可以說些極力想人們愿意聽的政治上蠱惑人心的事。”演員們時而扮演癡傻癲狂的瘋子,時而扮演暴民、貴族、革命者,舞臺上呈現出來的是一片雜亂、喧鬧。既有詠嘆調式的大段臺詞,又有詼諧、滑稽的語言處理。既有中國戲曲寫意的形體動作,又有荒誕式的表演手法。劇中還有雜技、歌舞、夢囈,并充滿了隨意性,這是一出非常復雜的戲。嚴肅與嬉鬧、高貴與庸俗、精致與粗糙對立交錯。劇本的意義就在這種怪誕的空間里變得不確定,是瘋子把歷史史實歪曲了,還是歷史本身就是由瘋子創造的,誰也不知道,薩德的行為無疑是一場鬧劇。
二、回憶造成的不確定性
常人的記憶總是飄忽不定,難以確切,特別是一些年代久遠的事情,我們的回憶顯得更加的不可靠。所以馬克·柯里認為,“自我敘事的可靠性有賴于敘事者與所敘內容之間在時間上的距離,但如果敘事要使人相信,就得犧牲敘事的自我意識表現出來的天真。”敘事體戲劇的劇作家也有這樣的實踐。
《皇家太陽獵隊》中的人物都是真實的,歷史上的皮薩羅遠征軍不過一百六十多人,而阿塔華坡的印加帝國卻有六百萬人口,而且皮薩羅是個拜金主義者、淘金人,并不是什么精神文明的追求者,皮薩羅一收到印加王國的贖金,就殺掉了作為人質的阿塔華坡。但這個事件卻是由一個虛構的人物講述出來的,本身就值得懷疑。同時,在這部劇作中,謝弗還改變了皮薩羅到達南美的動機,屬于有意歪曲歷史,殖民者皮薩羅不遠萬里來到南美,不是為了尋求黃金而是為了尋求信仰。作者將目光投向了非歷史的神性世界和精神家園,皮薩羅在印加找到了信仰,又丟失了信仰。找到信仰后,他脫去了冷漠的外殼、洗滌了玩世不恭的心,再造了靈魂。印加王朝不死的神話在劇中只是一個背影,一個搭建戲劇情節的平臺。劇中的老馬丁既是此行的幸存者、親歷者,又是故事的敘述者,少年馬丁是當年跟隨西班牙征服者首領皮薩羅作戰的傳令兵,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少年馬丁帶著我們走進歷史事件,老年馬丁又把觀眾拉回到現實中來,過去與現在就這樣交織在我們面前,他們相互補充,有時又相互抵觸。當少年馬丁從劇情中走出成為老年馬丁時,他就是布萊希特所說的“車禍目擊者”,向我們講述過去發生的事,可惜他已經老態龍鐘,往日的記憶逐漸腐蝕,只留下了一些斷斷續續,甚至根本不可靠的記憶碎片。
所有人都像凝固了似的。
老年馬丁:死的塵土,它就在我們的鼻子里。令人恐懼的感覺來得這么快,像一場瘟疫一樣。(眾人都轉過頭來。)所有的人都擠在廣場周圍的建筑物中。(眾人都站了起來)他們站在那里,渾身發抖,隨地大小便。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三個小時過去了。(所有人都處在絕對靜止狀態。)五個小時過去了,印第安人的營地里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們的軍營也鴉雀無聲。一百六十個人,全副盔甲,騎兵已上了戰馬,步兵整裝待命,大家都站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等待。
皮薩羅:要堅持下去,聽著,你們是上帝,要鼓足勇氣,不要眨眼睛,不要吵鬧。
老年馬丁:七個小時過去了。
皮薩羅:不要動,不要動,你們要自己管住自己。孩子們,你們不再是農夫了,你們的機會來。抓住它,別把它放走。
老年馬丁:九個小時過去了,十個小時過去了。大家都感覺到寒冷在浸透著我們的軀體。
皮薩羅:(悄聲地)派他去,派他去,派他去。
老年馬丁:夜風嗖嗖,恐懼感油然而生。神父的手臂也失去了效力。
皮薩羅:太陽正慢慢地落下去。
老年馬丁:沒有人看一下自己身旁的人。后來,夜的陰影朝我們撲來。
少年馬丁:他們來啦,瞧,他們下山了。
德索托:有多少人?
少年馬丁:有幾百人,先生。
整個劇情都操近代在老年馬丁的手中,他帶領著觀眾回到從前那段時光,他所承擔的功能正是把觀眾從過去帶回到現在,而少年馬丁的表演卻又讓觀眾從現在回到過去,他們一近一遠,穿梭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英國的斯托帕德創作的《戲謔》也是如此,它的敘述人是圖書館的一名老管理員卡爾,由他回憶查拉、列寧和喬伊斯在一起的日子。可惜這個老管理員記憶力衰退,帶給我們的是一段殘缺不全的往事。
三、視角差異造成的不確定性
在敘事人的設置上,我們說存在一種分裂式的視角,就是由兩個以上的敘事人從各自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同一件事情,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去敘述同一件事,他們的視角可能會因為各自的秉性差異造成一種不確定感。也就是說,傳統戲劇中敘述視角的統一性被敘事人物的多重性破壞了,就連旁觀式和固定式視角也因為過于強調獨斷和單一而被徹底顛覆了、解構了。
在《安道爾》中,整個十二場戲可以看作是“眾人眼中的安德利”,每場戲都把不同人物與安德利的接觸作為重點,從而構成了安德利生活的一個個片斷的組接,場與場之間相對獨立,單獨存在。但就整個劇情來看,卻又保持著整體情節走勢的向前發展,即安德利一步步走向死亡。也就是說,場與場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具有視角的統一性,更多地表現為平行關系。這種情節發展的非連貫性特征,與敘事體戲劇不追求情節的完整性相關。但對于弗里施來說,他并沒有完全按照布萊希特的理論行事,而是對其進行了某種改造和創新。這主要表現在,他的劇作就整體情節來說也是完整的,但場與場之間缺乏布萊希特式的遞進關系,而表現為一種平行關系,可以說,他走在傳統戲劇體戲劇與敘事體戲劇的中間道路上。在這部劇作中,安德利死了,但每一個人都聲明不對這件事負責,那么,究竟誰應該對安德利的死負責呢,弗里施并沒有給出答案,只是理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讓觀眾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斷,自己得出結論。觀眾一邊看戲一邊思考,從而把自己從安德利之死的悲傷中解脫出來,將關注的焦點更多地放在致死原因的分析上。
海納·米勒《任務》中至少出現了四個敘述人,從而形成四個敘事文本。第一個敘述文本是劇本剛開始時格隆狄寫的信,這是以格隆狄的視角進行的第一人稱敘述,講述他和其他兩位戰友的情況,水兵與安東尼的對白是對那份信的補充。第二個敘述文本出現在第一幕與第二幕之間,是第一人稱的復數形式,描述我們初到牙買加時的情況,它雖然在敘述人稱上與第一幕相似,都是第一人稱,但它已經變為復數,可見這個視角就不再個人性的了,而是擴大了的視角。這一幕中三個人的討論和偽裝身份的場面是對第二敘述文本的戲劇性展示。第三個敘述文本是第三幕與第四幕之間,這個敘述文本相對較長,也是第一人稱敘述,但敘述者不是劇中人,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旁觀式視角,而是一個身份不明的現代歐洲人,他敘述的內容也似乎與劇情無關,但這個敘述的經歷和心態與狄波遜十分相似,他們都對一個不存在的任務產生懷疑和絕望,這實際上是第三幕敘述內容的隱喻。第四個敘述文本是第四幕之后,是第三人稱有限制的敘述,以劇中象征性人物即第一情人對狄波遜的引誘及背叛革命為主要內容,這一幕的敘述內容是這個敘述文本的延伸。可以看出,這四個敘述文本的角度和限度各不相同,從而使各個段落成為相對獨立的敘述片斷,敘述角度的統一性被取消了,這些異質化的片斷被拼貼在一起,具有拼貼戲劇的特征,體現了后現代藝術以破碎形式對抗破碎世界的藝術態度。德國威爾什說:“后現代藝術最突出的特點是對世界知覺方式的改變。世界不再是統一的,意義單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亂的,無法認識的。”也就是說,布萊希特的插曲式片斷由于敘述角度的內在統一仍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海納·米勒的敘事片斷由于敘述角度的頻繁變動,內在的統一性也取消了,場與場之間完全是異質的。打個比方,他們的劇作都是一個由碎片重新拼貼而成的整體,布萊希特的花瓶的碎片來自于原先同一個完整的花瓶,而海納·米勒的花瓶的碎片卻分別來自于原先幾個完全不同的花瓶,這些花瓶不是同一個型號,甚至不是同一窯或同一時間燒制的。
《哥本哈根》試圖解開物理大師海森堡1941年去哥本哈根拜訪老師玻爾所留下的歷史謎團。海森堡、玻爾及瑪格麗特的亡魂重聚在一起,談論1941年的戰爭,談論哥本哈根9月的一個雨夜,挪威滑雪場的比賽,納粹德國的核反應堆,同盟國正在研制的原子彈;談論量子、粒子、鈾裂變和測不準原理,談論貝多芬、巴赫的鋼琴曲;談論戰爭期間個人為國家履行的責任和義務、原子彈爆炸后城市里狼藉扭曲的尸體。原子彈的研制和爆炸使兩位物理大師深陷精神地獄,他們背負道義的重壓難以解脫。因為房間里被安裝竊聽器,他們的談話無法展開也無法深入。這次神秘的會見對以后的原子彈研究和制造,對以后的戰爭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海森堡到底跟玻爾說了什么,他們的亡魂無法說清楚。他們在尋找、回憶、思辨,不斷回到前生,回到往昔,求證他們想要的答案。“哥本哈根會見”被三個幽靈演繹了四次,但每一次都提出不同的可能性。他們不斷地重回1941年的傍晚,面對當年的困惑,但結果總是陷于迷霧,直到最后都沒能找到確切的答案。真正的問題是,他們如何面對這個道德的兩難選擇:國家抑或良知。戰后三十年,海森堡作為一名曾幫助納粹從事核研究的科學家,他的命運是悲慘的,陷入了數不清的辯解和解釋中,可是需要辯解的僅僅是海森堡一人嗎?波爾這個真正在制造原子彈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面對當年無辜百姓受害的局面,能夠僅僅逃到戰爭受難方的外衣里,逃脫良知的責問嗎?于是劇中人物一次淪入到自我辯解的怪圈中,連靈魂都無法逃脫。而這一次次辯解,一次次“讓我們再來一遍”,追尋當晚的真相,卻如同海森堡發現的測不準原理那樣,永遠無法達到事實的臨界點。在每一次的事實重演中,我們都看到了兩人談論了許多話題,再一點點地靠近那個不能觸碰的往事之痛。但是每一次的事實重演都不是事實,而展現了科學家對一些古老命題的思考:關于愛,關于良知,關于國家,關于真理,關于人性,關于父子。
總之,以這些病態人物或老人為代表,當代敘事制造了一種不可靠的信息。“當代敘事理論普遍認定這樣一個思想,即敘事只是構筑了關于事件的一種說法,而不是描述了它們的真實狀況;敘事是施為的而不是陳述的,是創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與傳統戲劇敘事相反,后現代戲劇敘事只陳述對事件的一種看法,而不是還原事件本身。因此,這是一種極具自我意識的敘述。
【注釋】
[1] [英]斯泰恩《現代戲劇理論與實踐》(三),第743頁,劉國彬等譯,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版。
[2] [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第130頁,寧一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 柳鳴九主編《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第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4] [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第130頁,寧一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