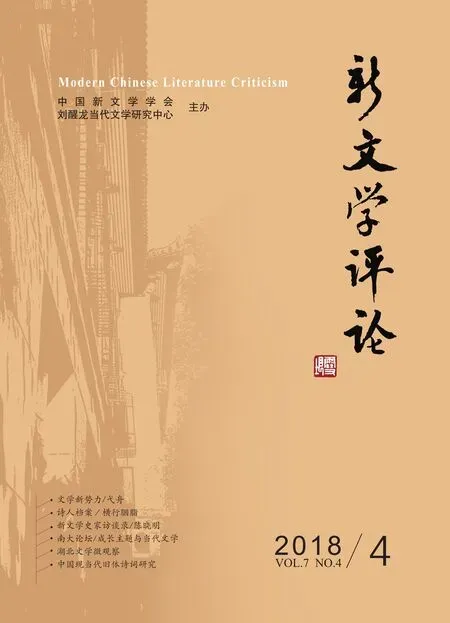主持人語
◆ 陳福民
關于弋舟及其小說創作的一些想法,包括此次推出的幾篇專論文章,如果在他獲得魯迅文學獎之前面世,也許是更為恰當的。事實上正是由于我的原因,這組文章才被拖延下來,變成了今天這種“事后諸葛亮”的樣子。然而這同時也帶給我一種理應如此的感覺,對于弋舟和他的小說來講,似乎這就是命運——弋舟小說幽深曲折的心理世界與人物性格的挫敗糾結,相對于當下的歷史認知而言,更像是暗示,那是一種無法提前宣告的柳暗花明。
當下中國的小說寫作可以說是這個世界最為繁盛的文化事業之一。無論從業人數,還是被制作、刊行的數量以及受眾的廣泛,都應該是世界之最了吧——這已經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認真說起來,這幾年的世界文學并不怎么景氣,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了“非虛構”寫作者,2016年頒發給搖滾歌手鮑勃·迪倫然后又被無情拒絕領獎,2017年石黑一雄似乎只是讓村上春樹的崇拜者再次感到了來自“日本”的失望,今年更是令人驚愕地宣布停發。盡管今年停發的表面理由是“性丑聞”所致,但這個獎項從評獎標準意識形態化愈演愈烈,到多方妥協勉力為之,事實上優品佳作難尋,其精神影響力幾近于無,所謂“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在全世界范圍的傳統語言文學衰退大潮中,中國小說是一朵逆市上揚、倔強盛開的奇葩。
弋舟是這個繁盛文化事業中的一員,但很顯然,他并不依賴潮流。盛衰之理對他不怎么起作用。比如,在現實主義以及非虛構寫作漸成大勢的今天,弋舟一直在堅持一種不那么“討好”的寫作方式。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與先鋒文學精神余韻的某種關系。這種精神關聯,讓他筆下的人物更多朝著“多余人”的方向踽踽獨行,而不是沿著涂自強的概念悲傷與一群概念裸奔。換言之,涂自強們是一覽無余的,而劉曉東們,同在失敗之余,卻仍然攜帶著很多相當熟悉也相當復雜的精神史元素。這多少讓弋舟看起來有些不合時宜。
但弋舟并不是先鋒文學的翻版。他的文學品質之所以引人矚目又令人慨嘆,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寫作始終閃爍著歷史糾葛打在現實人生上面的深刻烙印,而不是像曾經的先鋒文學那樣,完全懸置社會關系,一味凌虛高蹈。這方面讓我們多少有些了解,他的文學為何是從呂新而非其他更為“經典”的先鋒作家那里起步。就這個“起步”來看,弋舟的文學創作具有非常鮮明的雙重性癥候:一方面,他癡迷于從黑格爾那里接過來的精神生活習慣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卻又對人的現實苦厄沉淪念念不忘,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
雙重性無處不在。弋舟是“冰冷”的,又是溫暖的,他是飛翔的,又是被牢牢釘在地面上的。連同他的小說,既是空靈的抒情詩,又是一連串滯重的糾結故事。他與他的時代,有太多不自洽的裂隙,又奇怪地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