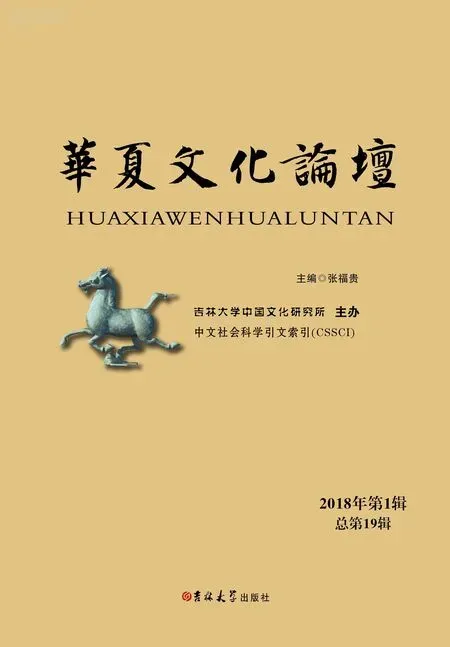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天人合一”乃國學所獨有的嗎?
——西學視野中的分析
黃保羅
【內容提要】本文以劉笑敢的 “天人合一:學術、學說和信仰——再論中國哲學之身分及研究取向的不同”(2012)一文之文獻整理的成果作為研究對象,從西學(“以理性為標準的人文學”和“以信仰為根基的基督教神學”)的視野對之進行系統的分析,論證“天人合一”并非國學所獨有。全文共分如下三個部分:首先,西學視野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天人合一”討論者的兩種類型;其次,西學視野中的宋元明清之天人合一;再次,國學之天人合一與西學之人神合一可以相互相通嗎?
在“國學熱”和中國傳統文化被特別加以強調的今天,筆者期望從西學的視野對20世紀以來已經成為代表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特點、中國哲學的基本命題、思維模式、或思維定式的熟語“天人合一”進行研究,來探索國學與西學在全球化語境里的融合性。這個術語的被重視,本由金岳霖在比較中西哲學差異時所提出,因此,在涉及中西方文化對比或對話時,“天人合一”一語似乎不可或缺。鑒于相關研究的不足之處,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劉笑敢先生曾撰文“天人合一:學術、學說和信仰——再論中國哲學之身分及研究取向的不同”(2012)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劉笑敢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天人合一”討論的文本和宋明清文獻中對“天人合一”術語的實際使用情況為研究對象,得出兩個結論:一則討論者分為學術研究路徑和文化建設路徑,二則“天人合一”擁有八條含義。
本文旨在從西學的視野來分析劉氏得出的這兩點結論,而本文所謂的“西學”,則包括“以理性為標準的人文學”和“以信仰為根基的基督教神學”兩個緯度。通過這些分析,筆者試圖論證“天人合一”是否國學所獨有之概念?
一、西學視野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天人合一”討論者的兩種類型
根據劉笑敢的研究,結合20世紀關于天人合一的討論,從宋元明清以來直接提到“天人合一”這個術語的文獻入手,可以發現,在討論有關天人合一的問題時,有兩種路徑,一是把“天人合一”作為確實存在的思想,進行學術研究;二是用“天人合一”思想來回應現代需求并以此來表達自己的宗教情懷似的文化信仰;學術研究和宗教情懷似的文化重建,是兩種在方向、方法、標準上都有不同性質的工作。在現代學科興起以前的中國,同時強調學問、修養與信仰,類似于新儒家所說的哲學、宗教、道德之為一體;而現代學術傳統則關注三者的分別。透明、公正與客觀是學術的要求,修養與信仰是私人及團體的事情,不干預公共事務也不受其限制。學術研究并不規定學者必須放棄個人的宗教信仰,但也不主張將學術園地當作個人信仰的宣教場所。劉氏提出的兩種定向,一是從事者在學術研究中以客觀、歷史和文獻資料為取向,二是以現實、當代和主觀為取向。中國哲學的身份本質是指,中國哲學是現代的學術科目,也是傳承中國文化與價值的載體;從事者可對儒、釋、道等哲學宗教作不同定位,但兩種定位不應該混淆。比如,討論天人合一的立場和目標,就涉及到它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思想,還是要用來回應現代需求的學說或用來表達自己文化信仰的工具?這二者的對象、目標、方法、標準都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劉氏的兩種定向和定位的理論在分析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天人合一的討論以及在梳理宋、明、清文獻中關于天人合一這個術語的實際使用情況上,是比較有效的工具,能夠清晰和簡潔地處理相關的文本,并能得出符合邏輯而自圓其說的結論。此文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這兩種理論,并借助它們有效地處理了相關的文本資料,就天人合一這個術語及其表達的概念內涵進行了系統的歸納。但是,劉氏對這個概念的內涵有待于進一步地深入分析,特別是從西學的視野進行分析還不夠充分,而與西學中的對應概念更是完全沒有比較。所以,筆者試圖對這些方面進行努力,特撰此文,以就教于劉氏與相關專家們。
20世紀80年代,重新討論天人合一時,最重要的文章以上面提及的金岳霖寫于1943年西南聯大時期而卻發表于1980年的題為“中國哲學”的英文文章為起點。根據劉氏的研究, 當時的觀點和立場可分成如下兩類。
第一條路徑是錢穆、季羨林二先生以現實關懷為導向,他們贊賞天人合一,因為他們相信或主張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最高代表和精華。這種工作取向不是純學術的學術研究,而是一種信仰或信念的提倡與推廣。二人都使用了“天”和“人”的術語,但他們都沒有進行界定。其實,天人合一說既是可以進行學術研究的對象,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和思想信仰,還是發展現代文化時可借鑒的一種精神資源。
劉氏正確地指出以錢、季為代表的此類關懷現實的文化建設工作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差異,類似于中國古代傳統之學中的學術、修養與道德實踐的結合。筆者認為,這其實更多地是一種帶有古希臘哲學的信仰實踐和基督教似的宗教情懷的信仰宣傳和判教。錢氏的中學高于西學的結論,更多地好像自說自話地缺乏比較。而季氏得出的中學之“天人合一”優于其他文化的結論,號稱是對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閃族文化及肇始于古代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的研究成果。拋開印度文化暫時不談,季氏對源于古代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的批評基本道出了理性主義的局限性,但他對閃族文化中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研究,似乎是不夠準確的,最起碼在“天人合一”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關系這個概念上的研究是不充分甚至是有錯誤的。首先,錢、季二位把中學傳統中的天人合一當作宗教情懷的信仰實踐而缺乏理性的界定、分析和自我反思,而完全以真理擁有者的姿態出現,混淆了學術研究和信仰實踐之間的區別,也就是沒有分清劉氏所云的兩種定位和定向。其次,錢、季沒有注意到猶太教和基督教里所擁有的“人神合一”這個概念的存在;拋開猶太教不談,就是在基督教里,就存在著羅馬天主教的“人神協作”(co-operation between God and human beings)、東正教里的“神化 (theosis)、圣化 (deification)、成神 (becoming god)”及新教里的“稱義 (justification)、成圣 (sanctification)、與基督合一(union with Christ)、在基督里 (presents/indwells in/within Christ)”等術語和概念。視如此豐富的內容而不見或不知,就得出中學之“天人合一”為最優秀的結論,的確有失匆忙而思慮不周之處。總之,以錢、季為代表的路徑有其把中學之天人合一當作信仰來宣揚和實踐的權力與合理性,但他們的問題是,在沒有按照學術規則嚴格與仔細界定所用術語的前提下,既沒有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不是學術性地對真理的探索而卻又以真理的擁有者自居,既沒有真切地認識他者(如基督教里相對的術語和概念)而卻又聲稱中學的“天人合一”最優秀。
第二條路徑是對上述宗教情懷似的文化重建路徑進行批評性分析的學術研究,有的努力研究相關概念的內涵,有的探索文化重建路徑的弊端,有的則試圖分析主張者的動機和目的。
關于相關概念含義的研究,劉笑敢提到以張岱年、李申和任繼愈為例。張強調純學術研究導向與客觀歷史的立場,進行以文本為根據的分析,不是簡單地直接將天人合一當作現代的精神資源進行弘揚,而是將“天人合一”當作研究的對象。內容主要是:(1)天人合一的思想雖然淵源于先秦時代,在漢代哲學及宋代哲學中才正式成為一種理論觀點。(2)以董仲舒、張載、程顥和程頤為代表的學說。(3)“在中國哲學史上,天人合一觀念與‘天人之分’的觀點是交參互含的。”(4)“大致說來,所謂天有三種涵義: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廣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5)“‘合’有符合、結合之義。古代所謂‘合一’,與現代語言中所謂‘統一’可以說是同義語。合一并不否認區別。合一是指對立的兩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聯不可分離的關系。”而李申則強調對于“天”之含義的學術性研究,他認為,中國傳統中的天人合一不是人與自然的合一,在《四庫全書》中找到二百余條明確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天”主要是“主宰之天”。張和李的如此研究,對于我們梳理“天人合一”這個概念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實際意義有重要貢獻,雖然他們所總結的這幾個方面是否準確、全面,不同學者可以根據發現的文獻來進行挑戰與質疑,但這種研究具有方法論和思路上的啟示。劉氏還提到了任繼愈對過分夸贊“天人合一”主張的人們的批評。任繼愈說:“有的哲學家盛贊中國哲學好就好在天人合一,這不對。人吃肉類,吃魚類,意味著對動物的摧殘,何曾合一?……生物鏈本身包含著對立的統一,并不是一味的‘合一’。”“‘天人合一’無論如何解釋,已不能反映現代人今天所要解決的問題……‘天人合一’的文章已做不下去。”任氏在這里也是把“天”理解為“自然界里的植物和動物等”,在此前提下,他反對以“天人合一”為理由地拒絕人吃肉類,吃魚類。
關于文化重建路徑之弊端的研究,劉笑敢提到了如下幾個人的研究。(1)馬積高擔心天人合一說妨礙客觀性的研究:“要給炒得過熱的天人合一說潑一點冷水,為天人相分說爭一點存在的空間”,而自然科學在古代中國落后是“束縛于天人合一說,不能把自然界之物當作獨立的對象來研究”。筆者認為,這里提到的“天人相分”和文化建設路徑堅持者對于研究對象之客觀性的忽略,的確是文化建設路徑者的軟肋,因為他們的本質是宗教情懷似的信仰宣傳和宗教實踐,但卻以學術理性和真理的姿態出現而不自知,混淆了學術性探索真理與宗教情懷似信仰之間的差異。導致的結果是,這條路徑的人們以自己未經學術探索而自以為是的主觀信仰當作客觀真理,來批評和排斥西學信仰的主觀性;而且對西學中以理性為主的科學和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宗教信仰缺乏學術性的客觀分析和研究。(2)好像任繼愈認為以“天人合一”反對人吃肉魚是不可能的那樣,劉笑敢也提到了歷史學家汪榮祖和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以歷史數據和事實說明,在生態保護方面,天人合一的傳統并沒有起到實質性的積極影響。如汪榮祖說:“季羨林所謂西方文化,重人力勝天的思維,導致生態失衡……而東方素尊天人合一的思想,與大自然為友,故能愛惜萬物,反對殺生。但事實并非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并沒有減緩中華帝國生態環境的惡化。像其他文明一樣,明清時代文明的開拓與社會經濟的進步,總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段義孚則努力根據歷史來證明,與其他宗教地區的情況相比,早期基督教地區的生態破壞情況相對更好,但在接觸西方文化之前,中國的生態環境就已經被破壞得很嚴重了。若說經濟不發達時,中國的自然災害和貧窮缺乏是天人合一的主要挑戰的話,在通過學習西方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后,中國目前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天人不合一的環境污染。但是,這里學習的西學主要是其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以人取代上帝的理性主義,對于猶太和基督教神學是幾乎完全忽略的,因此,西方經濟物質發達的同時,生態是平衡優美的,這主要得益于西學中的神學傳統的制約,但中國在學習西學的改革開放中,只學其一,未學其二。這是天人合一的討論所沒有關注的問題。
關于“天人合一”主張者的動機和目的,劉氏指出,堅持批孔的蔡尚思認為,許多人都借天的名義來宣揚自己的理論,似乎無人真誠地信仰天,他說道:“錢穆先生引孔子說的‘知我者莫天乎’等語作為孔子首先提出天人合一論的證據。其實,這句話顯然是孔子托天來提高自己的地位的。”此論不是要對古代文獻進行理解和解釋,而是要注意言者的目的和取向。蔡氏注重辨別歷史的客觀事實,而不是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更不贊同儒學可糾正與替代西方文化。蔡氏不僅把“天”當作“廣大自然”,而且當作“最高主宰”和“最高原理”。
劉得出如下兩個線索和角度。第一,從事者的工作取向不同。如,張岱年探求客觀真相,而季羨林的目的則要去滿足現代世界的需要和解決現實與未來的問題。第二,對天人合一的定位不同,前者把它當作客觀研究的對象,后者則把它當作一種用來關心或解決現實問題的思想資源,不受歷史文獻的限制而較多地加以自由發揮。劉氏的這兩點結論可以成立,但其研究主要是梳理文獻,而沒有對“天人合一”概念本身進行深入地研究,因此,劉在自己的研究中就未能充分地分析如下的背景:“天人合一”概念的內涵及其錢、季所謂的優越性是在與西學的比較中突顯出來的。也就是說,劉氏正確地指出,當錢、季等人強調“天人合一”優越于西學的時候,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這三個概念缺乏精確地界定;但是,不僅錢、季等學者,而且劉本人也沒有對西學中的相應概念“天”“人”“合”“一”及這些概念的結合體“天人合一”進行研究。比如,蔡氏把“天”當作“廣大自然”“最高主宰”和“最高原理”,這不僅與西學中理性而且與猶太和基督教神學里的上帝有可比性,但傳統的中國文獻中是否有此意義呢?
二、西學視野中的宋元明清之天人合一
除去從先秦到張載和二程的思想及少數向下延續到王陽明與王夫之的一些表述以外,宋、明、清時期對“天人合一”術語的實際使用中有多種意義,但天人合一并非思想內容清晰的理論,甚至在明清時代,這個詞語作為信仰和共同贊頌語的特征就明顯了;“天”“人”“合”“一”及“天人合一”等術語所表達的概念,都缺乏客觀性標志或界限,隨意性極大,以至于人人可講天人合一,但其內容始終不確定;天人合一的重要性隨時被夸大,而其確切含義卻不清晰;天人合一被當成宗教情懷似的重要信仰,卻沒有充分關注言語實際中該術語的使用情況;有時甚至成了空洞的套話或贊美。此特點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討論天人合一時很少涉及的。劉文得出如下結論,宋、明、清以來明確提到“天人合一”的解說模式或思想傾向,除去道家、禪宗、唯器和頌贊之語以外,主要有如下四個,筆者將從理性學術研究和基督教神學視野對它們分別進行分析。
1.張載(1020—1077)主張天人合一乃 “天道人事相貫通”。張載是第一個清晰使用“天人合一”這個詞語的儒家學者,他與儒學傳統主流一致地強調 “天道與人事之一致性或貫通性”。但“天人合一”之語本身在張載思想及后人心目中并非核心觀念,根據王夫之、張載所謂的“天人合一”就是“性之良能”出于“天之實理”。
用西方哲學的術語“本體論”(ontology)來說,人性包括其中的良能,都是來源于天、天道及天理。因此,就人學的本質來說,人性與天性、人道與天道、人與天是一致的,類似于西學中主張世界只有一個本原的“一元論”(monism)這個本體論的分支。至于張載的一元論,就其所主張的“氣”論而言,似乎很像唯物主義的一元論,雖然對此可有多種解讀。從基督教神學來看,“天人合一”可從本體論、人學(anthropology)、救贖論(soteriology)與終末論(eschatology)幾個不同視角來分析。基督教的本體論表明,若以天來表示上帝的話,人是被天/上帝造的,二者本有質的差異。從人學來說,人本來擁有“天/上帝”的“形象”(Image)和“樣式”(likenness)(創1:26-27)并“得與上帝/天的性情有份”(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彼后1:4)。而從救贖論來說,基督徒是“在基督里”(in/within/inside Christ羅16:7),而且基督也是“在基督徒里”(being/dwelling/presenting/inhabitating in/within/inside Christians,加2:20),基督徒受洗“歸入”(into)基督和“披戴”(to clothe)了基督(加3:26-27)。從終末論來說,人最終將要與天/上帝/基督聯合/合一(Union with Christ,羅6:5:“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聯合”與“合一”,在這里是同義詞。所以,就以上分析而言,不僅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天人合一”的概念,而且在西學的理性學術和基督教神學中擁有“天(/上帝)人合一”的概念和理論,甚至是更豐富的。簡單地以天人合一為由來強調國學/中學優于西學的結論是難以成立的。
2.以朱熹(1130—1200)為代表的 “以人事為重心”的天人合一:朱熹很少用“天人合一”之語,根據他的《詩集傳》,“天人合一”表示的可能是《詩經》時代 “意志之天與人事之間的關系”,與表示天道與人道之間關系的宋儒“天理”不同。《詩經》原詩講到上天降禍以示懲罰,君子應事必躬親,消弭災難,平息民怨。當時,人們多相信,天有賞善罰惡的意志。宋儒多不信天有意志,朱熹亦云“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因此,我們可從兩方面對朱熹的“天人合一”加以特別注意。
首先,朱熹所說的“天人合一”中的 “天”,不是主宰或主導性的,而且,它也不是會直接干預人事吉兇的天理,人也不能將錯誤歸咎于天理。劉氏不把朱熹所說的“天人合一”中的 “天”理解為“意志之天”而是“人/人類”,這似乎以朱熹本人的文本為根據,但朱熹之“天”是否還有其他意義,學者們可有不同觀點。在西方的哲學傳統中,唯物主義思想就把“天/上帝”理解為“人/人類”的想象或臆造。這種“天”與基督教神學里的“天/上帝”是不同的,因為基督教里的“天/上帝”不僅是有意志的,而且還是人的創造者、護佑者和救贖者。
其次,朱熹強調“天人合一”的手段和途徑是“以人事為重心”,即人的主觀原因及其行為表現決定了人是否可與天合一。雖然劉氏沒有詳細解釋朱熹所謂的“天人合一”的具體內涵,但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使“天”與“人”合一的途徑和手段。
這種思路在西方人文主義哲學中是重要流派之一,特別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首先,如耶穌基督所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約14:6)這把基督教與其他宗教文化的路徑進行了區分,強調在人與天父上帝之間,只有耶穌基督這一條排他性的道路。
其次,在基督教神學內部,討論如何通過耶穌基督這條途徑和手段來達到“天[父]與人合一”之目的時,對“人事”的討論也非常重要。貝拉基(Pelagius,360—418)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人神合作以使人與天父合一,這里對人的主觀能動性還有許多的強調,要求人的主觀行為必須順應和滿足天道的要求,只有符合天道的人的主觀努力才有與天相合的可能,如此來走“從下往上”的道路,似乎也可以達到人與天合一的境界與目的。但這種導致自由主義思想起源的貝拉基主義或半貝拉基主義被基督教會定為異端。
再次,奧古斯丁(354—430),特別是新教改革家馬丁·路德(1483—1546)則強調,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應該、能夠或可以滿足天道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目標時,特別強調了“人事”在兩種處境里的不同意義。一是在人和世界面前(coram hominibus(mundo)/ in front of human beings/the world),一個人的行為和所做的事情具有社會學和倫理學的意義,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因此,在處理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上,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有價值的。二是在天/上帝面前(coram Deo / in front of God),人通過主觀所作出的行為和事情雖有好壞的程度之分,但卻是不完善、不完美和有罪的;所謂的“罪”就是人無法達到上帝般的圣潔、公義和完全,等等。因此,在處理人與天/上帝之間的關系時,人是絕望的和無法自救的。也就是說,人的行為只能達到相對的真善美,而無法達到絕對的真善美。假如“天在上,人在下”的話,若要天人合一,從下往上的路徑是走不通的。漢語學界討論朱熹等對“以人事為重心”的強調時,參考西學中的神學人神二分當有借鑒意義,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天人無法合一的現實。
3.“以天道為重心”的天人合一:在明胡居仁(1443—1484)看來,圣人可據陰陽變化來決定權變損益,陰陽之時不能據人事損益而變化。楊爵(1493—1549)有類似觀點,即“人道必本于天道”,人事當隨順天道陰陽。但古今不同,今人一般相信,借助于科學,自然是可知的,但古人的天道陰陽卻充滿神秘。
“以天道為重心”也可以理解為對“天的客觀外在性”的強調,此與中國的“天命”思想似乎有許多可相通之處。“天命”乃“天道的意志”,延伸為“天道主宰眾生命運”,語出《書·盤庚上》:“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相當于英語的“destiny,fate”。這種意義的“天人合一”套用筆者上述“天在上、人在下”的比喻來說,要達到天人合一,必須走“從上往下”的道路,即天道主宰了人的命運,這一點恰恰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誠如耶穌基督所說:“是我揀選了你們,不是你們揀選了我”(約15:17)。這也是強調外力得救的宗教的主張。
但是,在明代胡居仁和楊爵等人“以天道為重心”的路徑中似乎很難挖掘出基督教似的“從上往下”的意義。當然,“天命”的也可以延伸理解為上天賦予人“遵行天道”的“使命”,讓人通過主觀努力來實現天的意志,但這往往會引入“以人事為重心”而“在人與世界面前”及“在天/上帝面前”都能實現天人合一的思想之中。這是中國傳統與基督教的重要差異之一。劉氏的點評也只注意西學中的理性,而沒有考慮西學中的神學,有失偏之嫌。
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在明朝的章潢(1527—1608)看來,天象和人事有內在關聯。此觀點在明代就似乎有代表性,如唐順之(1507—1560)和薛瑄(1392—1464)喜歡講天人合一,薛還以五行與五常相對應,把天人合一理解為宇宙運行與人世道德的互動,如火災等災異雖是自然現象,卻不能完全排除人為因素。根據明人邱浚(1421—1495)所說的 “七政(日月及五星)不在天而在人”,天人合一表明,自然界與人事之間有關聯。如此的“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強調政治和人事與天地之間的互動,承認自然界對人類社會有直接的政治暗示或道德警示。從現代人的理性科學來看,是一種神秘主義,是理性無法證明的信仰。但是,從基督教神學來看,天人感通則是核心教義。上帝創造、護佑、引導、獎賞、懲戒人,而人則贊美、感謝、順服和祈禱上帝。天人感通、互動是基本事實。
以上諸說表明,“天人合一”的內涵模糊而復雜:“天”可以是“自然之天、最高主宰、最高原理”。“人”則可以是包含“人性、人道”的整全之“人”。所謂“合”則可以是“以人隨天,以天隨人,天人不分,或天人感通”。“一”可能是“天意、天心、規律原則、人事倫理、萬物的世界、個人的修養境界”,有隨意和靈活性。所以,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可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但其根本特點是,很多人都不顧及天人合一的實際意含,而只將它當作最高的贊頌之語來代表最根本的原則、最高深的境界或最重要的價值。
三、國學之天人合一與西學之人神合一可以相通嗎?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這個術語,在宋明清時代就被作為一種共同接受的崇高的贊頌之詞廣泛使用,雖然對其內容本身甚少討論,但它真正在中國學術與文化界被抬高,主要還是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金岳霖比較中西哲學的文章之中。漢語學界的多數人在使用這個術語時主要存在如下幾方面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
第一,使用者們經常沒有自覺到,自己是把它當作理性學術的研究對象,還是把它當作宗教情懷似的文化建設工作在推廣和宣揚。
第二,即使在理性學術的研究中,這個術語的使用者們也往往缺乏確切的概念界定,在文化建設的推廣者特別是主張“天人合一”優于其他文化的工作者們中間,更是這樣缺乏確切的定義。
第三,當學者們對“天人合一”進行概念界定時,可從本體論、人論、救贖論和終末論等不同視角進行。
第四,從倫理學和救贖論的視角來看,通過修身養性的功夫操練,人可以逐步地提升自己而達到與天合一的目標。從救贖論的視角而言,自力得救的“從下往上”之路只能在倫理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達到相對的真善美境界,而無法達到絕對的真善美的“天”,所以,如此的天人合一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而基督教主張的外力得救,則是靠上帝的恩典通過“從上往下”的路徑拯救人,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因此,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國學之天人合一與西學之神人合一,在倫理、道德、修養和人格修煉、與大自然相處及改變生態環境等領域有許多共同點和可相通之處;所謂相通,筆者表示的是二者之間有許多相似點與合作可能性。但在本體論、救贖論和終末論等領域則有較多的差異。在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國學與西學都有所肯定,但所針對的對象卻有形而上的天或神與形而下的自然與人之分,在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分野語境中,包括理性在內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限度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簡單地宣稱國學或西學的優劣,是難以經得起學術考究的,最起碼在天人合一的問題上。在全球化的語境里,認識相似點和差異性,避免簡單的優劣和排他,努力追求相通合作,是文化或宗教相處(engagement of cultures or religions)的重要思路。總之,鑒于上述論證,筆者認為,“天人合一”并非國學所獨有之概念,西學中也有著相當甚至更加豐富的內容,且有著更加嚴密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