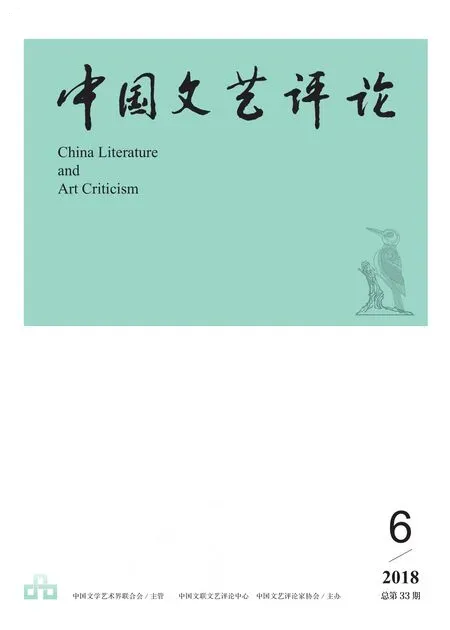如何將生活真實轉換為動人戲曲?
顏全毅
近年來,各地非常重視現實題材戲劇創作,許多反映現實生活的劇目紛紜出現,但不少作品因照搬生活、缺乏戲劇性而被詬病,在現實中足以感動人心甚至振聾發聵的“善舉”“真情”,在戲劇搬演中,為何成為干癟枯燥的說教,這也為許多戲劇創作者和觀者不解。這是因為一些創作者誤以為生活中的“事”就是臺上的“戲”,缺乏戲劇手段的合理運用;同時,一些決策者和創作者缺乏對題材的認知判斷能力,在選材上出現偏頗。現實題材戲曲劇目創作需要在選題和切入點上做好準備工作,盡量選取合適的題材和表現點,并要求創作者充分尊重戲劇規律和戲曲特性,做好充分的戲劇性轉換,避免就事說事、無戲可演。
一
如果不經過創作者的精心構思和反復琢磨,生活真實有時很難便捷地轉換為舞臺上的真實感人力量。事實上,戲劇作品還原現實真實場景的能力有時遠遠不及一張圖片或者一篇新聞報道,后二者往往是最直接迅捷和完整全息傳達信息的手段。以2008年5月發生的“汶川大地震”事件為例,在慘劇發生的同時,政府部門、社會力量參與救援的力度和艱苦付出可謂感天動地;災難中受災群眾自強不息、互相幫持的行為也感動了許多人。甚至,一位丈夫背著死去的妻子徒步十里的照片,都讓觀者久久落淚。政府的以民為本、群眾的自立自強、災難下人性的堅韌與溫暖,種種動人力量,在一則則新聞報道和一張張圖片中被反復放大和傳播。而當一些戲劇工作者試圖將這些動人故事搬上舞臺,他們的創作卻有些捉襟見肘,原本讓人淚流滿面的故事與細節在舞臺上卻未達到預期,甚至效果不如一幅圖片。
同樣,一些源自現實新聞人物的戲劇,原型故事十分感人,但在戲劇搬演后,效果不盡如人意。例如,一個山區的小姑娘贍養繼父的故事,真實動人。小姑娘因親父去世,隨母親來到繼父家中,家中還有一個老太太和兩個上中學的異姓兄長,一家人靠繼父做泥瓦匠為生。不幸的是,繼父在一次意外中受傷殘廢,砥柱中流坍塌,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生活陷入絕境,小姑娘的母親無奈要帶女兒離開,去外地打工。但小姑娘面對繼父一家的窘境,沒有選擇離去,而是獨自承擔起養家重任,在母親外出,兩位哥哥去外地上學后,她進磚廠打工,幫家里種地,在無米下鍋的窘迫中,甚至進醫院賣血,引發醫院醫生、護士的同情,紛紛為其解囊捐款。度過了艱難幾載后,隨著母親和兄長的回歸,一家人過上了安穩生活。這樣的困境事例在現實中并非偶見,小姑娘的堅韌勇敢也很值得敬佩。但搬上戲曲舞臺后,為了突出主人公的個性,頻頻制造危機乃至絕境,于是觀眾在感佩的同時,也詫異于身邊人和社會力量的缺失,身為成年人的母親離去了,兩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原本應替妹妹承擔起責任,或因上學或考軍校,都對家中困難不聞不問,而政府和社會力量也全部缺位。本來這樣的悲劇不該由小姑娘一人來完全肩負,突出主人公所陷入的絕境更使人感到不合理。生活中的偶然與散漫的元素,因為戲劇性的集中和尖銳表現,使得劇情的漏洞和瑕疵被放大,反而使真實的題材失了真。
現實生活的熱點事件和人物,如上面所舉的例子,稱得上符合“真”“善”“美”的標準,但搬上舞臺后,反而難以起到打動人心的效果,有的甚至讓觀眾覺得虛假乏味,這是一個關于現實真實和藝術真實有趣的悖論,值得創作者深思,也讓人們警醒,并非所有的現實熱點、火熱事件和優秀人物都適合搬演,創作者在選材時應謹慎掂量。以前述汶川大地震事件為例,新聞、記錄所帶有的真實震撼相對舞臺而言,更為直觀真實,而事件正在發生,強烈的真實性對于觀眾來說還記憶猶新,如果這時我們舞臺創作迅速跟進還在持續發生效應的現實事件,藝術真實很難勝過觀眾心上的真實場景,反而造成真實效果的遞減,有時候為了營造戲劇效果而產生的夸張和放大,又與真實場景產生了一定距離。因此,舞臺不能在客觀效果上與電視新聞競爭真實性,而應在內容深度和藝術效果上發揮自己的優勢。馮小剛導演的電影《唐山大地震》是在真實事件發生多年后的創作,劇情以真實事件為基礎,截取的卻是一家人在巨大災禍發生后產生的心靈“后遺癥”,特別是女主人公在“只能救一個”的天平上艱難做出選擇時,這一悲劇意味產生了強烈的戲劇沖突效果,構成了文藝作品的深刻性和震撼力,這才是揚長避短的做法。另外,我們也應看到,藝術的真實性有時會與現實真實拉開較大的距離,所謂“戲劇情境”,一些夸張甚至變形的情節與幻境設置,照樣能為觀眾認同,甚至更有真實的感覺。《牡丹亭》《羅慕路斯大帝》《青鳥》這些古今中外的名劇,或以夢幻取勝,或因夸張變形的戲劇情境而形成特色,從而構成另一種藝術上的真實。
當前現實題材舞臺劇創作中,特別是一些謳歌優秀黨員干部、英模人物與地方名人的劇目,劇情取材多有所本,感人處也非憑空虛構,一意表現“正能量”價值取向,但讓觀眾觀后,或覺得人物失真,或反覺不夠“正能量”,與前面所舉例子非常相似,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劇界的普遍重視,從戲劇創作手法和戲曲舞臺特性而言,我認為有兩個角度值得重視。
其一,并非所有真實事件和真實人物都適合戲曲舞臺進行搬演,創作者在選材和切入點上需要格外謹慎小心。這樣的例子很多,有些真實事件固然感人,卻缺乏典型性和沖突轉折;有些人物固然可敬,卻缺少個性魅力和突出特色,較難塑造出與眾不同的形象。而文藝作品常需要一定的傳奇性,所謂傳奇性,既有事件上的特殊性和引人入勝感,也有人物個性上的魅力。許多現實題材劇目不僅選材于身邊現實,更照搬現實,缺乏戲劇的波瀾起伏;在人物塑造上,又一味以仰視態度歌頌表揚,人物顯得板正,個性上缺乏神采。還有一些題材自身的矛盾過于瑣碎細微,很難構成懸念,難以具備戲劇基本要求的起承轉合,這樣的選題能否創作或怎么創作,值得三思。
其二,當下現實題材的戲曲創作,受影視、小品創作影響較大,許多作品忽視了戲曲藝術特有的表現手法和藝術規律,導致了所謂的“話劇加唱”甚至“影視加唱”的一些狀況出現。同時,由于缺乏對傳統創作手法和規律的熟悉,出現“有事無戲”“有矛盾無情趣”的問題。“事”不一定等同于戲劇中的“戲”,有時候“戲”只是一些細節、情緒或者表演技巧,現在的許多現代戲中各種事件接踵而至,卻沒有將事件升華成戲劇表演空間,其呈現缺乏審美意味。同時,一些唱念只是表現事件沖突,卻沒能轉換成高度凝練并具有沖擊力的抒情手段,更沒有提高為審美的情趣。
二
現實題材的戲曲創作除了以上常見的問題存在之外,還應特別注重“場上性”的諸種問題,包括對戲劇性的重視,對戲曲藝術規律、傳統戲曲關目的借鑒學習等等,通過運用扎實的戲劇技巧手段,使得現實題材的創作更引人入勝,更有“戲味”。
“場上性”,即針對戲劇創作,特別是戲曲創作的舞臺而特殊要求的。清代李漁就認為:“填詞之設,專為登場”,古人把戲文創作分為“案頭文學”和“場上文字”兩種,案頭文學多為作者自我欣賞、難以搬上舞臺;“場上文字”則要為舞臺呈現提供直觀的表演空間,可唱可念。“場上文字”和一般文學寫作的要求不盡相同,純粹文本的好看距離舞臺實際還有不小的距離。因而如前所述,有些在新聞報告或其他文本中感人至深的故事,舞臺呈現后卻沒能轉化為相同效果的情節,歸根結底是未能完成從“事”到“戲”的催化轉變,這種轉變,一方面,要在選題環節進行遴選,考慮題材是否具備戲劇性轉化的空間;另一方面,從原始素材中尋找切入點,運用場上創作的規律技巧進行編織設置。戲劇“場上性”特色難以遽然歸納為幾點,但對于今天現實題材的創作而言, “戲劇沖突”和“高潮兩難”的處理無疑是現實故事轉化為舞臺作品的重點和難點,既完成戲劇性的演繹,又能符合戲曲抒發情感的要求,這需要創作者的特別注意。
“沖突”當然是戲劇發生的重要基石,如同英國學者尼柯爾在《西歐戲劇理論》一書中所說:“所有的戲劇基本上都產生于沖突”,我們也很難接受一部類似說明記錄片而缺少沖突波瀾的戲劇作品。劇本創作者在選擇題目、具體創作時,都會主動尋找構成戲劇沖突的點與面,但在現實題材劇目的沖突設計時,我們經常會發現“失焦”現象。傳統戲曲注重“一人一事”,圍繞主人公的核心事件展開戲劇的起承轉合。但在現實題材創作中,往往缺少一個能夠貫穿始終的戲劇事件和沖突始末,尤其是好人好事,需要用眾多小事件、小沖突完成主題渲染,這導致事件之間缺乏遞進聯系和戲劇層次,在同一層面重復往返,這樣的沖突更多是無用功。甚至,有些劇目的主人公游離于沖突之外,成為沖突的旁觀者,這樣的劇目不符合戲曲創作的基本規律。例如,鄉村調解是現代中國社會促進穩定的重要機制,許多鄉村調解員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辛苦艱難,其中有眾多感人事跡。一些據此創作的現代戲將調解員參與調解幾件棘手案件作為戲劇沖突的主線,但主人公并不是戲劇沖突的雙方,作為調解方往往游離于事件核心之外,這就使得表現鄉村調解的劇目在沖突設計上很難吸引觀眾。
傳統戲中的沖突最引人入勝的往往是忠奸斗爭和生離死別之不得已,尖銳的沖突帶來懸念與吸引力,但在現實題材創作中,這樣的沖突是比較少見的,特別是反映當代黨員干部和英模人物的故事題材,瑣碎紛繁的日常工作才構成生活真實。為了形成沖突張力,創作者通常需要設計一些思想觀念相對落后的人物,與主人公的行動形成對比。例如最近火熱演出的歌劇《馬向陽下鄉記》,在正氣凜然的主人公村第一書記馬向陽和村委主任元芳之外,設計了貪戀覬覦村支書之位的劉世榮和商人劉玉彬,劉世榮為爭支書職位與元芳、馬向陽產生了沖突;劉玉彬要挪走村頭的老槐樹,與馬向陽形成了沖突。在主要沖突之外,又設計了村民因為貧窮與愚昧相互之間產生小矛盾,形成豐富有趣的沖突副線。應該說,這樣的沖突對于劇情的推進是行之有效的,使得戲劇具備了跌宕起伏的吸引力。但是沖突雙方有人為設定道德評價的痕跡,為了襯托主人公的無私正直,就要表現出劉世榮的私心和淺陋,實際上這個人物在劇本中的前后是割裂的,收受一個手機就為商人的愚蠢舉動說話,與他前面一心一意要掌權的訴求并不一致。實際上,當代生活的真實沖突在道德行為的高下之分之外,更多的是利益之爭、觀念之爭,甚至包括人與環境沖突、人與自身沖突等,這些都能形成強烈的戲劇沖突。歌劇《呦呦鹿鳴》表現醫學家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攻克瘧疾的艱難之路,劇作上并未習慣性地設計一些沖突對象,而把沖突設定為不可知的實驗結果以及在此過程中主人公的痛苦選擇,劇情平實但戲劇性較強,就值得現代戲創作借鑒。
高潮爆發是大型戲劇作品的核心,以抒情見長的戲曲,其高潮爆發與一般電影、電視、話劇的高潮爆發表現方式有較大的差異。影視作品、話劇的高潮往往是矛盾沖突最尖銳、懸念解決的轉圜初期,各種矛盾、懸念累積到引人入勝的節點,高潮因之爆發。戲曲藝術除了矛盾沖突的蓄積爆發,更需要注重的是情感的大沖撞大釋放。好的高潮設計,常是壓抑蓄積已久的人物內心情感一瀉千里地吐露,帶給觀眾情感沖擊。也就是說,戲曲創作有事件高潮和情感高潮,在事件高潮完成的同時或者之后,要給情感高潮以爆發的節點與空間。例如京劇傳統戲《宇宙鋒》,趙艷蓉得知父親趙高要將自己獻于秦二世胡亥時,情急之下裝瘋戲弄趙高,趙艷蓉能否裝瘋成功,瞞過父親,是戲劇的核心矛盾,當趙艷蓉不得不用女孩兒羞于表達的瘋癲狀態欺瞞過趙高,情節高潮完成,進入了情感高潮,表現的是趙艷蓉在裝瘋成功之后內心的悲慘情感,一大段【反二黃慢板】吐露了人物內心的凄楚悲憤,使人聞之動容。
當代戲曲創作的高潮設計,最好設置為人物的兩難選擇。當人物面對著兩種對立的選擇,其結果會使其命運、境遇、情感獲得截然不同的結局,而較好的選擇、容易的選擇又往往和人物內心初衷相違背,這就造成了情感的糾結,使得情感高潮隨之產生,帶給觀眾情感沖擊。兩難選擇既有自我斗爭、猶豫不決的情感牽扯,也有大是大非、大愛大恨的艱難面對,人物處于一個非常不得已的狀況中,這時的如何選擇,能帶來強烈的懸念。前者常見的如“去、留”“做、棄”的兩難,豫劇《朝陽溝》中銀環帶著對農村生活的向往,不顧母親的堅決反對,高中畢業后追隨男友栓寶來到農村,打算一輩子扎根農村。屢屢碰壁后,銀環想離開農村,可這樣一來,違背了當初自己的豪言壯語,又羞于面對母親,此時她的內心糾結不已,一大段“走一道嶺來翻一道溝”的唱詞細膩描摹出人物內心的兩難。歌劇《呦呦鹿鳴》的情感高潮是屠呦呦決定在自己身上做青蒿素實驗,實驗卻發生了意外,很可能對人造成傷害,領導為了保護人才要求停止實驗,這將使屠呦呦和同事們多年的艱辛探求付之汪洋。這時,是忍受不可知的痛苦,以求實驗完整進行;還是中止實驗,安全第一,歌劇的核心詠嘆調在這種糾結兩難中噴薄而出。后一種大是大非、愛恨兩難的情感則讓戲劇高潮更為激蕩,引人入勝。再如近些年引起強烈反響的淮劇現代戲《小鎮》,面對500萬的巨額誘惑,優秀教師朱文軒在特殊情勢下一度曾想冒領,險些因此身敗名裂,但在小鎮領頭人朱老爹極力塑造小鎮道德形象,要將朱文軒將錯就錯塑造成拾金不昧而又拒絕金錢的道德完人時,朱文軒在良知和聲名兩個選擇前產生了極為痛苦的兩難糾結。之后,戲劇的高潮便是在兩難中,朱文軒毅然公開了自己不為人知的失范行為,以勇敢認錯來完成自我救贖,高潮兩難結合淮劇一氣呵成的大段唱腔,帶給觀眾強烈的心理沖擊。
三
戲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藝術樣式,運用好歌舞手段來表現現代生活,也是讓現實題材劇目更具可看性,吸引觀眾的一種手段。
目前,一些現代題材戲曲作品存在幾類常見問題,一個是“話劇加唱”情況嚴重。現實生活場景中演故事,人物登場唱地方聲腔,看似戲曲,但味道卻不濃厚,缺乏戲曲引人入勝的場景和技巧美感,使觀賞性打了折扣;其次,戲曲歌舞是程式性的歌舞,需要對現實生活的動作進行提純、藝術化,使之符合劇種特質的程式樣貌,而不是把生活中常見的歌舞手段堆砌在戲中,給人以“戲不夠、舞來湊”的感覺。避免“話劇加唱”現象,增加戲曲表現力,就需要創作者在結構場面時盡量選取戲曲善于表現、能夠充分展開表演的情節細節,盡量避免舞臺上難以處理的空間和表演。例如,戲曲擅長于表現動態的開放空間,翻山越嶺、趕車行船、風雨行路,都是適宜表演的所在,這樣的場景入戲,會增加戲曲味道。許多現代戲作品都渲染了這樣的場景,例如越劇現代戲《我的娘姨我的娘》中,表現海島女醫生吳棣梅在臺風來臨之際,為了搶救島上的病人,在顛簸的海浪上行船,這種場景既符合劇情,又因空間的開闊和海上行船的動作性,產生載歌載舞的表現。相反,閉合的現代空間,例如高樓大廈中的寫字樓、汽車上的場景,戲曲表現力就遜色得多,現代人坐于汽車內就幾乎在戲曲現代戲中不曾出現。而歌舞的程式化處理需要現代戲創作者不斷探索和研究,現代生活的場景和方式并非與戲曲固有的程式相排斥,20世紀80年代漢劇《彈吉他的姑娘》,創作者安排并排演出了“打電話舞”,讓觀眾感到新鮮。而后京劇現代戲《駱駝祥子》和《華子良》也有將生活中的動作與程式化表演有機協調起來的成功嘗試。
既要堅持“以歌舞演故事”的戲曲美學原則,又要將現實生活的新元素、新樣式巧妙融合在戲中,這需要創作者不斷摸索,并創造性轉化,“無論是恢弘的戰爭場面還是庸常的日常生活,叱咤風云的營銷還是樸實無華的平民,是否適宜于用戲曲表現,關鍵不在于它們與戲曲通常習見的表演程式是否有距離或多大距離,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找到合適的表達內容,為戲劇家想表達的對象找到精彩的舞臺手段。”“合適的表達內容”和“精彩的舞臺手段”相結合,是現實題材戲曲特別需要開掘的內容。當前現實題材戲曲作品在舞臺手段上的貧乏、單一已經讓很多觀眾對這一類作品失去了興趣,更何況,戲曲一向有“無技不成戲”的傳統說法,戲曲作為一種藝術樣式,有自身獨特的審美范式,《四郎探母》“坐宮”一折中觀眾對“叫小番”的期待;《挑滑車》中主角高寵“三起三落”的高難度技巧所帶來的觀感沖擊,都是值得重視的藝術規律與特色。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新編京劇的成功,某種程度就是對“技”和“戲”的雙重重視,李少春排演《響馬傳》,核心場次考慮的是表演的手段和樣式,即“技”的展示可能和“戲”的支點,最終,“觀陣”一場唱舞并重,可聽可看,深為觀眾所喜,正是內容與形式的雙美所致。
其實,從現實生活中尋找題材、創作作品,與從傳統戲及其表現手法上尋找借鑒并不矛盾。相反,越是新的手段,越可以在傳統中尋找參照物,使新的表現手法與戲曲的傳統手段形成聯系。現代戲的創作者,應該努力學習并借鑒戲曲“關目”的運用。“關目”又稱“排場”,其實是長期在實踐中積累形成的適合戲曲表現、吸引觀眾的習慣套路,“關目”的使用,通常能引人入勝,使劇目顯得格外熱鬧好看。戲曲的“關目”與現代影視中的“橋段”是有直接對應關系的,在許多影視作品,特別是類型片里,常用“橋段”是凸顯類型特色的重要手段。例如,“武俠”類型片里,酒店的打斗、逼仄空間里的閃轉騰挪都必不可少;“警匪片”中,飛車競馳、各色槍戰的表現決定了作品的精彩程度。在傳統戲曲中,“長亭送別”“女扮男裝”“追舟”“微服私訪”“喬裝算命”等關目,都能讓劇目更為精彩好看,便于抒情,如《西廂記》《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長亭送別”“十八相送”等,而“女扮男裝”則更增強傳奇性,因為性別掩飾與暗示能產生很強的戲劇性。如《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祝英臺一開始在梁山伯面前掩飾自己的真實性別,在不小心說漏嘴后,乃以“我家有個小九妹”為借口岔開,其后在“十八相送”中則頻頻暗示自己的女兒身,奈何梁山伯愚鈍不解,造成強烈的戲劇效果;而《孟麗君》中,皇帝看穿孟麗君的性別妝扮,在“游上林”一出中,試圖揭穿這種喬裝,而孟麗君竭力避免被看穿。“追舟”關目適合舞臺表現,常載歌載舞,動感十足,如《玉簪記》中陳妙常對潘必正的追趕就十分膾炙人口。“微服私訪”“喬裝算命”等關目也都深受戲曲觀眾喜愛,無論是《四進士》中毛朋的微服私訪,還是《何文秀》中的喬裝算命,都因其隱含“反轉”之后的戲劇效果而為觀眾期待。現代生活固然較難套用傳統戲的關目,但思考什么樣的情節套路更適合戲曲搬演、更能為觀眾接受,從而避免“話劇加唱”“戲不夠、舞來湊”的局面,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戲曲一直有編演現代戲的傳統,以京劇為例,有《孽海波瀾》《一縷麻》等時裝戲的失敗案例,也有《白毛女》《駱駝祥子》等的成功典范,其他劇種如豫劇的《朝陽溝》、評劇的《劉巧兒》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可以說,面對現實題材,戲曲是有辦法也有手段演好的。創作者應更多借鑒以往成功經驗,吸取教訓,尊重舞臺藝術規律,創作出有質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