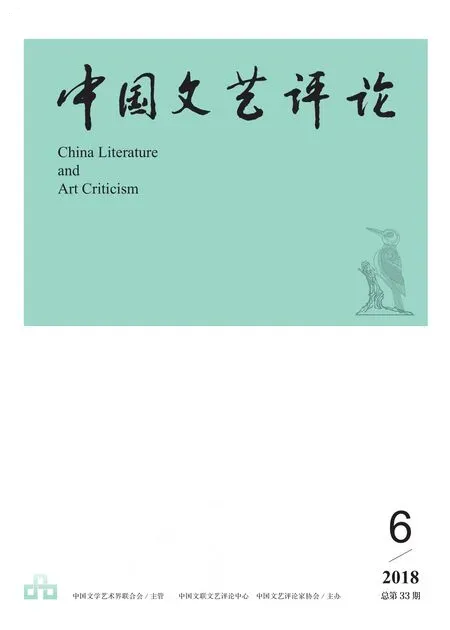十七年時期農村題材小說得失之辯:以《創業史》為例
倪萬軍
“十七年”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其文學創作遵從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文學為階級、政治、歷史服務的要求,作品的數量較前有所增加,作家的熱情高漲,很多作品著重揭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歷史巨變,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部分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以土改、農業合作化、“大躍進”等中心事件為主的作品引領著創作的風潮,并在當時獲得極高的評價。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文學敘述中,十七年文學卻是一個尷尬的存在,要么被遺忘,要么被質疑,要么被拒絕。之所以有這種結果,是因為后來的學者更多的是把十七年文學放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下重新考量。
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在當時曾經產生過轟動效果,但是也同樣經歷著被遺忘或者被質疑的尷尬。其實這種現象也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關注,為什么《創業史》在當時能夠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后來又備受冷落,或者只是被當作特殊歷史語境下的特殊文本對待,而忽視了其文本可能存在的藝術和審美因素?如果把這個問題再放大一些,在整個20世紀文學的進程中,40年代以后的文學創作在數量上每年都在呈幾何級遞增,直至今日每年的長篇小說數量都是幾千部,但是到底會有多少作品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引起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這是今天研究歷史時尤其需要深究的問題。
柳青曾希望《創業史》在50年之后還能引起人們的關注,他說:“任何一部優秀作品,傳世之作,決不是專家、編輯和作家個人自封的,至少要經過50年的考驗,才能看出個結果。”但就目前的閱讀和接受情況來看,1949年以后長篇小說中影響力能夠持續50年的恐怕并不多。不論是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所謂“當代”作品如果要獲得50年的生命力取得突破性的大發展,恐怕還需要漫長的等待。本文嘗試以柳青的《創業史》為例,著重從柳青創作的思想背景和精神資源以及作家創作沖動等角度,將柳青的創作放在十七年甚至延安文學思潮的背景下作一簡單分析,并試圖探討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為什么會處于這種尷尬境地的主要原因。
一、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思想和理論資源
十七年文學的思想和理論資源自然也是對解放區文學思想和理論資源的繼承和發揚。自延安整風運動之后,為工農兵服務、反映階級斗爭、用無產階級的文藝觀世界觀表現工農大眾的生活已經成了此后幾十年文藝創作的主導思想。尤其是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奠定了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深入影響了此后幾十年的文藝創作。
《講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集中體現,但是毛澤東文藝思想最初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在談到“十四件大事”時專門論及文化運動:
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
這是毛澤東較早關于文化與農民運動關系的闡述,完全可以看做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胚芽”,這顆“胚芽”生長在中國革命實踐的土壤中,在中國革命的風雨中迅速生根抽枝,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這顆“胚芽”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并且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這主要體現在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一節至第十五節《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和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8日的《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等文中。
尤其是《講話》發表之后,“毛澤東算了此夙愿,中國文藝中終于出現了真實的農民群眾、真實的農村生活及其苦難和斗爭。知識者的個性(以及個性解放)、只是給他們帶來的高貴氣派、多愁善感、纖細復雜、優雅恬靜……在這里都沒有地位以致消失了。頭纏羊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腳上有著牛屎’的樸素、粗狂、單純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情感方式’連同它的生活視野變得極單純又狹窄,既樸實又單調;國際的、都市的、中上層社會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見了。”這時候,毛澤東在文藝思想上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確立了文學發展的新方向,即文藝工作者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為工農兵群眾服務,文藝要處理好普及和提高的關系,文藝要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根據地“文藝界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步調漸漸趨于一致……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方向,成為眾所歸趨的道路”。
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恩來、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作了報告。周揚的報告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周揚的報告還把文學題材的轉移作為解放區文藝“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重要依據:“民族的、階級的斗爭與勞動生產成為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作為整個人民解放事業中各個方面的工作干部、作為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的腦力勞動者被描寫著。知識分子離開人民的斗爭,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內的生活及個人情感的世界,這樣的主題就顯得渺小與沒有意義了。”周揚的這種思想其實早已經產生并且成熟了,作為黨的文藝理論家,在此之前就已經對黨的文藝路線的形成和闡釋作出了很大努力。1944年周揚任延安大學校長、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時選編了《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收錄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魯迅、毛澤東關于文藝的作品,此書是一部較早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基本觀點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選本,周揚在《序言》中說明,本書是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編纂的,認為《講話》“很好地說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文藝思想,另一方面,他們的文藝思想又恰好證實了毛澤東同志文藝理論的正確”。毛澤東也對周揚的理解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給周揚的信中說:“此篇看了,寫得很好。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歷史敘述,借以證實我們今天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一點很有益處,對我也是上了一課。”
因此,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揚的發言總結了解放區文藝工作的經驗并且提出:“除了思想領導之外,還必須加強對文藝工作者的組織領導”,這其實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新的時代背景中的進一步落實。當然,1953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確定為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的最高準則,也對文藝創作一元化格局的形成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二、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主流
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在面臨改造與自我改造的同時,開始真誠考量文藝創作能否為新中國政治服務的問題,開始糾正和發展自己的創作思路、藝術風格,使之能在新中國文壇上取得一席之地。
趙樹理是其中比較成功的一位。“趙樹理現象”引起極大關注,早在1947年8月的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就提出“向趙樹理方向邁進”而且還認為“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獲,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縱觀趙樹理的創作,農民立場上的農民意識以及永遠為農民寫作的熱情使得他的小說呈現出大眾化、口語化、通俗化的特點,而且重要的是農業社會的文化心態深刻影響著趙樹理的創作。茅盾認為趙樹理的作品“標志了向大眾化前進的一步,這也是標志了進向民族形式的一步”,“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解放區以外的作者們足資借鑒”。郭沫若在讀了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之后說:“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樸素的內容與手法。” 之后他用 “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新的時代”來評價趙樹理的小說。所謂“新的時代”表示以為農民服務精神為內容的作家世界觀的確立。“新的天地”說明這一時期小說的主題內容是以無產階級農民解放和新生為前提的農村小說。“新的人物”則表示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人物描寫替代五四以來階級面目不清或者其他階級階層的人物塑造。“新的感情”表示客觀中性的情感世界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充滿了為底層農民請命的階級情感。“新的作風”則意味著鄉土小說要擺脫歐化的傾向,從形式和技巧上全面地恢復到民族傳統上來,創造適合于農民能夠接受的文風和格調。“新的文化”則預示著鄉土小說要真正走入農民文化圈,反映農民的文化傳統和革命要求,以農民的眼光來看農民,以農民的心理來書寫農民。其實這里所謂六個“新的”包含著1949年后文學發展的總體方向:為黨在農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提供文藝的依據和說明。這不但符合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本觀念也符合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在這種對農村題材小說的推崇和影響之下,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出現了以《創業史》為代表的對農村社會的描寫。一方面表現了農民在這一時代新變面前豐富的內心活動和靈魂的斗爭,另一方面表現了農民的集體意識、國家意識的逐漸形成和新的文化信仰的建立。
除了趙樹理所代表的“中國文學的方向”之外,長期生活在天津的孫犁的小說以水墨畫般的民間詩意和浪漫情懷而成為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重要收獲。當時的孫犁努力向主流文學觀念靠近,他在《論農村題材》中說:“總路線給文學指出一個重大的光輝的主題,文學應該反映農村在過渡時期的各種斗爭,反映農村生活在過渡時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文學如果充分地描寫了廣大農民在總路線燈塔照耀下所作的奮斗和努力,文學本身也就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下,得到了創作上的成功。”《鐵木前傳》等是作者這一努力的證明,作者把冀中平原和北方水鄉特有的民間的生活信念和淳樸的人性放在戰爭、革命、合作化等典型環境中,使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浪漫氣質,既不是純粹的田園牧歌式的抒情,也沒有完全陷于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窠臼。正如孫犁自己所說:“看到真善美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惡的極致,我不愿意寫,這些東西我體驗很深,可以說是鏤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寫這些東西。我也不愿意回憶它。”正因為希望表現一般的生活的美,人情美、人性美,孫犁的小說具有散文化、詩化的特征,充滿了“風俗畫”“風景畫”的靜止的美,強調地方色彩和異域情調。也因為如此,孫犁的小說并沒有獲得當時讀者的認同,不過他得到的是未來讀者的認同。孫犁的農村題材小說反映了合作化運動初期農村社會各階層思想情感和人際關系的復雜變化,中間其實包含著作者復雜的情緒,既有對童年生活的深切回憶,又有對于城市生活中復雜人際關系的反感。從藝術上來看,孫犁的小說將故事性降到最低,呈現出散文化的特點,“其藝術重心是表現流貫于生活過程間的情緒和氣質。但又不耽溺于感傷。敘述者顯露的情感介入,因著明晰、確定的描述而得到控制”。但是孫犁這種創作追求卻遠離時代,遠離政治,使得這種浪漫主義小說遠離時代風氣,從而成為一種特殊的記憶。
三、《創業史》: 無法回避的時代旋律
1949年后,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三里灣》的發表奠定了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階級斗爭的主題。此后包括孫犁的《鐵木前傳》、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大量作品均或多或少與階級斗爭的主題相關。這當中最有影響最為成功的作品就是柳青的《創業史》。
1953年4月柳青離開北京來到陜西省長安縣的皇甫鄉安家落戶,像苦行僧一樣生活在那里,并且一住就是14年。柳青在此生活期間完全像個農民,并且參加了當地的合作化運動,對這里的百姓、生產生活極為熟悉。因為有這樣的深刻體驗,所以柳青對當時中國農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對當時農民的訴求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并且“把農村的變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識到他是在面對一場歷史性的巨變,而他是史詩的記錄者”。柳青試圖通過這種史詩性的呈現,為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巨變的合法性做出注釋:“我們這個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社會制度……我寫這本書就是寫這個制度的新生活,《創業史》就是寫這個制度誕生的。”所以柳青是帶著虔誠、帶著熱情寫作《創業史》的。
《創業史》1959年在《延河》連載,1960年出版單行本,之后受到好評。尤其是小說的主題,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作家的杰出之作,是敏銳地揭示還不為許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潛流’,揭示潛在的、還未充分暴露的農村各階層的心理動向和階級沖突,并向歷史深處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現實的、歷史的根源。”
作者在諸多矛盾中抓住了四個不同的陣線(陣營):一是以梁生寶、高增福等為代表的貧雇農,他們積極倡導合作化運動,在農村的巨大變革中具有自我犧牲精神,試圖尋找到“創業”的道路帶領貧雇農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二是土改時彎下了腰,現在又想重振威勢并且破壞合作化運動的富農姚士杰、富裕中農郭世福等;三是以郭振山為代表的1949年后農村中第一代黨員干部,他們在土改時發揮過巨大作用,而在獲得土地后卻滿足個人的小富即安,甚至對于年青一代農村干部的努力表現出一種蔑視的態度;四是以梁三老漢為代表的夾在幾條陣線中徘徊不前、搖擺不定的農民。
作者在這四個主要陣線(陣營)中突出了階級斗爭和合作化運動中不同陣線的矛盾。通過富農、富裕中農和貧雇農的矛盾斗爭體現出農民階級主體性的形成,通過農民內部不同陣線的矛盾體現出農民“創業”的艱難。正如《創業史》扉頁上引用的毛澤東的話:“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斗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顯然小說中下堡鄉農民斗爭的情況只會比毛澤東的敘述更加復雜。
在這一復雜的矛盾斗爭中,作者通過梁生寶的成長、覺醒和“創業”推動了下堡鄉階級斗爭的深入發展,同時也著重突出了梁生寶這一“創業新人”的光輝形象。尤其從梁生寶的立場來看,階級斗爭不再是不同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相互消滅,而是通過無產階級的理性與包容去感化容納其他階級。可惜的是,這部長篇巨制沒能最終完成,我們也無法從作者的立場去考察梁生寶式“創業”和“斗爭”的最終成果,但是可以從農業合作化運動及此后發展中窺得一二。
土改的時候農民獲得土地,經過戰后的休養生息,農村出現貧富分化的苗頭,同時也出現農業合作化的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模式。其實農業合作化就是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業經濟改造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經濟模式。農業合作化運動共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第二階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第三階段是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
《創業史》中的農業合作化恰好處在第一二階段,1953年春秋之間。1953年合作化中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為了糾正這種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發出了《關于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五年計劃的指示》,又于3月28日發表《關于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4月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闡述了“穩步前進”的方針。但是,下半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澤東在兩次同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談話時指出“糾正急躁冒進”是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農業合作社從試辦進入發展期。
《創業史》中陜西農村下堡鄉蛤蟆灘農民經歷的恰好就是農業合作化從急躁冒進到穩步發展的階段,這也正是中國農村所有制發生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正如作品“題敘”所言:“梁三老漢草棚院子里的矛盾和統一,與下堡鄉第五村(蛤蟆灘)的矛盾和統一,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頭幾年里糾纏在一起,就構成了這部‘生活故事’的內容”,所以,將“社會主義革命”寫進小說,這便不是一部農家院子里的悲喜劇了,作者所要呈現的正是以合作化運動為主要內容的新時代農民的“創業史”。但“創業難”也是梁生寶及其他很多中國農民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這種“創業難”的感嘆在合作化的曲折進程中表現的準確而深刻,尤其是梁生寶創業的見證者梁三老漢對合作化運動及“創業難”的憂慮,體現了當時很多農民的理解和看法。在梁生寶即將帶領大家進山搞副業之前,梁三老漢帶著極大的憂慮去找支書盧明昌,最后得到盧明昌的保證和回答是“出了事情,也是俺共產黨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寶一個人坐班房呢?你放心好哩!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即便這樣,這種可能的失敗最終還是沒有能夠避免。梁三老漢的憂慮體現了部分農民對于合作化運動中梁生寶們個人命運的憂慮,同時也包含著對合作化運動的顧慮。
四、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向傳統鄉土小說的告別
這里所謂傳統“鄉土小說”是發端于五四后期,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鄉土小說的創作。在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敘述中,最早是1925年1月30日張定璜在《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出了“鄉土”的問題,他認為魯迅的作品“滿熏著中國的土氣,他可以說是眼前我們唯一的鄉土藝術家,他畢竟是中國的兒子,畢竟忘不掉中國”,并且張定璜對魯迅小說中所謂“鄉土”的氣氛作了較為恰當的描述:“極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稍后魯迅明確提出“鄉土小說”的說法:“許欽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為《故鄉》,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不過在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卻已被故鄉所放逐”,至此“鄉土文學”這一概念得以確立。
而“農村題材小說”則是1949年后對以描寫農村為主的現實主義創作的統稱,是建立在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的時代與政治背景之下的,是對社會主義農村的文學想象。
1960年邵荃麟在《文藝報》編輯部的會上說:“《創業史》中梁三老漢比梁生寶寫得好,概括了中國幾千年來個體農民的精神負擔。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漢這個人物,因此,對這部作品分析不夠”,“我覺得梁生寶不是最成功的,作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漢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嚴家炎在總體上肯定這部作品的同時,表示“我不能認同這樣一種流行說法:《創業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寶這個嶄新的青年農民英雄形象。一年來關于梁生寶的評論已經很多,而且在個別文章中,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過分的、與作品實際完全不符合的程度;相對而言,梁三老漢的形象則被注意得這樣少,這恐怕不能認為是文藝批評上的公正現象。梁生寶在作品中誠然思想上最先進。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進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作為藝術形象,《創業史》里最成功的是梁三老漢。”
嚴家炎并不認同梁生寶這個“嶄新的青年農民英雄形象”的“流行說法”,認為在反映“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偉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創業史》的成就在于“最突出地表現在梁三老漢形象的塑造上”,他的依據在于:一是形象的“豐滿”“厚實”,這是美學的標準;二是梁三老漢在“兩條道路斗爭”中處于觀望、動搖的“中間狀態”。
所以嚴家炎認為梁生寶的形象刻畫存在“三多三不多”的問題: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
針對嚴家炎等人的批評,柳青于1963年7月21日寫了一篇題為《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我如果對這些重大的問題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對革命文學事業不嚴肅的表現……我要把梁生寶描寫為黨的忠實的兒子。我以為這是當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這部小說里,是因為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不是因為有了梁生寶,村里掀起了社會主義革命浪潮。是梁生寶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長著。小說的字里行間徘徊著一個巨大的形象——黨,批評者為什么始終沒有看見它?”顯然在這里,柳青以“黨的正確領導”和黨的“巨大的形象”來批判和否定《創業史》的批評者,并將其推到了政治的對立面,而沒有像嚴家炎等批評家那樣從文學審美的角度按照美學規范來要求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以整個20世紀中國小說的審美要求來看,梁生寶的形象過于理想化英雄化,愛情、家庭和傳統的村莊秩序等在梁生寶這里都成了“創業”的羈絆,這反倒遮蔽了“梁生寶”們的真實性,遮蔽了新時代農村青年應有的光輝的人性。比如和改霞的愛情問題,梁生寶的階級和革命的理性戰勝了人的情感,與改霞分離了。作者在處理這一問題的時候,人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被簡化了,革命的、斗爭的標簽遮蓋了人性的光輝。再比如改霞對于郭振山的態度轉變也存在簡單化觀念化處理的問題。
按照嚴家炎的說法:“梁三老漢雖然不屬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是卻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特有的藝術價值”。而且從梁三老漢和梁生寶兩人的人生選擇和掙扎中來看,梁三老漢所表現出來是更多的內心沖突、失望和落寞,這恰好非常符合當時貧雇農的形象。在最初接受王氏寡母幼子時,梁三老漢內心充滿了男人的豪壯之氣和悲憫情懷:“他突然覺得自己是世界上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他雖然不曾實現父親創業的理想,但這時候“買牛、租地、立莊稼……將要把孤兒當做自己親生兒子一模一樣撫養成人,創立家業”的理想成為他新的“創業”的理想和情懷。梁三老漢這種“目光短淺”甚至“自私自利”小富即安的農民的思想和梁生寶階級上的絕對正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也是日后他們之間矛盾沖突的主要原因。但梁三老漢這種覺悟和行動都落后于這個時代的生動表現,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血肉豐滿活生生的人,而梁生寶的確有一些概念化的嫌疑。
茅盾最早在關于“鄉土文學”的論述中談到:“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然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一個只具有游歷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予我們。”可見,在考察鄉土小說的時候,最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家園及其帶給作家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批判思想。
在鄉土小說領域取得成就的作家對中國傳統鄉村田園牧歌式的盛贊,包含著浪漫主義的濃郁的鄉愁。晚清至民國,現代化的步伐及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這種“鄉愁”就發生在作家集體離別故鄉的背景之下,充滿了對鄉村社會深情的回憶。因此這一時期的鄉土小說充滿了對鄉村的重構和想象,當然也包含著以文學的方式對傳統中國的基本問題和普遍人性的深刻探討。
1949年之后,很多作家或主動或被動重新又回到了農村,這一次他們面對的是對農村的驚心動魄錯綜復雜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對農村這一現狀的描寫則構成了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因此,由此開始的農村題材小說更多的是對當時農村的階級斗爭、社會革命的記錄和書寫,正如柳青所說:“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個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為、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
所以,在《創業史》中我們遺憾地看到作者更多呈現了農村復雜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沖突,將其時農民的“創業史”寫成了一部農村的階級斗爭史;同時,作者在呈現鄉土子民的時候缺少對人性深處最為幽微的世界的探討和關懷,以階級關系簡化了農村里豐富復雜的人際關系,并且因此遮蔽了古老中國根深蒂固的鄉村秩序。因此,在《創業史》中,傳統意義上的鄉土不見了,那種讓人傷懷的鄉土不見了,取而代之卻是充滿了階級斗爭的、轟轟烈烈的農村,這或許就是從鄉土到農村的最大變化,這種變化最終的結果就是1949年之后的“農村小說”代替了五四以來的“鄉土小說”。
五、結語:如何回望過去
單將《創業史》作為一個孤立的文本討論,雖然能窺得作品價值與不足之一斑,但是卻無法求證文學與時代的特殊關系。尤其是1949年之后一段時間,中國社會陷入豐富復雜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漩渦,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影響甚至沖擊。所以,今天在考察和評價十七年文學時,首先要考慮當時的大多數作家在創作中其實根本無法回避當時的階級斗爭狀況,不能不表現時代特征和旋律;其次要看到當時的作家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需要迅速認清形勢,在時代洪流中安身立命自我保全,這也是部分作家風格轉變的重要原因;再次要看到作家本身認識的局限性使得他們無法看清當時的現實和中國的未來,盲從于各種政治宣傳和口號。
所以,今天對包括《創業史》在內的很多文學作品的遺忘和簡單拒絕并不是面對文學及其時代的客觀態度,我們要看到他們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局限性。但我們不能否定柳青在寫作《創業史》時抱著極大的真誠,其作品在當時的確把中國長篇小說的創作引向了一個高度,并對后來中國長篇小說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不能否定其在十七年期間的價值和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