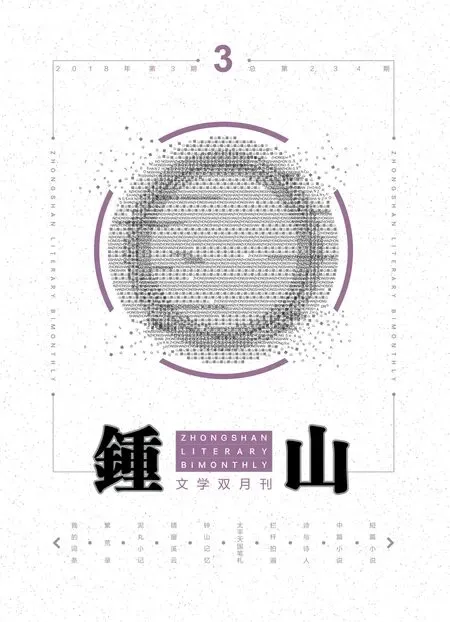沈從文與五四
張新穎
沈從文與五四,不能納入他那一代人與五四關系的大敘述模式中,應該就從他個人來說。
這個關系也不固定,隨著時代而發生變化;但卻不是順從于時代潮流而變化,因此就常常顯得不合時宜。
下面從三個時段,來做嘗試性簡述。
一、“你們所要的‘思想’”
《從文自傳》最后一節題為《一個轉機》,敘
述在湘西軍隊的末期,一個印刷工人帶來新書、新雜志,沈從文讀后感到新鮮異樣,“為時不久,我便被這些大小書本征服了。我對于新書投了降,不再看《花間集》,不再寫《曹娥碑》,卻歡喜看《新潮》《改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斷擴大滲透的影響,到一九二三年,波及到這個湘西一隅的年輕人,他決定去北京闖蕩另一種生活。這在個人身上產生的震動,說成影響是可以的,而且是彼時彼地的強烈影響,但要說成是“啟蒙”,恐怕就有些過頭了。他說,“我記下了許多新人物的名字”,“崇拜”他們,而且覺得“稀奇”,“他們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動起手來就寫了那么多,并且寫得那么好。”但是緊接著,就來了這么一句:
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來知道比他們更多,過一些日子我并且會比他們寫得更好。
這個三十歲寫自傳的人,何以如此 “前恭后倨”?
他開始寫作,既是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實際謀生問題,又是從長遠考慮尋找合乎人生理想的出路。在北大旁聽,與年輕朋友——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別的氛圍中,不拘形式的友誼,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緒、困惑,躍躍欲試的沖動,匯聚到新文學這個點上,不但增進他對新文學的理解和興趣,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寫作的欲望。
按說,他應該很快就變為“新青年”群體中的一分子——他這一代人,如果從事五四所開啟的新文學創作,不就是“新青年”嗎?可他,偏偏不像——因為不夠“新”。
“新青年”之“新”,在于拋棄“舊我”,獲得“新生”,其間的關鍵,是經歷現代思想和觀念的“啟蒙”而“覺醒”,否定“覺醒”之前的階段而確立“新我”。沈從文身上沒有發生斷裂式的“覺醒”,他的自我是以往所有生命經驗的積累、擴大和化合,有根源,有來路。他逐漸清晰而堅定地相信,他的現在和將來,他的文學,也根植于此。
《從文自傳》還說:那個工人告訴他,“白話文最要緊處是‘有思想’,若無思想,不成文章。當時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覺得十分忸怩。若猜想得著十年后我寫了些文章,被一些連看我文章上所說的話語意思也不懂的批評家,胡亂來批評我文章‘沒有思想’時,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當時似乎也就不必怎樣慚愧了。”
既不“啟蒙”,又不“革命”,不能跟著時代“前進”,不必多說,似乎自然就是“沒有思想”——如果 “思想”是時代潮流的強勢話語所定義和壟斷的,是“拿來”放到你面前要你“接受”和“武裝”的話。
在“思想”的時代,在潮流定義“思想”的變幻中,“沒有思想”當然“落伍”。一九三四年,沈從文發表《〈邊城〉題記》:
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于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后者“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讀這類作品。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個有點理性的人,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但多數人誰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話想說:“我這本書不是為這種多數人而寫的。”……這本書的出版,即或并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所棄,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并不完全放棄它,但本書作者,卻早已存心把這個“多數”放棄了。
“多數”有“思想”或要求“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就需要沒有潮流力量支撐的個人的堅持,沈從文有的,就是這種個人的堅持:“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于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過了兩年,沈從文又在《習作選集代序》中,總結自己十年來的創作歷程,強硬回應一直伴隨這一歷程的不絕責難:“只是可惜你們大多數即不被批評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時卻早被理論家把興味凝固了。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言語上,甚至于一本書的封面上,目錄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在那書的序言上就寫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么意義。”
沈從文自有他的思想,只是這是他個人的思想,是從他自己的生命經驗和現實摩擦碰撞中產生出來的,是生成之中的,不是凝固的,不是外來的,不是現成的。用現成思想的眼光打量他的作品,看不到想看到的東西,對不上號,就以為是“沒有思想”了。這樣的情形,在匆忙而沒有耐心的時代——時代的思想也匆忙而沒有耐心——似乎也無足深怪?
二、不合時宜反復談五四精神
抗戰以后,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沈從文異于往常,也異于其他多數人,頻頻談論五四,每年都寫幾篇文章,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八年。問題是,不論救國救亡,還是緊接其后的國共內戰,各有當務之急,五四都不再被時代潮流認為是適宜的話題。
沈從文這一系列文章反復強調:五四開啟的新文學運動,興起之初,以大學為中心向社會發散,但在以后的發展變化中,與大學、與教育脫離,先是與商業結緣,接著與政治攜手,顯出墮落之勢;所以需要文學運動的重建,把文運從商場和官場中解放出來,再度與學術和教育結合,這樣“一面可防止作品過度商品化與作家純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學校中保守退化腐敗現象的擴大”。
前前后后這些文章,從不同的人看來,感受的重點不甚相同。在作者自己,深憂痛感,郁結于心,迫不得已,不吐不快,乃至一說再說;友人或不免擔心,如此多管閑事,難保不惹是生非;出于好意而惋惜者也多有人在,以為舍小說創作而作這種批評,實非必要。左翼文壇反應激烈,一批文化人撰文反駁,誤解越深,敵意越重,文章的意思越被簡化,乃至標簽化。
沈從文并非“純文學”論者、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人,他回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認定它是“廿年來這個民族向上掙扎的主力”;時至今日,它仍然應該傾心致力于“社會重造”和“民族重造”的長遠愿望,努力恢復文學革命初始的莊嚴、勇敢和天真,以避免淪落為某時某地某種政治或政策的工具,附庸依賴的流行貨和裝飾品。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抗戰的大環境和救亡的迫切形勢下,以及在此后民族內部你死我活的激烈戰爭期間,沈從文偏偏反世違俗,成了一個不合時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復復的絮叨者,不僅談文學時如此,新的現實中所遭遇的種種刺激,都能觸發他從五四的立場做出反應:批評陳銓的《論英雄崇拜》,他標舉的是五四倡言的民主政治、科學精神和個人自覺,明確反對集權與領袖獨裁式的“英雄崇拜”;談論婦女問題,他覺察到的是五四所爭取的女性解放,在后來的現代教育中,并沒有進一步引導和落實到放大女性的生命和人格,《燭虛》之一、之二論女子教育,痛心于“類型女子”“做人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為她們爭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實上她并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么。”“若想起這種青年女子,在另一時社會上還稱她們為‘摩登女郎’,……會覺得這個社會退化的可怕。”他所置身其中的知識階層,沒有遠慮,沒有生活理想,“把一部分生命交給花骨頭和花紙,實在是件可怕和可羞事情。”——他的觀察或有個人化的局限和偏頗;不過由五四檢視當今,從文學運動、社會思想到文化生活,在他個人看來,諸多方面的確見出歷史過程中的“墮落”和“退化”。一些現象或為平常,而人若熟視無睹,一些個人習慣和嗜好,亦似乎不必小題大做,沈從文卻嚴苛對待,即使親近的人有時也難以理解他為什么要如此操心焦慮。他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位于他觀察、感受、評判的中心,即“從全個民族精力使用方式上來說”,以此來衡量眼前的種種人事,他不免陷入苛人而自苦的境地。
而面對“民族自殺”的悲劇,沈從文更是焦心如焚,他的五四論說,明知必會得罪雙方,陷自己于被夾擊之地,仍然忍不住要一再發聲。其心也不忍,其聲也哀痛:
一九四七年五月,發表《五四》:“五四又來了,紀念了快有三十次,這個國家的破產光景卻已差不多了。各種火都還正在燃燒,一直燒到許多人的心上。……我們要從戰爭以外想辦法,用愛與合作來代替仇恨,才會有個轉機。”
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同時發表兩篇短文,《紀念五四》和《五四和五四人》,前一篇重提五四精神的“天真”和“勇敢”,重申文運應與商場、官場分離,同教育、學術聯結,“爭取應有的真正的自由與合理的民主,希望它明日對國家有個更大的貢獻!”后一篇說,五四人“即從事政治,也有所為有所不為,永遠不失定向,決不用縱橫捭闔權譎詭祟自見。……其次是對事對人的客觀性與包涵性,對于政見文論,一面不失個人信守,一面復能承認他人存在。……民主與自由不徒是個名詞,還是一個堅定不移作人對事原則。”
三、更為悠久的“有情”歷史
此后的歲月,用不著沈從文來談五四。他自己在時代轉折之后陷入更大的困境:他的文學遭遇了新興文學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僅他個人的文學無以應付,就是他個人的文學所屬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也遭遇尷尬,也就是說,他不能依靠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來應對新興文學;況且,他個人的文學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的主導潮流,并非親密無間。但他又不愿意認同新興文學和新時代對文學的 “事功”“要求”。這個時候,就需要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來救助和支撐自己。一直隱伏在他身上的歷史意識此時蘇醒而活躍起來,幫助他找到了更為悠久的傳統。
一九五二年,在四川內江參加土改工作的沈從文,由當前而回想過去,由回憶而串聯起個人生命的歷史,自是感慨萬千;感慨之上,更有宏闊的進境:個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為久遠的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會是怎樣莊嚴的景象?
萬千人在歷史中而動,或一時功名赫赫,或身邊財富萬千,存在的即儼然千載永保……但是,一通過時間,什么也不留下,過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隨同歷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雖和事事儼然隔著,只能在這種情形下,將一切身邊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無章次條理,但是一經過種種綜合排比,隨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國風》和《小雅》,有《史記》和《國語》,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謝……時代過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相晤對。
沈從文的思想最終通到了這里:一個偉大的文化創造的歷史,一個少數艱困寂寞的人進行文化創造的傳統。
他在老式油燈下反復翻看從糖房垃圾堆中撿來的一本《史記》,夜不成寐,進入“有情”的歷史:“有情”從哪里來?“過去我受《史記》影響深,先還是以為從文筆方面,從所敘人物方法方面,有啟發,現在才明白主要還是作者本身種種影響多。……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特別重要,還是作者對于人,對于事,對于問題,對于社會,所抱有態度,對于史所具態度,都是既有一個傳統史家抱負,又有時代作家見解的。這種態度的形成,卻本于這個人一生從各方面得來的教育總量有關。換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憂患相關,不僅僅是積學而來的!年表諸書說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傳卻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東西。我們說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的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 千載之下,會心體認,自己的文學遭遇和人的現實遭遇放進這個更為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之中,可以得到解釋,得到安慰,更能從中獲得對于命運的接受和對于自我的確認。簡單地說,他把自己放進了悠久歷史和傳統的連續性之中而從精神上克服時代和現實的困境,并進而暗中認領自己的歷史責任和文化使命。
新時代,“時間開始了”,他卻進入了“舊時間”的漫漫“長河”。
同時,這也仿佛是自己過去生命中的經驗重新連接了起來,譬如:當二十一歲的軍中書記從中國古代文物和藝術品中感受人類智慧的光輝時;當三十歲的小說家的自傳寫到“學歷史的地方”來回憶這段經歷時;當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在回鄉的河流上徹悟“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而“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里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時……而生命經驗的重新連接和貫通,將一直延伸到他未來以研究文物和物質文化史安身立命的后半生歲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