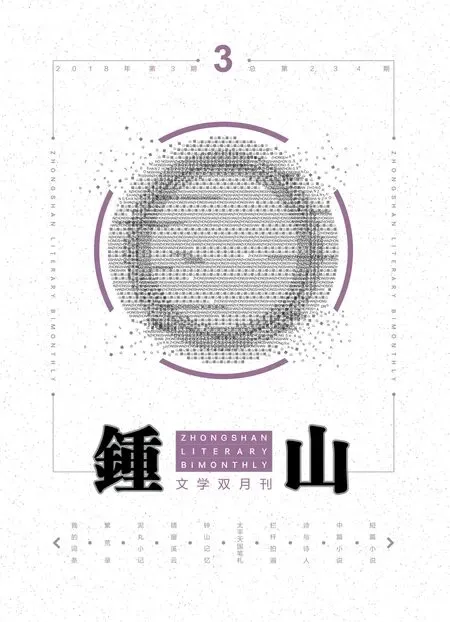我的詞條(九)
張羊羊
夏
挽了籃兒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遠去,一個胳膊已顯結實的小伙轉眼到了跟前。那年戀愛中的姑姑快要出嫁,臉紅撲撲的。姑姑嫁了個裁縫,她心靈手巧,很快也成了個裁縫。我有時去姑姑家玩,沒帶換洗的衣服,她很快就能給我做好一條短褲。
夏天一來,就有草莓吃了,還有楊梅。那是以前的事,想吃上心愛的水果得慢慢等來季節。望梅是止不了渴的,無論草本,還是木本,甜的,酸的,塞入嘴巴才會有津津之感。這兩種水果名里都有“每”字,有一說“每”是“母”的異體字,我喜歡這樣的說法。先秦有逸詩《輿人誦》“原田每每”,讀起來亦有“蓮葉何田田”的妙處,土地肥沃,草木茂盛,可謂夏天有了分量。
那是村村巷巷唱著韓寶儀柔情歡快的《粉紅色的回憶》的夏天,夏天悄悄過去了,我沒有留下什么小秘密,還未到情竇初開的年紀。那是我沒吃過烤肉、也不知道有一種調味品叫椒鹽的夏天,螢火蟲在身旁繞來繞去卻沒人理會,小板凳上手托下巴的孩子們排排坐在露天電影前。那是小學時第二個學期最后一道下課鈴一打響,第一個背上書包、捏著優異成績單跑出教室去外婆家的夏天。
一說起童年,背后都有一雙外婆的眼睛。就像有個叫澎湖灣的地方,一提到仿佛在敘述一種外婆文化。
外婆家沒有澎湖灣,外婆家也有好看的夕陽。夕陽下的黃昏,我是安靜的,乖乖喝兩碗涼好的烏豇豆大麥粥,外婆在我身邊撲打著蒲扇。我認識外婆的時候,她已是穿一身的確良短衫、不必再為隱隱透出干癟黑奶頭而含羞的老人。
自小,我就背誦了許多把農耕和讀書放一起說事的諺語。外婆姓孔,家譜里沒有她的名字,她的兄弟都是孔子的77代孫。張潮編了份讀書時間表,“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外婆識不得幾個字,要不,貪玩的漫長假日我大概也可以是個在外婆的看護下讀書認字的幸福孩子。可即便外婆有學識,我那時除了隨處可見的毛選和連環畫,經史子集手無一冊。所以也就談不上什么時間讀什么書了。
古人感嘆“我愛夏日長”也為了讀書,到我這有了生動的內容,夏日盛滿的童年比其他季節更為豐富。小腳外婆追不上我,但曉得夏日午后我大致的去處,吩咐外公提上一根長長的竹竿來不遠處的“澎湖灣”找我。那河溝不寬不長,有個小小的灣道,溝北岸是片茂密的竹林,我游得那么歡暢之際,外公的聲音就會突然出現,那竹竿差不多能夠到我的身體。他一邊喊,一邊追,像趕一只自己放養的不聽話的鴨子,直到把我趕上岸。
上岸后,外公從來不罵我一聲,領我回去替我擦干身子。我總是嘀咕,那溝也太窄了,那竹子也長得太長了,外婆稍微嘮叨幾句后,就把我摸上來的幾只河蚌剖開,用鹽打下臟膩的東西,晚上又有了一碗好湯。
一九九〇年,外公走了,前一年的夏天,他還提了竹竿把我趕上了岸。那時,我不愛聽廣播,也沒興趣看電視,方圓幾公里的村莊、田野、小河、學校就是我全部的世界。后來每年去看望外公的時候,粗糙石碑上的名字都會剝落掉些,像越穿越破的衣裳。透過邊長十厘米的正方形玻璃,不知道有條蛇是怎么爬進去的,還留了蛇蛻纏繞在那骨灰盒上。外公的照片糊得幾乎看不出任何樣子,但總覺得他的眼睛還是那么慈愛地笑著,趕我上岸的那根竹竿仿佛又要伸出來。
二〇一三年夏天外婆走了。那年,遠嫁他鄉的妹妹生第二個孩子,很想媽媽能在身邊。臥床不起的外婆讓媽媽不要去遠門了,她十分平靜地對媽媽說一句,我這幾天就快走了,不想你不在身邊。外婆還叮囑我,一定別讓媽媽出門,見我答應了她才安心。一邊是生,一邊是死,生已確定日期:6月19日;死雖也在眼前,卻估摸著有幾日時差,媽媽還是去了妹妹那。這也造成了我對外婆的最后一次謊言。日子閃了幾下,媽媽從這邊的航班剛升空,那邊的航班又升空了……外婆的一生里,領袖的名字換了一茬又一茬,記憶中的她,即便到了夏天也會把領子和袖子扣得整整齊齊。她沒讀過多少書,卻有大家閨秀的素養。最后的一刻,她還意識到用舌頭、用僅剩的力氣,將脫落下來的假牙一點一點舔回原位。她是個很要面子的人。墳不遠處的樺樹上掛了落日,小腳外婆怎么追也追不上。而我呢?依稀覺著“外婆還在輕摸我的頭/她的耳環上/下著一場民國的好看的雪”。
外婆家沒有澎湖灣,外婆家也有好看的夕陽。那條河溝不長不寬,東南西北分別住了我的四個舅舅。溝北岸茂密的竹林現已一棵不剩,溝南面的大舅舅也已離世三年。四十個夏天流經身體后,我已是一個縫縫補補的人,烏豇豆大麥粥也越來越適合我的牙口。
田字格
孩子在寫作業,嘴巴里嚼了塊口香糖,抄杜甫《春雨》時不再那么一筆一劃。覺著他寫字的速度快了,本子上的線條底紋似乎有了變化,隨手翻了下那本子的封面“方格本”。于是問他,你們不是用“田字本”嗎?他說,那是一年級用的,我已二年級了。那口氣,聽起來一年即有隔世之感。
我到四十歲這年,才琢磨起一個問題,為什么我最初的漢語書寫會從“田字格”格式開始呢?一個“口”里面一個“十”。有時還用一種本子,一個“口”里含著的虛線部分,那是一個“米”字。
孩子在寫字,寫得很自如,像一塊原野草長鶯飛。我默念宋人陳與義“田壟粲高低,白水一時滿。農夫暮猶作,愧我讀書懶。”坦白說,我這人讀書不勤也談不上多懶,想起這些句子,確因孩子作業本換成“方格本”時,仿佛看見了蒔秧時節,灌溉之水一下將畦藏了起來,白茫茫的,只有方方正正的壟露在外面。
平日,田野之壟圍起地的屬性,田野之畦就如“田字格”的虛線,更像是一種“家規”,作物生長顯得比較素凈,整齊。我們寫字也因了那虛線,有了橫、豎、撇、捺的基本規范,一個字的偏旁部首長在一起,如那些生長空間恰好的瓜棗,不歪,不裂。我見有些大人物,連起碼的橫、豎、撇、捺都沒受過規范,寫的字真不如我二年級的孩子,還好意思到處題字,不得不佩服他的膽子。
小時候用的鉛筆,真是很好的結構,一頭削了寫字,一頭鑲了塊小橡皮。我在《收集》中描述過“鐵皮文具盒上的乘法口訣/不會生銹……那里還躺著一支削尖的鉛筆/它倒立的粉橡皮/沒有擦去女孩兒的名字/她的兩條黑辮子/在方格子里擺動/她的微笑三十年不老”,這里說的是我的女同桌。她成績優異,字也寫得比我漂亮,由于家中條件不好,時常買不起新本子,以致作業本寫到最后一頁,她不得不用很好的技術從第一頁擦起。盡管她那么小心,那么認真,像對待一種藝術,第一次鉛筆壓出的痕跡還是擦不去的。她第二遍使用本子時,往往會因為作業量的不同,寫了一半已“路過”第一遍時老師用紅圓珠筆畫下的好看如蝴蝶的“優”。那個老師曾批評過我的女同桌,快換一本新作業本,每想起她臉紅耳赤的窘迫,覺著這可能也算女人最美時刻的一種。
西部某山村小學的操場上,畫出了十四乘以十的土“方格本”,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孩子們聲音清脆,一起朗誦一首綠意盎然的小詩“我家住在小山村,清晨太陽從東方慢慢升起,陽光灑在山坡上,灑在木林里,野花一朵朵遍地開放,蝴蝶來了,蜜蜂也來了,夜晚月亮悄悄地把月光帶進村子,星星眨著眼睛,好像在聽老奶奶講故事”。字跡稚嫩,看起來還沒有我那二年級的孩子不需要“田字格”的虛線在方格本寫的好。這是《上學路上》的開頭一幕,因為第八句最長有十四個字,所以操場上才畫出了這樣的行列。第四句其實是“灑在森林里”,那個默寫的孩子忘記了這個字的寫法,在那個方格的上半部分寫了個瘦弱的“木”,那個孩子還是受過“田字格”的規范的,即便寫不出來,還留了地方給字的另一半。老師拎著王二瓜的耳朵問,為什么把“森林寫成木林”?森林和木林一樣嗎?王二瓜答不上來,反問老師森林是啥樣的。老師一時無法回答森林到底是什么樣子,轉身問孩子們森和林加起來究竟有幾個木?學生們和老師以袖管答數字的方式分別有了“木林”,“森森”,“森森木”的答案。 這畫面頗為有趣,卻也能看見西部的荒涼大地上,人們對一片“森”的綠色向往。
多年來,我一直有收集各種筆記本的習慣,書柜有好幾格擺滿了它們。這些本子怕是我寫一輩子也寫不滿了,但每遇到那些本子,印有一楨喜歡的圖案或一個心動的句子,我就忍不住買了回來,更不用說看見那種封皮上粘了各類小花草標本的了。這一堆本子中,唯獨缺了本“田字格”,想想,得補上。
蓑 笠
黃圖珌認為“引古”應該這樣:引用典雅,妙在無斧鑿之痕,如美璧無瑕,明珠成串耳。我覺著吧,做到這點挺難的。可事實上,我做文章似乎離不開“引古”這個習慣。就像媽媽鋤地,一鋤頭下去掀開一個土塊,會隨手將鋤頭反過來將其敲碎,扒弄平整。所以“引古”很難“無斧鑿之痕”,做到“平整”已是不易。我寫著寫著,就想和古人“交談”一下。
本來想以《帽子》為題,似乎沒了古意,而且冒出一個詞“衣冠楚楚”來,聽起來整潔,實則有罵人之味。而《斗笠》不同,一寫下這兩字,柳宗元就出來了:“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一“引古”,唐代和共和國是那么近,就在一張紙的上一行和下一行,我陶醉于這種美妙。或者說張岱也起身了,他“擁毳衣爐火”打算去西湖邊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他穿的是毛皮衣,至于“舟中人兩三粒”什么打扮,我可以認為穿了蓑衣戴了斗笠。反正,幾個年代的雪又下到了一張紙上。
蓑衣和斗笠,都是遮雨的工具。前者用不易腐爛的蓑草或棕樹絲編織成厚厚的衣服,后者是用竹篾編織的寬邊帽。說是遮雨工具,還不如說是勞動用具,耕夫和漁夫都是謀生活。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化纖革命,雨衣把帽子和衣服整合到了一起,輕巧簡便,蓑衣和斗笠慢慢被擠出了日常生活。一些發明,刪繁就簡,抽打著古老的中國手藝和情感,都變成了輕飄飄的事物。
本家張志和寫過《漁歌子》,說的是“青箬笠,綠蓑衣”穿戴的漁翁冒著斜風細雨不想回家,那是因為時逢桃花水漲潮,眼前有肥美的鱖魚游來游去。那春雨小,西塞山前的白鷺也不怕,自在地飛著。崔道融遇見的是夏雨,又密又急,野鳥都被壓得飛不起來。“耕蓑釣笠取未暇,秋田有望從淋漓”,耕夫和釣者都沒來得及去取蓑衣斗笠。很多時候,蓑衣和斗笠似乎不能分開,成了勞作的隨身物品。
若我披蓑衣戴斗笠,那當是江湖夜雨時,我輕功甚好,踩柳踏竹,那個賊子回頭間,白光一閃,我的刀已歸鞘。若給我件塑料雨衣,我怎么也找不到俠客的感覺,它一點也不配我的刀法,那就扛把鋤頭去田里干干農活吧。
覺著蓑衣和斗笠不能合并為一個詞語,有點可惜,仿佛漢語有了缺憾。后讀《儀禮》“道車載朝服, 車載蓑笠”,原來周代就有了“蓑笠”這個詞語,不免暗暗心喜。再讀《天工開物》“紈绔之子,以赭衣視笠蓑”,漢語真有點不講理了,連倒過來“笠蓑”也可以啊。看來,對于勞動者來說,蓑和笠是平等的。于是,我干脆開心地把《斗笠》的文章名改為《蓑笠》。
我
我最古老的樣子在西安。每次到西安,陜西歷史博物館我是必去的。我會在歷史的第一個“入口”呆上很久。我第一次面對他的時候,十分驚訝,歷史書里的那張圖片竟然擺在眼前。我看著藍田猿人的神情,他也看著我,如同在照鏡子。一米之內,雖隔了上百萬年的時光和萬水千山,我總覺得他的心還在跳著,他有許多話要和我說,我和他之間存有無數種聯系。
想起一個類似的場景。有次和孩子去動物園玩,溜達到大猩猩的“居所”時,他憋不住尿就在它面前撒了起來。這其實也是不文明的,但我沒有去阻止,其他人也不會指指點點,我們都能原諒一個兩三歲的孩子在尿急時的無奈。有趣的是,隔了道玻璃,大猩猩盯著孩子的舉動一會兒竟然也撒起尿來。原來他們都是孩子,說遠點,還是表兄弟。起碼,它是那只從非洲喀麥隆逮到、坐“水星”號航天艙完成太空之旅、登上《生活》雜志封面、在北卡羅萊納州動物園度過余生的名叫漢姆的黑猩猩的表兄弟。
我被這一幕逗樂了,但樂了三秒鐘就皺起了眉頭。一個習慣了使用第一人稱語調的書寫者一時間有了“我是誰”的疑惑。其實,之前我已有過很多逃避,重設了我的身份,那里不分國籍,不知何時開始有了與人類劃清界限的想法。比如《樂園》的溫馨,“當我攜妻兒隱入叢林/變成溫順的小獸/當我的世界/沒有眾目睽睽”,比如《小王國》的浪漫,“我和她,鱗翅目籍貫的/兩個公民/在一只西紅柿里/安家,布置漂亮的/廚房與臥室/甘露漱口,花蜜香甜/我們憨厚的鄰居/住在青椒里/鞘翅目籍貫的/七星瓢蟲夫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看星光下的棉花和果園”,只有在詩歌里我可以膽子大點,過上更向往的生活。可有一天,我發覺一旦成為了人類,你換個身份過日子也挺難的,哪怕一個小小的細節。格里高爾·薩姆沙夢醒時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之后的艱難且不必說了,他習慣側向右邊睡的姿勢都無法擺出來。我也是以這種睡姿最為舒適,所以看到“他總是又擺蕩回復到仰臥姿勢”時如縛在身,仿佛看見親人因手術部位在病床上仰臥半月的無奈。想想,變成昆蟲去愛、去過日子確實有新鮮的美,但睡覺的姿勢都不能左右挺不好的,睡覺可是件大事啊。
“我”的早期甲骨文像一種有許多利齒的武器,字本義:手持大戌,吶喊示威。看起來我們常有“我行我素”的自信,但“我”的內心定還隱藏著遠古時代“吃還是被吃,獵還是被獵”困境的不安。雖然有時我想和人劃清界限,但看到獵人用一種狩獵工具“夾子”夾住一只狼、那狼無望掙脫便咬斷被夾的那條腿逃去時心里不免發毛,我還是加入人類的一員吧,如果我不成為他們,另一種狩獵工具“布魯”上的鐵錘又將被一個肌肉發達的牧民重重甩向我身體的某個部位,我的大腿骨一旦被砸碎,那該多疼。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鏡子》里有段短敘述,我覺著大致回憶了“我”組成的“我們”的簡史,“在充滿敵意的曠野中,誰也不尊敬我們,誰也不懼怕我們。黑夜和叢林讓我們滿懷恐懼。在大地上的動物群落中,我們是最羸弱的蟲豸,最無用的幼崽,即使成年也無足輕重……當時我們似乎只是一個勁地把石頭砸開,舉起棍棒合力戰斗……現在我們長大了,曾經滿懷恐懼的我們,現在制造恐懼。獵物成了獵手,口中之食成了吞食之口。昨天追殺我們的猛獸,今天成了我們的囚徒。它們住在我們的動物園里,裝點我們的旗幟和我們的頌歌。”我一出生,就已站在勝利者的陣營。可以帶著孩子,去看被圍困的獅子,老虎,豹。它們慵懶地打著哈欠,看我們的眼神已沒什么敵意了。我的孩子看《熊出沒》會笑聲不斷,恨不得找它們一起玩,他不曉得即便是動物園的狗熊,發起火來,也可以一掌擊倒他的爸爸。
后來我讀到了女詩人辛波斯卡,她的詩我最偏愛那首《在眾生中》,仿佛在解決我的一些困惑:“我就是我。/一個令人不解的偶然,/一如每個偶然。//我原本可能擁有/不同的祖先,/從另一個巢/振翅而出,/或者從另一棵樹/脫殼爬行。//大自然的更衣室里/有許多服裝:/蜘蛛,海鷗,田鼠之裝。/每一件都完全合身,/竭盡其責,/直到被穿破。//我也沒有選擇,/但我毫無怨言。/我原本可能成為/不是那么離群的事物,/蟻群,魚群,嗡嗡作響的蜂群的一份子,/被風吹亂的風景的一小部分。//某個被運者,/因身上的毛皮/或節慶的菜肴而被飼養,/某個在玻璃片下游動的東西。//扎根于地的一棵樹,/烈火行將逼近。//一片草葉,被莫名事件/引發的驚逃所踐踏。//黑暗星星下的典型,/為他人而發亮。//該怎么辦,如果我引發人們/恐懼,或者只讓人憎惡,/只讓人同情?//如果我出生于/不該出生的部落,/前面的道路都被封閉?//命運到目前為止/待我不薄。//我原本可能無法/回憶任何美好時光。//我原本可能被剝奪/好作譬喻的氣質。//我可能是我——但一無驚奇可言,/也就是說,/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是啊,命運到目前為止,待我們都不薄。翅膀有翅膀的苦惱,尾巴有尾巴的不幸。
兩者的設計理念不同,G9追求旗艦級單反的操控和使用體驗。而E-M1 II則是正統的無反思路。如果你傾向于旅行、街頭拍攝,E-M1 II顯然用起來更加方便。但如果你專注體育題材拍攝,或者手比一般人都大,G9的設計會更加適合你。
基于我不懂波蘭語,只能不動譯者的任何標點抄錄下來。如果我懂那種語言,大概可以更為感同身受。所以,我以一首《千萬個我》呼應辛波斯卡并向她致敬:“一條狐貍,一頭鯨魚/一只寡言的貓頭鷹/它們都是我,它們不說/當父親將我從千萬個我中/領回人類,從名門中/領回一個尋常人家/在過去每年的這個日期/背了書包去了學堂/我的許多真身/也在過著各自的生活/……這其實是一首糟糕的詩/一首沒有必要去完成的詩/二零一二年,在一座/叫波蘭的小鄉村/一個女詩人已寫完迷人的/《在眾生中》,她叫/——辛波斯卡/她也是另一個我”。
和辛波斯卡互換出生地,去另一片養育這樣一位詩人的土地看看。互換性別,我還缺了點勇氣,但比那些去泰國變性的有意思多了。我把她詩中某個因毛皮的被運者看作狐貍,狐貍在中國狐文化中最暖心的一幕來自戰國楚大夫屈原的 《九章·涉江》:“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沒有獵人的話,鳥兒飛了千里還能幸運地回到故鄉,狐貍也能幸運地保存好毛皮,在臨死的時候將頭朝向出生的山丘。有一天,我,也會用那只狐貍的姿勢躺下,完成我作為人的最后的儀式。
豆 腐
見媽媽供養祖宗的菜品中,豆腐是總不能少的。問及為什么不可以缺豆腐,她說上代傳下來的,不能不用。想到“菽水承歡”這個善良美好的詞語,日子再怎么清貧,做晚輩的也要好好地孝順老人。我看那桌被祭的祖宗里,爺爺是輩分最小的也是我唯一見過的,他活著時,從未聽見過大豆還有轉了基因的說法。被他供養的先人面前的那碗豆腐,豆也完全在“菽”的年月。現在,他被供上這樣一碗豆腐,當然,擺在他位置上的筷子從沒有舉起過,儀式中他仿佛夾了塊。供養完后,那碗豆腐還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吃完了。
豆腐,似乎代指了一個時代的清苦中國。若說起往后歲月廚藝中的豆腐,就擺在了美食的宴席上。別的不說,一道蟹黃豆腐,大概已和《紅樓夢》里“茄鲞”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處。還有各種我沒見過的花樣,我是無法想象這個國度在飲食上的“靈感”的,比如泥鰍鉆豆腐:水里的泥鰍被煮著煮著發現豆腐清涼,是避難的城堡,最后和豆腐相互成全。
“最后……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1935年5月23日,瞿秋白列完上面一串書單后,還說了句,“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6月18日,他被國民黨槍決于福建長汀。
我沒有離開過共和國的疆界,不曉得異國他鄉有沒有豆腐這道食物。瞿秋白說中國豆腐很好吃,那是他的口味,說世界第一,也談不上吧。辭世前念念不忘那豆腐,聽起來意味深長,像是自喻。瞿秋白吃的豆腐是什么做法?有人考證瞿秋白就義地點,說他指的是長汀的鹵水豆腐。瞿秋白是我老鄉,江蘇常州人,個人覺得即便是“世界第一”也應該是家鄉的豆腐。“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何況一個將死之人?常州豆腐湯,取嫩豆腐、豬血、百葉絲、豆渣餅(也可不放,但這確是常州獨有),煮好勾芡撒蔥花,咸淡相宜,賞心悅目,一碗豆腐湯加一塊鐵皮爐烘烤出來的大麻糕的早餐結構,我倒是想夸句“世界第一”。
不能肯定瞿秋白有沒有喝過常州豆腐湯,但家鄉冬至日風俗的一道菜總歸吃過吧——胡蔥篤豆腐。豆腐偏老點,不加任何肉類,就大胡蔥切段放一起燜,文火燉,有“篤”的耐心,出鍋就是特有的香。那豆腐“篤”得蜂窩似的,十分入味,我想完全可以令瞿秋白念及,并說很好吃。我后來每見人家做一擔豆腐挑回去時,寓意喜慶的紅紙貼在擔里最高的那塊豆腐上,一絲絲紅彌散開來,就覺得看見了瞿秋白和夫人楊之華的那枚印章 “秋之白華”。
鄉下,鄰近的幾個村都會有個豆腐作坊。媽媽娘家會挑擔黃豆去找王家村的王姓師傅加工,我們這邊會去找夏家村的丁姓師傅。豆腐做回家,年味就來了,接下來就是殺豬這件重要的事。豆腐做得多,是因為父輩們的儲備憂患。一部分切片,擺篩子露天會變成凍豆腐;一部分切塊,做成豆腐乳。來年,凍豆腐燉肉吃,豆腐乳下粥。加個小料,我們那有句罵人話,“你去買塊豆腐撞死算了”,說的是那人極其沒用。豆腐怎么能撞死人呢?但如果換成堅硬如磚的凍豆腐撞死一個人也不是沒有可能。
汪曾祺寫美食,篇幅較長的,一篇是《蘿卜》,一篇是《豆腐》,他是真把天南地北的蘿卜豆腐吃了個遍。他說的香椿拌豆腐有“一箸入口,三春不忘”之妙,我媽習慣小蔥拌豆腐,一塊豆腐加尋常佐料,醬油一定要倒點,雖沒汪曾祺所言之味,想起來還是挺饞人的。可惜,那種拌起來好吃的豆腐難找了。有人問汪曾祺敢不敢喝豆汁,他自嘲自己是個“有毛的不吃撣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老實說,他在吃方面的膽子,令我羨慕得很。
豆腐有兩鄰居,左鄰百葉,右鄰干絲,做得好,比豆腐還好吃。
元人悄大雅有《豆腐》詩,“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即入盤。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皚。青鹽化鹽鹵,絳蜂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煎烹適我口,不畏老齒摧”。讀此詩可一覽從豆到豆腐的制作過程,還能一窺典故里淮南王劉安煉制長生丹藥無意間發明豆腐的化學反應。最有意思的,我覺得收獲了某種可能的答案。供養祖先為什么不能缺豆腐呢?一,供養屬于佛教用語,與素有關;二,供養之人都是牙齒稀疏的老人,豆腐最容易咬了。當然,我的這些想法就不去和媽媽說了。
媽媽愛聽越劇,黃梅戲,還有錫劇。錫劇是我老家的劇種,有個名段《雙推磨》,所以老老少少都會哼上兩句“上坂好像龍吞珠,下坂好像白浪卷”。主人公何宜度幫寡婦蘇小娥一起挑水、推磨、灌漿、燒火……把蘇小娥一個人平常干到二更天的活很快就干完了。偶遇,相互同情,何宜度帶上老母和寡婦蘇小娥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家庭。我偶爾聽到《雙推磨》的唱句,也傻傻想過,若我還沒婚娶,帶上媽媽和一個小寡婦賣賣豆腐,過過日子,也挺好的。等媽媽走了,我開始她曾經進行過的儀式,親手做一碗好豆腐,供養她。
毛 衣
一團絨線,兩根竹針,紗窗前,有個女人在陽光下打毛衣。一個男人在想,四十歲后,衣櫥里還有件媽媽、姐姐,或者初戀打的毛衣,多好。
寫這篇文章時,媽媽在我身邊打毛衣。或者說媽媽在我身邊打毛衣,我才覺得有必要寫這篇文章。三十多年前的洋油燈邊,她就這樣打著毛衣,陪護我做作業。后來,每當我寫作的時候,我的身邊是不能有任何人的,連孩子都不許出現,任何小的動靜都可以打斷我。可媽媽在我身邊打毛衣,我依然能寫得很順手,還有種安全感。瞥一眼,看見的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線”。當然,媽媽不給我打毛衣了,她左右均勻,雙手飛快,想著給小孫子打了。兒子屬虎,她選的毛線真有老虎的斑斕膚色。她給孩子打毛衣時,我想起異國他鄉的故事,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小女孩擦亮火柴取暖,看見了火爐、烤鵝、圣誕樹、奶奶,在墻角凍死后嘴邊還露著微笑。在她周圍撒滿一地的火柴梗,小手中還捏著一根火柴。這是屬于我們這一代的童話,那小女孩太需要媽媽織件毛衣了,如果我把丹麥的這個故事說給她聽,她定會搖頭嘆息,那孩子太可憐了。
孟郊的唐代,大概還沒有毛線。唐詩里的毛衣,說的大多是鳥的羽毛: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山雞羞綠水,不敢照毛衣”、王維的《黃雀癡》“一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元稹的《表夏十首》“啖食筋力盡,毛衣成紫襦”。還有個“醉酒詩僧”可朋(約896-963,楊慎《升庵詩話》論及唐世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太白、丹棱僧可朋不相上下”),寫了個《桐花鳥》,那鳥真乖、真神奇,“五色毛衣比鳳雛,深花叢里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個人覺著,我們穿的毛衣多多少少受到過鳥羽的啟發。
開司米,馬海毛,老詞語在腦中亮晶晶地跳躍起來。我談過幾個女朋友,她們一個也不會打毛衣。談女朋友前,我穿的手工編織的毛衣,要么是媽媽打的,要么是表姐打的,我的表姐們早已成了富太太,再沒耐心打毛衣了。現在的女人怎么不會打毛衣了,真是怪事。以前的女人,多有一雙裁縫的眼光,打量一下你的身材,打的毛衣都很合身。
男耕女織的分配方式,古老而又合理。但我們村上有兩個男的也會打毛衣,而且打得很好,因為他們自小就沒有媽媽。媽媽打毛衣前,嘴巴里會冒出一串算術題。毛衣分上衣后片、上衣前片、袖片、領片。里面涉及到底邊起針、身長行數、正身長行數、肩寬針數、掛肩總行數、掛肩收針針數、掛肩收針方法、后領口針數、單肩針數、肩坡每行收針針數、袖橫密、袖口起針、袖長行數、袖根針數、袖身每邊應加針數、袖身行數、袖山行數、袖山單側收針針數、領片針數、領片行數,每一個術語還有一個數學公式,這些都熟諳于媽媽肚里。毛線一般按針數來定尺寸,所以高粗線、中粗線和細線的粗細程度又意味著各個公式的針數變化。
我說得這么專業,其實是邊寫邊問媽媽的。媽媽在身邊打毛衣,我才能寫這篇文章。我學過的所有數學知識,除了日常的加減乘除,幾乎沒派上任何用場,加起來都沒有一件毛衣所包含的智慧。我媽很多年不打毛衣了,和我住一起后靠這手工打發時間,她說孫子的毛衣打好了,又沒什么事可干了。我就和她開玩笑,你把它拆了重新打一遍。
我的衣櫥里還有兩件毛衣。幾年前,看見同事在打毛衣,就向她討,我也想穿你打的毛衣。一個月后,她拎給我一只袋子,一看,還裝了兩件。我一直喊她姐姐。
草 藥
康·帕烏斯托夫斯基有次在湖邊垂釣,因為樹叢茂盛,野花長得半人多高,岸上的人一般不容易覺察到他的人影。他聽到了幾個鄉下孩子采摘酸模時的對話。一個小姑娘像炒爆豆子似的講出了一連串花草的名字。“這是豬秧秧。這是睡蓮。瞧,就是那長著白鈴鐺的。這是杜鵑淚。”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被這極其生動的植物課驚嘆不已,這個小姑娘還講出了女婁、紫茉莉、石竹、薺草、細辛、皂根、唐菖蒲、穿心排草、百里香、金絲桃、白屈菜等等,有些花草我也認識,有些則從來沒聽說過。又瘦又小的帕姆霍老頭正好來砍柳條,用以編籮筐和籃子,他阻止那些孩子不要大聲嚷嚷,別人在釣魚呢。孩子們走開后,老頭過來向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討煙抽,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說,剛才有個小姑娘可真了不起,什么花草都認識。
“您說的是克拉娃吧?”老頭問。下面的一句開始令我驚嘆不已了,“她是集體農莊飼馬員卡爾納烏霍夫的閨女。她奶奶是全州最有本事的草藥郎中,這丫頭還有什么不認得的呢!”
那個地方是奧卡河左岸的葉塞寧諾村,俄羅斯詩人葉賽寧的故鄉。那里也有草藥郎中,完全顛覆了我腦中草藥獨屬神農氏后人的國度的概念。先人嘗了百草,一筆一筆地記錄了各類草的樣貌,當歸、枸杞、地黃、牛膝、天麻……從偶然性慢慢歸納總結它們與身體的奇妙相處。連清人黃圖珌在《看山閣閑筆》寫幾句閑情的《挽髻》也加了個“附治發少方”:側柏葉不拘多少,陰干為末,和香油涂之,其發自生且黑。黃圖珌在醫學界沒李時珍名聲大,他的這藥方看來沒什么人會去用,更不用說他的“又”了:“取羊尿不拘多少,納鯽魚腹中,用瓦缶固濟澆灰,和香油涂發,數日漸漸長而黑矣。”試問,哪個女子愿意試試?
當年,賈島去尋訪一個隱士,沒遇見,那人的弟子告訴他,師傅采藥去了。“云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這個弟子伶牙俐齒,聽起來反正就在這座山里,可山太大了,賈島未免有點失落。感覺想去找回一個姑娘,有人指一指,她就在那片海上。
我平生羨慕兩個職業。一種是牧羊人,趕了羊群翻山越嶺,從草地上尋找前程。還有一種,就是采藥人。賈島面前的那座山叫什么山,我不清楚,但山里可能藏有千年老參,靈芝,或者一朵雪蓮,像武俠中說的那樣,各有神奇的功效。我倒不是想尋得靈丹妙藥,可長生不老。瞅著愈漸衰弱的媽媽,若能采到一支好藥,有望看護她的垂暮之年。
武俠里的名醫,都有很怪的脾氣。比如《倚天屠龍記》里“非明教人士不救”的胡青牛,《天龍八部》里“你不教我一招絕招,我是不會救你的”的薛慕華,《笑傲江湖》里“醫一人,殺一人。殺一人,醫一人”的平一指。他們的怪脾氣令張三豐、喬峰、令狐沖三位俠士一點辦法也沒有。可他們的醫術名滿天下,他們就是最后的希望,他們的怪脾氣不妨看作“職業準則”,并不比當今某些名醫道德操守差。他們似乎擅長針灸、把脈,愛用草藥的是《飛狐外傳》里那個嬌弱的女子。她說,“據師父講,我的名字來源于一本叫做《黃帝內經》的醫書,靈指《靈樞》,素指《素問》。”她即是用毒專家,也是杏林妙手。當胡斐身中碧蠶毒蠱、鶴頂紅、孔雀膽三種劇毒,她瞧著胡斐柔情無限,從藥囊中取出兩種藥粉,替他敷在手背,又取出一粒黃色藥丸塞在他口中,低聲道:“我師父說中了這三種劇毒,無藥可治,因為他只道世上沒有一個醫生,肯不要自己的性命來救活病人。大哥,他不知……我會待你這樣……”說真的,我真是感動。程靈素和她用酒澆培出來“七心海棠”,一度成了我內心的一種符號。上哪去娶這樣的女子呢?可以不怕生病不怕中毒,生了病中了毒也可以被照顧好被解掉,像我這種“仰頭空了那只葫蘆,哪怕已下鶴頂紅”的癡人,則更無擔憂,有靈素和可解世間奇毒的“七心海棠”呢。
我想吧,人一出生就病了,一病一輩子。而每天吃的蔬菜就是一種好的草藥,青菜補鉀,菠菜補鐵,調理著我們身體的日常。一旦需要那些少見、甚至罕見的草藥,是我們的小病變成了大病。很多年來,我不吃那些藥丸。一是不知何故,它們總是卡在我的喉嚨,苦上老半天。二是學過化學后,我總看見那小小藥丸的身子里藏了巨大又復雜的分子結構,若進入我的體內,它們會組成無數的可能性。而草藥雖也苦,看起來卻溫和、簡單,用中國的文火熬著。
草藥是中藥的一部分,中藥的另一部分說的是動物的故事。比如刺猬可以治療什么,穿山甲可以治療什么,那些故事我就不談了,說起來會心生不適。我呢,很容易就去相信一些事,但即便相信,我也不會因為相關部位的需要去吃那些動物的腎啊肝啊的,更討厭那些熱愛消化動物生殖器的人。我喝過兩回草藥,一回是十六七歲時,個子長得不高,媽媽去藥房配了幾帖中藥。其中成分我是不知道的,反正那褐黃色的紙里包著十幾二十多種干枯的植物,我也認不出它們的面目來。那幾貼中藥苦了我半個夏天,秋天時,我的個子一下子透了出來。我的課桌也從第一、第二排到了最后的兩排。我記得那年的合影,在天安門廣場上爸爸比我高出半個頭,很快我比爸爸高出半個頭。我看著同學們的后腦勺時,想想比被同學們看著后腦勺要有意思得多。
另一回喝中藥的經歷如今想來還是很后怕的。那年去南京讀大學,因為住宿舍人多沒辦法安心寫東西,就和結識的一位文友合租了一個房子。確切地說,是他和一個女的合租了一間兩室的房子,于是讓了一間給我,他就睡到那女的房間去了。第一次進那房子,就聞到了一股草藥味,陰陰的,讓人有點兒不安。他比我大兩歲,胡子稀少得也令人不安。他有一個小本子,記載了一些藥方,卻不給任何人看。他說起了早年在山里拜師采藥的經歷,聽起來有點神奇,他說因為從小身體不好,學醫采藥是為了可以自己調理。我和他居住的短短半年里發生過許多故事,十幾年前我就用小說寫了一半,還有一半我一直想把它寫完。再回到喝藥的事情上吧,有次我重感冒,因為拒絕藥丸,又將出遠門,他說給你熬兩帖中藥喝吧,很管用。雖然我對他的醫術有所懷疑,還是被他的熱情消解了,結果證明我的重感冒在古老的西安未見得有任何好轉。
二十多歲的年紀,我的膽子太大了,居然敢喝下那么一碗中藥。
愁 恨
白居易在唐有《長恨歌》,晏殊在宋有《玉樓春·春恨》,納蘭性德在清有 《鷓鴣天·離恨》。唐之前,清以后,“恨”這種情緒就像“滾滾長江東逝水”里的浪花,從來沒有間斷過。看多了,連這個字都好像在瞪著眼睛。又有幾個人可以一壺濁酒后灑脫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有些愁恨只是小情緒,眼前擺上了國破家亡的事實,才有“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樣的悲慨從杜甫體內破胸而出。
有的恨,因為是名人嘴里說出來的,變成了流行用語中的“恨”,恨得小資了點。張愛玲就在發嗲,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鰣魚多刺,三恨《紅樓夢》未完。這恨原來也可以“抄襲”的。宋人彭幾關于海棠和鰣魚的恨又被張愛玲恨了一遍。彭幾的恨有五恨,除這兩恨外,他還恨金橘太酸、莼菜性冷、曾子固不能詩。金橘太酸,你就去吃蜜桔好了,莼菜性冷,你可以換換水芹,樹上結的,水里長的,可選的東西很多,你口味不對去恨它們干什么?南豐先生寫散文,獨樹一幟,唐宋八大家也有他一個席位,彭幾又恨他詩寫不好。畫面上,彭幾像長輩訓斥小輩似的手指著曾鞏“孺子不可教也”。我覺著這些埋怨挺沒意思的。
說得多了,“海棠無香”似乎也成了真的。這么說吧,若你靜下心來,探上鼻子,海棠初開時,芳香清新,閉上眼如有少女輕盈而過。我是聞得見海棠的香,我想一冊《劍南詩稿》有四十多首寫海棠的陸游也聞得見。說海棠無香者大概喜歡那種花香略為濃郁的,我遇見過有些花,香味過了,反倒如聞狐臭味,頭都暈。張愛玲那么鐘愛《紅樓夢》,應該不見海棠,也能從紙頁上隱隱聞得大觀園里那株西府海棠的花香來。
有人“三恨”、有人“五恨”,張潮干脆來了個“十恨”:一恨書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臺易漏,四恨菊葉多焦,五恨松多大蟻,六恨竹有落葉,七恨桂荷易謝,八恨薜蘿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有毒。老實說,我挺喜歡張潮的大部分文字,隨性,又耐看。但有時候覺得他這人愛湊數。聽個聲音吧,得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那雪聲又有什么好聽的呢?和朋友喝個酒吧,還得在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九分別找豪友、麗友、韻友、淡友、逸友,弄得我都搞不清楚身邊的朋友究竟屬于哪種了。就像這十恨,也是硬生生湊出來的。書蛀了確實挺可惜,夏天蚊子多也令人討厭,你嫌松樹下螞蟻多、綠蘿里有毒蛇,還讓別的物種活不活啊?他這十恨簡直和大自然作對。
以后,我再遇到說什么恨鰣魚多刺的,就建議他去吃河豚,遇到說什么恨河豚有毒的,就建議他去吃鰣魚。或者干脆揶揄他,你恨這恨那完全可以不吃嘛。我還在想呢,要是鰣魚和河豚能吃人的話,它們還恨你骨頭太老呢。
還有個人的“三恨”,一是沒能參加科舉以進士及第,二是未能娶山東五姓的女子為妻,三是不能參與編修國史。此人薛元超,貴為唐朝宰相,晚年說起三個遺憾來,已是閱盡千帆后的人生總結。他的“恨”與那些三恨、五恨、十恨的相比,有了分量,那些恨看起來就像是很孩子氣地隨口恨恨的。
說了那么多別人的恨,我在想自己有什么恨可以談談的。似乎沒遇上那些咬牙切齒、撕心裂肺的恩怨,我有時羨慕爸爸,生下我后,再怎么樣也解決了生下妹妹后的麻煩。我和愛人在四個字的國策中長大,慢慢就有了一個家一個孩子的觀念。后來,國策說你們可以再生一個了,我看看發間夾了些須白的女人,也終于不再忍心。若說我有什么恨的話,只有一恨:平生無女。
鑰 匙
說鑰匙的發明要比鎖晚些,這話邏輯不錯,顯然有點多余。老祖先洞穴時,還沒來得及思考鎖與鑰匙的關系。秦風漢雨中,多數人還是住土墻柴門。到我小時候,依然是平房三間,剪著瓦片的發型,東窗和西窗十分勻稱,一雙東部鄉村的眼睛,溫和地注視著平穩的田野。那時候,鄉下的門差不多是一種擺飾。一個房子沒有一扇主人進出的門,好像說不過去,鄉下的房子一般在門左下方,還有一扇小門,那是給狗進出的。鄉下,人和狗都有點身份,這身份又遠不同于如今人與狗的關系,人都快疏遠爹媽,孝子般的和狗形影不離了。
鄉下的門對開,夜深了用木頭栓下。白天時,人干農活離家不遠,一眼就能瞧見自家的門,鎖不鎖都無所謂了。有時,也假裝鎖下,左右兩個門環,一把結構簡易的鎖將它們拴一起。好像是鎖了,推下,還有個足夠的空間,鑰匙就掛在門后的鐵鉤上,兩扇門之間,胳膊是完全可以伸進去摸到那鑰匙的。鄉下,十有八九你想開哪家門都能摸到鑰匙打開,但誰有心思去開別人家的門呢?米都是一塊土地長出來的,想偷的瓜菜也是露天的,油鹽醬醋沒太多的去處,紅糖還得憑計劃供應,除了極個別的少數,哪家也不比哪家多點什么。鑰匙,就像剛出乳牙的孩子,咬在誰身上也不會疼到哪去。那門,也有一個共同的用處,哪家老人過世了,會卸下一扇,架在兩條板凳上,擺老人的尸體。
我寫過一句感嘆,用了兩個詞牌,“猶記少年《摸魚兒》,一覺醒來《瑣寒窗》”,“瑣寒窗”也可以叫做“鎖窗寒”。兩者各有味道,我偏愛于后者。還有收藏者,將存世最早的唐代銅鑄鑰匙稱作“鎖寒窗”,因為那鑰匙形狀似中國古代香閣的窗格。這么繞來繞去,鎖似乎和門沒多大的事,與窗倒是關系密切。周邦彥寫《鎖寒窗·暗柳啼鴉》有“故人剪燭西窗語”句,化的是李商隱《夜雨寄北》里“何當共剪西窗燭”。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從前的老朋友相逢,話題特別多,聊啊聊啊,就有了“剪燭”這樣美好的意象。而且,一旦老朋友相聚,燈總會亮在西窗。東窗似乎更適合設計陰謀,設計完了還容易事發。“剪燭西窗”于是成了古詩的特有畫面,連蒲松齡寫《聊齋志異》,寫楊于畏與女鬼連瑣的故事,也設置了“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的場景。以前,老朋友盼望“剪燭西窗”時還少不了一個“道具”:雨。李商隱生活在“巴山夜雨”現象中,那是西南山地多雨;周邦彥恰逢清明時節,雨也不少,“靜鎖一庭愁雨”用的是“桐花半畝”。寫著寫著,想起故鄉的泡桐花確實很快就要開了。
最初我只有一把鑰匙,用細繩串好,掛在脖子上。那時世界小,只有一扇門等著你。后來讀書遠了,得騎上一輛單車往回,就多了一把自行車鑰匙。第三把鑰匙,是書桌抽屜的,因為有些小秘密得藏起來不想讓大人知道 (那時還流行一種帶鎖的日記本,鎖與鑰匙的質地極差)。我想,有兩種鑰匙我是一輩子用不上的,我家沒有太值錢的東西,我也沒有保管絕密文件的身份,家里就不必擺保險柜了。還有四個輪子的車鑰匙,我是一點興趣也沒有。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有了第四把鑰匙,門口那只小小的信箱是我精神的巨大城堡。有書信,有《散文》、《鍾山》、《天涯》、《花城》紛至沓來,有我一生的閱讀。這兩日讀到余華說的一個細節,很有趣,“當時我們家有一個院子,郵遞員騎車過來把退稿從圍墻外面扔進來,只要聽到很響的聲音就知道退稿來了,連我父親都知道。有時候如果飛進來像雪花一樣飄揚的信,我父親就說這次有希望。”這段敘述對大多數職業來說,沒什么特別的感受,像我們這些人,會想起心提到嗓子眼的往事。我曾經每天在那差不多的時刻,等郵遞員的身影,有種厚厚的信,裝回你熬過的夜和編輯寫上“大作不適刊用,請另投他處”之類字眼的稿簽。失望了許多許多次后,終于有一天,我打開那只信箱,收到一封薄薄的“像雪花一樣飄揚的信”,信封上的來信地址是天津,印刷好的“《散文》編輯部”。我捏著這只蝴蝶,對著太陽,祈愿未拆前,陽光穿過翅膀能透出一點點命運的花紋。打開后,一張小小的信紙上寫了幾行清秀的字 “您好,大作 《輪回》、《關于一條狗》留用,刊明年第1期,有新作繼續寄來。鮑伯霞”,從投稿信到用稿信僅隔了一個星期,這短短的時間和短短的幾句影響了我以后的歲月,我吻了吻那把信箱鑰匙,等著兩個月后2005年第1期《散文》的燦爛笑臉。
后來搬過兩次家,鑰匙又多了幾把。我始終沒有給門裝上一種手指可以當鑰匙用的指紋鎖。像我媽那樣不肯歇下來的人,忙這忙那的,手指上的老繭也變換著個頭,我怕有一天指紋鎖認不出她來,她只能呆呆地被關在門外。再讀賈平凹先生的《寫給母親》,他說“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閉著的眼是再沒有睜開,但她肯定還是認為她在掛液體了,沒有意識到從此不再醒來,因為她躺下時還讓我妹把給她擦臉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邊,系在褲帶上的鑰匙沒有解,也沒有交代任何后事啊。”坦白講,因為讀到這一段我才想起寫寫鑰匙,我媽就是把那一串鑰匙系在褲帶上的,仿佛系住了鄉下的房子,鎮上的房子,城里的房子,我的城里的新房子。她隔段日子就會去每個家打掃打掃,收拾收拾,她的褲帶上系著爸爸,我,愛人和孩子,我媽那么滿足。
和愛人婚后兩年,終于等來了兩把牙齒一模一樣的鑰匙,那個屋子里,我們開始安心生育。我就像把鑰匙,打開了她這道門,門一開,有了張簡之。他的脖子上也快掛上一把牙齒一模一樣的鑰匙。有時我還做夢,夢見有人敲門,門一打開,是一個長得那么像我的女孩,她抬頭望著我,仿佛有許多話要說,“快叫爸爸”,一個耳熟的聲音囑咐小女孩。我失散多年的初戀出現在我面前,她的眼角多了皺紋。“爸爸。”我鼻子一酸,擁小女孩入懷,給她的脖子掛上一把牙齒一模一樣的鑰匙……看來,我是想女兒想瘋了。
張羊羊,男,1979年生于江蘇武進,現居常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作品散見《散文》《十月》等刊物,著有詩集《馬蘭謠》《綠手帕》,散文集《庭院》等。曾在本刊發表《平原故事》《鄉村肖像》等詩文,自2017年1期始在本刊撰寫“我的詞條”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