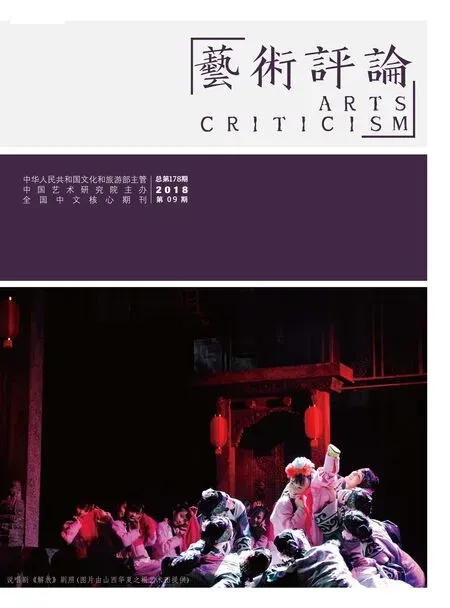從《幾乎標準》到《萬無一失》
宋建樹
如果說從2010年開始做《幾乎標準》《七倍于一拃》這類作品是以觀念之名來為自己身體的感覺加冕,那么完成于2014年的《一公里塔》《一米螺旋》和《等量齊觀》等就是通過聲東擊西的視角轉移去重構一個個約定俗成的概念,而2015年開始做的《八十一截》《三秒半落地》和《萬無一失》等作品則是肯定了一種基于失準和偏差的美學。
創作《幾乎標準》時,我憑雙眼一瞄去判定一段1米的長度,并用這段實際只有95.5厘米長的木條制作了一把“米尺”,雖然這把米尺并不準確,但在我的感覺里它卻是正確。這件作品打開了我信任自己的身體和感覺的大門,在這扇門后面,我看到的是一條驗證自身個體性存在的途徑。后來我又利用自己身體的一段長度做了另一件與尺寸有關的作品——《七倍于一拃》。用“拃”去測量長度本是古老而實用的方法,它和步測、肘測一樣都是源于身體,最后固定下來成為一種標準化的度量衡存在。有意思的是盡管不同的身體以及感覺是千差萬別的,但是刻度以一種高度抽象的形式符號統一了人們表述空間感的語言。我在《七倍于一拃》這件作品里以標準刻度的形象為載體,讓它去標榜一個個人的一拃被放大了七倍的結果,在那段刻度喪失了丈量功能的同時,留下的是一個說不清該屬于個人身體還是屬于群體經驗的符號。
這兩件貼墻展示的作品盡管在創作方法和作品觀念的對應上沒有問題,但是作品中立體感和雕塑感的缺失讓作為一個雕塑家的我還是有些許失落,后來我突然意識到每當我想到一段長度的時候,腦海里總是呈現出兩點之間一條直線的形象,這種扁平的思維顯然對我沒有幫助。只到某天我駕車在盤山公路上繞行的時候才豁然開朗:當直線運動變成曲線的運動時,空間不是就頓時展開了嗎?基于這個想法進行實踐,我將一段長度為1000米的鋼筋條盤繞成一座3米高的圓錐形鐵塔,算是我為一公里的長度所做的紀念碑。而將鋼筋盤成一個圓片的《一米螺旋》則是相對于《一公里塔》所做的“降維”處理,當視角又轉向二維的時候,我發現這條鋼筋的絕對長度在平面的語言上失去了意義,反而是有如年輪一般不斷疊加的圈數形成了其語言特征,于是我也就自然地放棄了用鋼筋總長的設定去結束這件作品,而是選擇在其直徑達到一米時與之了斷。《等量齊觀》則是將1000根1米長的鋼筋棍捆成一個近乎于實心的圓柱體,并緊密地焊接在一起,最后再對兩端的平面進行滿焊、打磨、拋光的處理。這個看起來平均、有序、統一且富有強制力的物體卻是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和時間才完成的,其實如果是為了得到這個簡單的造型,更多方便的辦法都可以用來滿足視覺要求,甚至還能得到更為精致的效果。但我認為對一個造物者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得到一個存在的事實而不是事實的影子。
幾年之后在重新審視《幾乎標準》時我總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我試圖去尋找一個答案——究竟要經過多少次失敗,我的身體感知才能和那個公共標準發生一次完美的吻合?實踐的結果是在經過80次或長或短的目測失敗后,終于在第81次實現了目測出幾乎是準確一米(誤差小于1mm)的目標。當我把這81節記錄自己目測結果的鐵管擺在一起的時候,這些長長短短的“錯誤”排列成了一首詩般的結構。我將這件作品稱為《八十一截》,也是因為這個數字結果太有超乎想象的戲劇性。這件作品開始使我意識到正是由于所有偏差和錯誤的存在才構成了美學,試想如果這個世界皆由標準模版構成,那也就沒有了所謂的風格、個性、奇葩和偶發的妙趣。這世上從來就沒有兩條一模一樣的拋物軌跡,也不存在任何一條相較其他而更加完美的拋物線,每一條拋物線都以其自身獨有的弧度和張力詮釋出了完美。這個想法后來落實在《三秒半落地》這件作品上,十多根隨機形成弧線的鋼筋各自優美而獨立的在空間中交錯,共同構成了一個虛無空幻的場域。《萬無一失》則是和《八十一截》異曲同工,通過偏離靶心的“失準”印記形成的一幅圖像。或許“這此一念與彼一念間”——用批評家黃碧赫的話說——“既不涉及現實的標準,亦無關于肉體帶來的偏差,藝術家以它們作為修辭,試圖占據的恰是二者間那個可以使‘美學’發生的精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