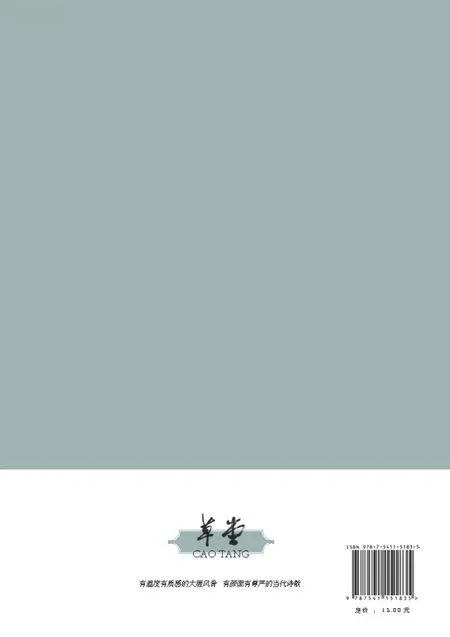青幕垂蕩的地平線 (組詩(shī))
2018-11-13 14:12:16王子瓜
草堂
2018年11期
關(guān)鍵詞:生活
王子瓜
總督府
早晨,海鷗送來一副冰耳墜,
兩人步行來到這兒。
售票廳負(fù)責(zé)復(fù)制游客,
府中擺設(shè)負(fù)責(zé)復(fù)制游客的感受。
并非一時(shí)的罪惡,便可造就
這些玲瓏的廳堂、椅柜和燈盞。
碉堡的遺址旁邊有個(gè)煉金師
這么說:為了煉成這座童話,
多少個(gè)世紀(jì)被我耗費(fèi),成為灰燼?
那兩人聽了,點(diǎn)點(diǎn)頭。一個(gè)說
原來這兒就是我小時(shí)玩樂的地方。
一個(gè)說就是在這兒,我曾死去。
去 信
剃須刀,像幾個(gè)朋友消失在雨中,
雨聲充滿了我和他們的窗戶。
醒,總是太遲,
總是救不起昨夜嘶鳴的垂柳。
這天氣不如繼續(xù)睡在家中,
胡亂去夢(mèng),這些年遺失的東西
都好端端地,在外面的世界四處躲著。
不要出門去吧,路邊的小作坊
總是失靈,整日
往外傾吐粉末和刨木卷。
我知道沒有一件家具誕生在里面。
生活給出的計(jì)算題我曾多么擅長(zhǎng),
如今總是解錯(cuò)。
所以如今這一顆才是真的。
像重要的小魚干,奔跑的每一秒
都令它掉落一點(diǎn)點(diǎn)。
下方是生活的出題機(jī):
新的大海,愿你別習(xí)慣。
黃昏劇場(chǎng)
傍晚,在一家餐廳里我們告別。
你們告別,而我
迷路到窗外去了。云霞上,
那孩子成桶地?fù)]霍著顏料,
街旁小樹幾乎要拽不住自己的影子。
現(xiàn)在,這出戲在按捺著高潮,
變暗的一切,反而使光線更加清楚。
哦,神的貓頭鷹,
已從那片醞釀里起飛了嗎?
東面樂海正在浪的高音上戛然而止。
青幕垂蕩的地平線,一邊
是暴怒的落日燃燒著,
呵退了周圍前來攙扶的夜;
一邊是年輕的樓廈,昂頭,不語,
只有純粹的金色,炫耀在胸前。……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風(fēng)流一代·經(jīng)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xué)·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xué)·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