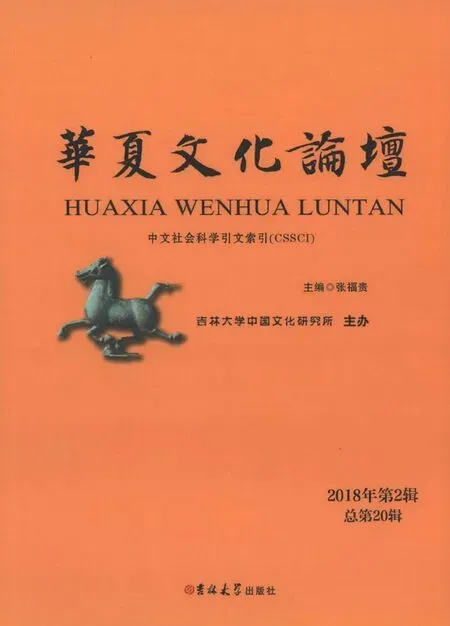長安文化對賈平凹文學創作的影響機制
韓 蕊 閻玥蓉
【內容提要】賈平凹的文學創作在很大程度上與其生活的這塊土地息息相關,長安文化不僅極大地促成了賈平凹文化性格的形成,而且深刻地影響甚至主宰著他的藝術創作的審美品格。賈作在呈現出強烈地域風格的同時,又以其獨特性豐富和發展了長安文化。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安文化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最發達的地域性文化,它包含著時空兩個方面的內容,既指這一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對于生活在陜西關中地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又指周秦漢唐包括以后宋元明清各時代對此文化的沿革與發展。長安文化具體的地域范圍可以分為核心發生區和輻射傳播區,核心發生區主要是在關中平原地帶,輻射傳播區指直接受長安文化影響以及與其他地區文化傳播交流的地區,即北起渭北高原,南至秦巴山區,東起洛陽,西至河西走廊的廣大地區。賈平凹成年定居的西安和幼年成長的商洛便分別位于長安文化的核心發生區和輻射傳播區。
一、塑形作家地域文化性格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形成的歷史遺存、文化形態、社會習俗、生產生活方式等,它由生活在該地域的人創造,同時它又影響著該地域內人的生存和發展、思想和個性。同樣,長安文化對于陜西人尤其是關中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幾乎不可回避的影響,而對于藝術家則不僅僅是人格的塑造,更借助其地域性格、思維模式及審美觀念而影響他們的藝術創作。所以,研究藝術家及其創作,不可忽略地域文化對其文化品格生成和發展淵源的探析。
長安文化對于定居該地區人的影響首先是地理位置造成的。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優勢使長安成為建都首選,至尊位置、富足生活一方面促成了關中人的大氣自信和勤勞進取,同時也容易使他們虛榮自負和消極守成。長安文化的源頭是秦漢,漢書所概括的“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正是陜西黃土文明最基本的特征。這一特征對關中人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行為方式和文化觀念具有潛移默化地模式化塑型作用。
長安文化有積極進取的一面。秦人頑強百折不撓,幾代人薪火相傳最終統一中國是這種頑強與堅持的最好證明。秦人求變機動靈活,秦能夠成為雄踞一方的霸主,改革與變通是其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國策,秦孝公的商鞅變法、軍功制度、爵位制等打破了僵化的舊等級,極大地激勵和提高了了秦人的生產力和戰斗力。秦人包容海納百川,秦穆公用五張羊皮換來百里奚,李斯一封《諫逐客書》便阻止了秦國的排外運動,而包容是自身強大的表現。秦人的這些特征在后來漫長歲月里的不斷積累,深深銘刻于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的精神中,流淌在他們的血液里。特別是接納包容的思想在漢唐時更加發揚光大,長安成為多民族甚至外域民族的聚集中心,唐時突厥、吐蕃、吐谷渾、黨項、高麗、新羅、波斯、大食、日本、印度等等,都有數字可觀的人口落戶長安,他們共同創建了隋唐時最先進的長安文化。
長安文化又有著濃郁的悲劇因素。凡事都有它的兩面,秦人的上述美德發展到極致就容易走向它始料未及的反面,務實使得人們在權衡利弊時可以舍小而取大,但也容易讓人急功近利,目光短淺,堅持到底的頑強也容易發展成為固執。特別是隨著天佑元年(904)年,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失去天下政治中心的地位,長安文化日益進入衰落階段。地勢險要的關中,只能維持西北重鎮的形象,以守為攻的戰略決策和被動防范的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磨平了秦人當初橫掃六國時的鋒芒和銳氣,同時埋下了閉塞與守成的性格種子,秦人的心理建構再次受到了極大的挫傷,變得日益收縮和保守。
長安文化深刻地影響著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更浸潤著與這塊土地血脈相連的藝術家。相較于普通大眾,藝術家通常比較敏感,他們對于自己生活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感受更為細膩深刻。賈平凹的故鄉商洛從歷史地理上看,西漢時屬弘農郡東漢時屬京兆尹,明清時屬西安府,民國初年劃歸關中道,可謂歷來是京畿毗鄰之地,為“長安文化”的輻射地帶。加之歷史上“商山四皓”,其民俗民風本質上是“長安文化”的衍生。
賈平凹性格內向而勤奮執著。作家早年沉默少言,但內心世界卻豐富多彩,而恰是這種向內心的回歸,發展了他細膩的觀察力和敏銳的感受力,不善言說的思想卻可用手中的筆盡情揮灑。賈平凹高興得時而“張狂”:“知我德行的人說我是:在生活里膽怯,卑微,伏低伏小,在作品里卻放肆,自在,爬高涉險,是個矛盾人。想一想,也是的。……我恐怕命定的就是文人,既然是文人,寫文章的規律是要張揚升騰,當然是老虎在山上就發兇發威,而不寫文章了,人就是鳳凰落架,必定不如雞的。”就自己的執著,賈平凹曾說“我這人有韌勁,小時候到山里砍柴,擔一擔柴走山路,很沉重,只能在某個特定的地方才能休息。我人小,咬牙跟著大人堅持到休息的地方。這樣,慢慢有了意志和毅力,是自己做事一定達到目的。”陜西俗語“不怕慢,單怕站”就是強調做事情一定要堅持,賈平凹深得其中奧妙,有著超乎常人的近乎癡狂的進取精神。寫作初期,他給自己規定每月必須寫作并寄出一定數量的文稿,這種幾乎是違背文學創作規律的方式硬是成全了他。很多和賈同時出名的寫作者,大都已經放下手中的筆或轉業干其他的了,像賈這樣一直在文壇上耕耘并新作不斷的為數不多。
陜西人倔強,自己認準的事一條道走到黑,旁人的議論或非議不產生任何作用,甚至會激發被議論者朝他們所說的相反方向前行。“不管外界如何議論紛紛,我的目標已相當清楚,我知道了我應該怎么辦,……當時文學界在對我近兩年所寫的散文作評價時說‘賈平凹的散文是可以留下來的,小說則是二流、三流的。這就是說,我的散文比小說好。這話倒使我甚為不服:我寫散文,是我暫時不寫小說后寫的,你說散文好,我偏不寫散文了,你說小說不好,我偏再寫寫讓你看!”結果賈氏小說連連獲獎,特別是《浮躁》、《廢都》、《秦腔》和《古爐》等奠定了作家在當代小說界的中堅地位。
生活中的賈平凹伏低伏小,創作時卻恣肆張揚創新多變求全兼擅,且詩文書畫均有涉獵,這或許正是對現實人格的一種互補吧。賈平凹的文筆徜徉于鄉村和城市,作家的靈魂更是徘徊于質樸與繁華、落后于現代之間。從散文到小說,從中短篇到長篇,從尋根的一味贊美到返觀鄉土的內省批評,作家對于城鄉的情感一直在變化之中。創作風格前后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早期基本遵循傳統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為目的,以編織跌宕起伏的情節取勝,而寫作內容基本是對于現實生活的直錄。《商州初錄》系列盡顯作家對于自己家鄉的熱愛與贊美之情,《浮躁》、《雞窩洼里的,人家》、《臘月·正月》等緊扣時代的鼓點為改革加油。由《廢都》開始作家將筆觸從對社會生活、時代變遷的記錄轉向了人物內心,關注藝術形象的靈魂及精神世界成為此后作品的一大亮點,至《秦腔》基本形成了獨特的賈氏風格。《高興》、《古爐》均采取了這種“密實流年式的敘寫”,即作品沒有明顯的情節線索,敘事結構為網狀連接,在有限的時間段內書寫無盡的人生悲歡,并在這悲喜劇中凸顯人物性格,進而表達作家對于人生對生活的感受與看法。
與西安40年的相濡以沫日夜浸淫,賈平凹已經完全融入到長安文化之中。如作家自己所言對于西安的歸屬感:“生不在此,但死必在此,當百年之后軀體焚燒于火葬場,我的靈魂隨同黑煙爬出了高高的煙囪,我也會變成一朵云游蕩在這座城的上空的。”
二、浸釀文本的藝術審美品格
地域文化對于普通人有性格塑形作用,對于藝術家則還會影響甚至主宰其藝術創作,長安文化深深地滲透和浸潤著賈平凹的文學創作。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這段話可以說是秦地作家的創作準則和座右銘。看重文學的社會功用價值,擁有知識分子的自覺擔當是陜西作家的共同特征,作為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寫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頭的書”(陳忠實語)是他們的一致追求。
陜西當代文學有明顯的“史詩情結”。《保衛延安》是當代最早被指認為“史詩”的長篇小說;《創業史》被直接定位為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史詩、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史詩;《平凡的世界》被譽為“史與詩的恢宏畫卷”;《白鹿原》的評論更是高頻率地使用了史詩或類似意指的稱謂。可以說在當代文學史上,很難找到另一個區域作家群或創作流派,如陜西作家群這般,如此地一致地在創作中追求雄渾的史詩效果,而其史詩般“宏大”“雄渾”“深刻”的美學標志則可在長安文化傳統中尋到根源。賈平凹的創作同樣史詩情結濃厚,從《浮躁》對改革年代人們心理的準確把握,到《廢都》里知識分子頹廢世紀末情緒的展示,包括穿插其間反映鄉鎮企業的《高老莊》、哀吟城中村改造的《土門》、以上訪為視角揭示農民問題的《帶燈》到反映農民難娶拐賣婦女的《極花》等等,賈平凹正如他自己所說要為時代做如實的記錄。從鄉村到城市,作家的筆觸所及無不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其間也無不滲透著作家自己濃重的憂患意識。尤其是他的集大成之作《秦腔》,以清風街一年間的敘事時間展現農村改革十年來的生活變化,作家自敘是在為自己的家鄉棣花鎮作傳,但其間發生的種種正匯聚成一部當代中國鄉村的轉型時代變遷史。
陜西當代作家還多具有濃厚的悲劇情結。“陜西作家群多以樸實、悲涼的風格見長— —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高健群……就像貧瘠、堅韌的黃土高原一樣。”論及賈平凹的小說,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擔當意識、老莊神秘文化及無為出世思想、佛家普渡眾生的曠達慈悲情懷,讀者均可在其作品中有深刻體驗。而在這矛盾復雜多樣文化雜糅的意識形態之下,起主宰作用的是一種深切的悲劇情結,它彌漫于文本的字里行間,極大地影響著作家的文學理念和創作心態。通觀賈氏小說,其中片段、細節或許是輕松甚至喜劇性的,但閱讀結束掩卷沉思,則總是讓我們感受到生活的諸多無奈與幾許沉重。
《浮躁》、《廢都》和《秦腔》在賈氏文學創作實績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綜合考量此三部作品,其中蘊含的悲劇線索最為明確,作家的悲劇情結也得以最大程度的彰顯。對于《浮躁》,作家坦言“我試圖表現中國當代社會的時代情緒,力圖寫出歷史陣痛的悲哀與信念。”按照馬克思文藝理論,悲劇產生于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沖突。金狗發財致富、出人頭地的要求是符合改革發展大潮的,但卻不被當時的社會現實所允許。悲劇中具體人物的實踐行為有一定的超前性,但卻因為缺少現實根基而遭致失敗,其悲劇原因不能僅僅歸于主人公自身的過失或性格缺陷等主觀方面,而應考察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去尋找。金狗的悲劇具有深廣的社會歷史內涵,這一改革時代的社會悲劇沖突具有對抗性、激烈性和不可調和性。《廢都》是作家自稱“安妥靈魂”之作,文本基調仍然是悲涼的。分析莊之蝶的悲劇成因,內心欲望的膨脹難辭其咎。其它的西京名人亦是結局慘淡,作為人類道義承擔者的知識分子,在《廢都》中競相沉淪墮落。如果說《浮躁》中,金狗、雷大空的悲劇命運還可以歸咎于時代與社會的不合理因素,莊之蝶們則更大程度上是自我原因造成的。事物的發展變化中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主體我出了問題,而改變自我比改造外界的難度要大得多。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較之于《浮躁》的悲哀,《廢都》的悲劇意味更為濃厚,謂之徹骨的悲涼。《秦腔》里現代化的建設需求使土地在一寸寸地減少,伴隨著土地的消失是勞動力的大量流散,只剩老人孩子的鄉村格外凄涼。從上世紀二十年代登上文壇的鄉土文學,當下卻面臨著“無土”的危機。鄉村不成其為鄉村,家園已經物變人非,作家在《〈秦腔〉后記》的結尾長嘆“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所有文字盡顯作家對于農民生存狀態的悲觀與憂慮。此時的人物生存已經擺脫了《浮躁》中民生的物質層面,生活已經充分改善甚至達到小康的人們,精神支柱的匱乏與缺失才是最嚴重的,他們的靈魂無以支撐。“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土地的消失改變了農民的身份與生活方式,秦腔的衰落更是抽掉了他們人生全部的情感寄托。
三部作品從失敗退回、無路可走到徹底絕望,深深的悲劇感貫穿始終并愈演愈烈。其實不僅僅是這三部經典性作品,賈氏其他小說也都蘊含著這種濃郁的挽歌情結和深重的悲劇底蘊。《古堡》中的淡薄世情及神秘白麝對鄉民的潛在威脅,《白朗》近乎史詩的英雄悲歌,《白夜》中夜郎的尋尋覓覓、《高老莊》里子路的歸來離去、《土門》中仁厚村的最終拆遷、《極花》中蝴蝶的重回拐賣村無不透露出這種悲涼的氣息。在《秦腔》后記中賈說“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正是這種作家的使命感使得悲天憫人的賈平凹創作中總是彌漫著揮之不去的悲劇情結,他自己曾多次在各類訪談中說到“人生很少有歡樂”、“人生就是痛苦的、苦難的”。評論家閻鋼曾在論及賈平凹時說,“平凹自己并沒有把世事看透,所以他悲從中來,靈魂始終不得安寧,他悲天憫人,卻又無法救苦救難。”其實未必是沒有看透,更多的是作家的悲憫與擔當讓他必須拿起筆做必須的抗爭。關于中國文學中的悲劇觀,胡適曾有論述:“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結局。……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并進而指出“承認世上的人事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會不良使人消磨志氣、墮落人格,陷入罪惡不能自脫。有這種悲劇的觀念,故能發生各種思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這種觀念乃是醫治我們中國那種說謊作偽、思想淺薄的文學的絕妙圣藥。”應該說,賈平凹的小說創作或許就是這種圣藥。
三、賈作對長安文化的豐富與發展
地域文化在潛移默化地塑造地域內人群性格和文化觀念的同時,也喚起了地域人群內在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對于豐富和發展該地域文化具有強大的反作用力,知識分子更是如此。除了像其他人一樣接受與生俱來的集體無意識,作家超越了自身的一己局限,科學正確地看到終生氤氳的長安文化中的優長和劣勢,并在自己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中盡可能地揚長矯短。賈平凹青少年時期秉承秦人內向性格沉默訥言,經過幾十年的砥礪磨練,如今的作家口若懸河,口語和他的小說語言一樣豐富形象引人入勝。不僅如此,賈平凹還以自己豐厚的創作實績為中國當代文學做出了極大貢獻,向更廣闊的地域傳播著長安文化,而在進行這種傳播的同時,他又以自己創作的獨特個性化藝術風格豐富和發展著長安文化,給它注入更加強勁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哈里斯認為“文化是指特定數量的人被模式化了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行為方式,個性也是指模式化了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行為方式,但其重點是在有關個人的方面。”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固然不錯,傳統的人文積淀也十分重要,而由于作家個性不同,才華不一,又可以將“一方水土”寫出氣象萬千的境界。在擁有陜西文學的史詩品格、悲劇情結等共同特征的同時,賈平凹的創作有著鮮明的個性風格。
賈平凹是當代陜西作家最多產的,藝術風格也是最多變的,早期作品呈現出輕盈靈動——如《商州三錄》文筆的雋秀跳躍很有孫犁散文的韻味,《商州》徜徉于戀鄉思親的筆墨頗似沈從文《邊城》的淡雅清新。而隨著作家定居西安日久,為長安文化的厚重渾樸吸引愈深時,他的寫作風格也逐漸地發生了變化。對比早期“商州”系列初入文壇的血氣方剛與澄澈單純,中期《廢都》、《秦腔》滿眼的世事滄桑與沉挫悲涼,至《高興》又轉化為歷盡大悲后的向世慈容,《古爐》則超越了上幾部的記錄時代現象,從人性角度追索底層鄉村掀起“文革”的成因,是作家最富哲思使人震撼和深省的作品。
賈平凹的創作還有一個足以區分于他人的唯美特征,即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呈現出精神意象性特點。在賈氏散文中,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被賦予了獨特的生命精神。在小說創作上,對精神的推崇還使賈氏非常注重作品精神維度和精神細節,通過思考與頓悟而達到對生命精神的理解,土匪系列的《白朗》、《晚雨》等均屬此類創作。至于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賈平凹早期接受和展現的是其中美的一面,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體驗的加深,作家漸漸不滿足于單純、熱情的肯定、贊美,而轉向對沉積在國民性中傳統文化的負面的冷峻揭示與理性思考,《古堡》《古爐》便是其代表作品。賈作的意象世界紛繁復雜又自成系統,是一個完整、自足的意象群落,其中寄予著作家對人生、宇宙的思考,有對美的謳歌,也有對丑的揭示,有對傳統的反思,也有對現代性的探求。早期《天狗》中天狗和師娘在月光朦朧的江邊充滿愛戀的對唱,《人極》中光子與拉毛那充滿古典意味的情誼,《商州》、《浮躁》中美麗的州河風景,都構成了詩情畫意的意境美。后期《秦腔》、《古爐》更是以意象取勝,至《古爐》里面的狗尿苔、蠶婆、善人等本身就是意象式的人物。
賈平凹對于道家精神的繼承也是極富個性的。作家輕靈飄逸的文筆正呼應著高古、空靈、自在的道家出世情懷。具體表現便是對于特異人物與神秘文化的信奉與書寫,這也是他被稱為“鬼才”的重要原因。作家或將自己的道家思想直接移植到小說主人公身上,甚至用一些魔幻手法富于人物超乎常人的能力,如引生可看見別人頭上生命光焰、狗尿苔懂獸語能聞見災難的味道等;或多由一些溝通陰陽的老年人特別是老太太形象來完成,《古堡》、《白夜》、《廢都》、《老生》、《極花》中均有此類人物。關于賈氏作品中的神秘文化已有不少專論,他的泛神論也是有目共睹的。“楚地好巫風”,泛神化意識與自然崇拜對于來自陜南的賈平凹影響極深,中華民族的精英文化和民間的信仰文化在此交匯沉積,形成作家深厚的文化心理原型。
綜上可以說,賈平凹創作改進了于長安文化“重質輕文”的價值取向。農耕文化特質使人們愿意依靠經驗而不愿創新冒險,導致了穩定持重的心理趨向,由此衍生的價值觀念的影響加深了“重質輕文”的地域特色,進而促成了陜西文學“重質輕文”傾向,而民風的“尚質”、“不善淫巧”也對藝術風格產生影響。無論文學創作還是其他藝術如雕塑、書法、繪畫等等,樸拙渾厚豪邁大氣中似乎都缺少細膩委婉和精雕細鑿,重質務實的文化取向必然導致對形式與外表的忽略。賈平凹的文學世界使他迥異于同時代其他作家,尤其是對比于另外兩位陜西籍作家路遙的苦難奮進和陳忠實的平穩敦厚,賈氏更顯得灑脫靈動,輕松率意。相較于《平凡的世界》的昂揚激情與《白鹿原》的滄桑厚重,人們欣賞賈氏作品的著重點也在他的通脫靈秀。相對于其他兩位作家的陽剛之氣,賈作多了一層進退有度、取舍悠游的自由與靈活,陽剛與陰柔在作家本人和他的創作中達到和諧的統一。可以說,賈平凹以自己具有獨創意義的寫作不僅改變了陜西文學的傳統面貌,豐富了長安文化的深厚內蘊,也改善了長安文化厚重有余靈秀不足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