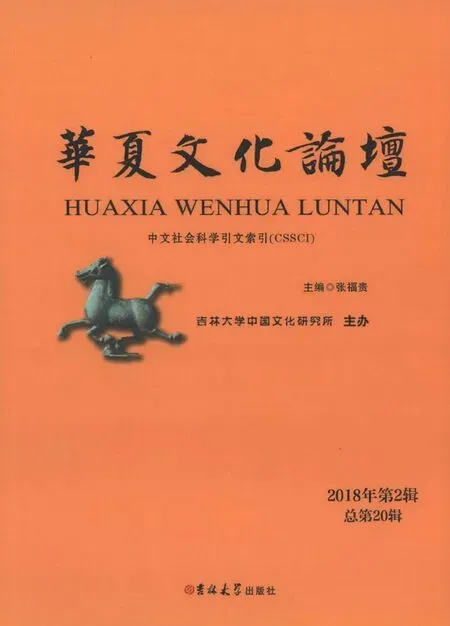《申報(bào)》(上海版)所載的歐陽(yáng)予倩佚文
李 斌
【內(nèi)容提要】歐陽(yáng)予倩在《申報(bào)》(上海版)發(fā)表過(guò)8篇作品:《年先生》《演劇閑談》《九江的乞兒》《介紹日本的歌舞伎》《民國(guó)十六年的電影界》《藝術(shù)與革命》《〈清明時(shí)節(jié)〉的演員》《話劇年的喜與懼》,時(shí)間從1924年到1937年,體裁有小說(shuō)、散文、文論,內(nèi)容涉及過(guò)新年、兒童乞討,是作者對(duì)民族命運(yùn)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思考,體現(xiàn)出作者的人道主義情懷;此外有對(duì)于連臺(tái)本戲與長(zhǎng)戲的反思、對(duì)話劇年的冷靜思考、電影發(fā)展和演員表演的評(píng)論、對(duì)日本的歌舞伎介紹、藝術(shù)與革命關(guān)系的闡述等,是研究這一時(shí)期歐陽(yáng)予倩的文藝活動(dòng)和文藝觀念、中國(guó)戲劇和電影發(fā)展?fàn)顩r的重要文獻(xiàn)。
歐陽(yáng)予倩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卓越的戲劇家,有“南歐北梅”、“活的戲劇史”的美譽(yù),夏衍就曾如此評(píng)價(jià)歐陽(yáng)予倩:中國(guó)話劇“三位杰出的開(kāi)山祖”之一,“名副其實(shí)的戲劇大師”。然而與歐陽(yáng)予倩的藝術(shù)成就不相稱(chēng)的是,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歐陽(yáng)予倩的研究還不夠全面和深入,原因之一大概是資料的不全面。六卷本的《歐陽(yáng)予倩全集》(1990年版)是在短短的一年多時(shí)間里倉(cāng)促編就的,存在大量遺漏。學(xué)者蘇關(guān)鑫編撰的《歐陽(yáng)予倩研究資料》(1989年版)中有“歐陽(yáng)予倩著譯系年目錄”,對(duì)《歐陽(yáng)予倩全集》中所不曾收錄的文章有所提及;即便如此,該目錄仍然有很多遺漏——本文所論及的歐陽(yáng)予倩在《申報(bào)》(上海版)所發(fā)表的8篇作品,就是上述全集和目錄所忽視的。
這些作品有《年先生》《演劇閑談》《九江的乞兒》《介紹日本的歌舞伎》《民國(guó)十六年的電影界》《藝術(shù)與革命》《〈清明時(shí)節(jié)〉的演員》《話劇年的喜與懼》,發(fā)表時(shí)間從1924年到1937年,體裁有小說(shuō)、散文、文論,內(nèi)容涉及過(guò)新年、兒童乞討,是作者對(duì)民族命運(yùn)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思考,體現(xiàn)出作者的人道主義情懷;此外有對(duì)于連臺(tái)本戲與長(zhǎng)戲的反思、對(duì)話劇年的冷靜思考、電影發(fā)展和演員表演的評(píng)論、對(duì)日本的歌舞伎介紹、藝術(shù)與革命關(guān)系的闡述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jià)值。故而筆者在此將其主要內(nèi)容予以闡釋?zhuān)员阄覀儗?duì)這一時(shí)期歐陽(yáng)予倩的文藝活動(dòng)和文藝觀念、對(duì)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戲劇和電影的狀況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華民族的象征與新生:小說(shuō)《年先生》
《年先生》為新年而作,是一篇頗具想象力的小說(shuō),載于《申報(bào)》1924年1月1日。如同標(biāo)題所示,小說(shuō)把“年” 擬人化,稱(chēng)作“年先生”,把辭舊迎新習(xí)俗予以形象地展示。許多小孩子預(yù)備送走要去的年先生,盼望著新來(lái)的年先生,預(yù)備著接風(fēng)。新的年先生是個(gè)手提大鐵箱的美少年;大家猜測(cè)箱里必定有無(wú)數(shù)珍寶,于是擁擠著去奪取。其中有幾個(gè)孔武有力的孩子產(chǎn)生一種“極聰明的思想”,覺(jué)得參加搶奪的人太多,非殺掉些不可,便抽出兵刃動(dòng)手宰殺他人,其中也有不能動(dòng)手的,只好幫著扯腳使絆子。混鬧了一陣之后,受害的孩子不少,但是并沒(méi)有見(jiàn)后來(lái)者退卻,而那些動(dòng)手殺人的孩子們也都疲癃?dú)埣擦恕D晗壬戳诉@些混鬧后,便不耐煩地提著鐵箱走上了不曉得多高的扶梯。孩子們慌亂中顧不得追,只好讓年先生一步步向天上走去。有一個(gè)穿五色衣服的孩子名叫華堅(jiān),只有他一言不發(fā)地緊緊跟隨著年先生。地上許多孩子看見(jiàn)后,就對(duì)著華堅(jiān)或放箭或擲石,意在阻止他上進(jìn),“因?yàn)樗麄円詾樽柚箘e人的上進(jìn)是應(yīng)該的”。而華堅(jiān)一點(diǎn)也不怕,不知受了多少創(chuàng)傷才漸漸扒到了矢石不能到達(dá)的一層。然而年先生并不打算就這么把鐵箱給他,繼續(xù)前進(jìn),并以寒冷、烈火、怨鬼狐貍魑魅魍魎來(lái)考驗(yàn)華堅(jiān)。華堅(jiān)克服了種種艱險(xiǎn)之后終于得到了鐵箱,用腰間盤(pán)古氏遺傳下來(lái)的鋒芒久斂的斧頭,把鐵箱劈開(kāi)了。鐵箱中有說(shuō)不出名字的寶貝制作的一頂帽子、一件衣服,寶光燦爛,只是上面有無(wú)數(shù)極鋒利的刺。華堅(jiān)說(shuō):“這不是我個(gè)人獨(dú)占的。”刺馬上就消滅了。華堅(jiān)也不肯要這帽子和衣服,他提起斧頭割斷了線,登時(shí)許多寶貝向各方掉下去,照得世界到處光明,天亮了。
小說(shuō)《年先生》不僅富于想象力,把“年”擬人化,而且頗具寓意,社會(huì)黑暗、生活艱難的現(xiàn)實(shí)情形在作品中有所揭示,“年先生要?jiǎng)由砹耍麄儽銓⒃S多的笨重東西,如愁苦、悲哀、恐怖、凄慘、痛楚、窮困、煩惱之類(lèi)裝成一包一包,堆滿了舊年先生的一車(chē)”。作者把社會(huì)的黑暗與人們的苦難、把社會(huì)混亂與殺戮都寫(xiě)在了“辭舊迎新”的過(guò)程中:孩子們爭(zhēng)搶鐵箱過(guò)程中的殺戮,分明是在揭露20世紀(jì)初的軍閥混戰(zhàn);天亮、新年到來(lái)的結(jié)局,寄托著人們對(duì)于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華堅(jiān)與其他孩子們不同,他要鐵箱不是為了個(gè)人的獨(dú)占,而是為了大家都能夠得到光明。這個(gè)人物其實(shí)是中華民族的整體象征:他不畏各種艱險(xiǎn),“不信有東西能夠屈服他”,不肯獨(dú)占寶物而要讓世界到處光明,“華堅(jiān)吃盡了辛苦,一無(wú)所得,回顧他自己身上變了太陽(yáng)一樣,比什么寶貝還亮”,從他身上我們感受到的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前進(jìn)的精神;小說(shuō)中的幾處用語(yǔ)也揭示了這一點(diǎn):“那華堅(jiān)原本是數(shù)千年遺傳下來(lái)的”,華堅(jiān)腰間的斧頭則是“盤(pán)古氏遺傳下來(lái)的一把鋒芒久斂的斧頭”,這都和中華民族有關(guān)。
人道主義情懷:《九江的乞兒》
1926年5月下旬,應(yīng)漢口戲臺(tái)的聘請(qǐng),歐陽(yáng)予倩去漢口演出了兩個(gè)月。《九江的乞兒》一文,就是歐陽(yáng)予倩從上海去漢口途中,5月24日在九江鄱陽(yáng)船上時(shí)所作,發(fā)表于6月4日《申報(bào)》。歐陽(yáng)予倩在船上吃過(guò)晚飯后,在船艙枯坐時(shí),來(lái)了一個(gè)小叫化子討錢(qián),卻沒(méi)人理他,然后又來(lái)了好幾個(gè)討飯的。歐陽(yáng)予倩仔細(xì)端詳小乞丐,“不見(jiàn)得就是窮乞相”,但是小乞丐的聲音“具有非常的魔力,又嬌嫩,又清脆,又甜蜜,又可憐”,乞討聲引起了歐陽(yáng)予倩無(wú)窮的感慨:
若是將他洗洗澡,穿上兩件干凈稱(chēng)身的衣裳,在人家廳堂里,誰(shuí)不說(shuō)是個(gè)小少爺?若是聽(tīng)他天真爛漫的唱支把愛(ài)國(guó)歌,誰(shuí)也對(duì)他有些將來(lái)的期許。如今他這樣討飯將來(lái)又怎么樣呢?他的父母是個(gè)不成器的隨落者?或是個(gè)受難者?不得而知。只是在這乞兒的本身,就算是長(zhǎng)大成人,又安知其不為餓殍?又安知其不為盜賊?又安知其不為最苦的奴隸?或者遇著異數(shù),成功一個(gè)有用的人才也未可知——這不過(guò)我對(duì)他的期望,其實(shí)因境遇而毀滅的人才又豈在少數(shù)。
歐陽(yáng)予倩叫茶房開(kāi)門(mén),一面打算拿幾個(gè)錢(qián)給小乞丐,一面想著貧民到底怎么救濟(jì),想到歐洲戰(zhàn)爭(zhēng),想到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一時(shí)同降乩似的,克納滿沙、麥克唐納、威爾遜、馬克司、李寧、托爾斯泰一類(lèi)的人物,亂七八糟都到了眼前”。然而歐陽(yáng)予倩取了錢(qián)追出去時(shí),小乞丐已經(jīng)不見(jiàn)了,“只他那代表世界可憐人的聲音,深深的印在我的心曲”,作者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涌將出來(lái)。
20世紀(jì)20年代的中國(guó),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歐陽(yáng)予倩對(duì)小乞丐給予了無(wú)限的同情,并且生發(fā)感慨,想到貧民如何救濟(jì),想到歐洲戰(zhàn)爭(zhēng)和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這篇散文體現(xiàn)了歐陽(yáng)予倩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懷,這和他的劇作如《車(chē)夫之家》《同住的三家人》、小說(shuō)《斷手》《三歲的童養(yǎng)媳》《傷兵的夢(mèng)》是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的。
對(duì)連臺(tái)本戲、長(zhǎng)戲的反思
1923年10月16日的夜戲,新舞臺(tái)始演初集《徽欽二帝》(歐陽(yáng)予倩、汪優(yōu)游、沈冰血合編),6時(shí)3刻登場(chǎng),全劇凡演8小時(shí)之久,張?jiān)峦わ椈兆冢w君玉飾劉妃,趙文連飾明達(dá)皇后,歐陽(yáng)予倩飾崔妃。1924年1月1日夜戲,新舞臺(tái)始演二集《徽欽二帝》,趙君玉飾顏王妃蕭氏,歐陽(yáng)予倩飾李師師,潘月樵飾燕王耶律淳,張?jiān)峦わ椝位兆冢脑律猴椡灒茗P文飾李邦彥。此后,歐陽(yáng)予倩還參加了三、四、五集的演出。《演劇閑談》載于《申報(bào)》1924年1月31日增刊3版,正值《徽欽二帝》演到第二集,歐陽(yáng)予倩的這篇文章談?wù)摰木褪沁B臺(tái)本戲《徽欽二帝》。
歐陽(yáng)予倩首先對(duì)劇本進(jìn)行了評(píng)介,肯定了汪優(yōu)游為編《徽欽二帝》考查了無(wú)數(shù)的書(shū),其中的事實(shí)都很有根據(jù);雖然是戲曲,但是在某些方面彌補(bǔ)了觀眾匱乏的歷史知識(shí)。然而汪優(yōu)游編《徽欽二帝》是采取作長(zhǎng)篇章回小說(shuō)的方法,是連臺(tái)本,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失了藝術(shù)的價(jià)值”,“我是從來(lái)不贊成連臺(tái)本戲的”。不過(guò)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不能怪汪優(yōu)游,因?yàn)榇蠹叶颊J(rèn)為連臺(tái)戲可以賣(mài)錢(qián)。雖然幾個(gè)月來(lái)新舞臺(tái)的生意全靠《徽欽二帝》支持,不過(guò)并沒(méi)有賣(mài)著多錢(qián);大家分析原因,以為是戲情太深,普通人不很了解,所以不能像《貍貓換太子》那樣叫座。
歐陽(yáng)予倩對(duì)于自己在《徽欽二帝》中表演的評(píng)價(jià)很謙虛:“毫沒(méi)有什么貢獻(xiàn),什么新歌新舞,雖然說(shuō)得好聽(tīng),老實(shí)說(shuō)都是不成器的。不過(guò)我以為不管對(duì)不對(duì),不妨盡量試驗(yàn),在試驗(yàn)中千萬(wàn)不可自己滿足罷了。”實(shí)際上《申報(bào)》的評(píng)論積極肯定了歐陽(yáng)予倩的藝術(shù)貢獻(xiàn):“歐陽(yáng)予倩飾崔妃,唱做俱佳,有佳人剪特丹舞一段,系八人共舞,由予倩領(lǐng)首,舞態(tài)絕美。予倩于中外歌舞素多研究,是劇亦殊費(fèi)心力不少。”
觀眾往往被罵“盲從”,歐陽(yáng)予倩從觀眾的盲從說(shuō)到研究者的盲從。歐陽(yáng)予倩“深信非有建設(shè)之才,不能妄談革命,破壞須用著建設(shè)的精神”。歐陽(yáng)予倩做了自我反思,從前研究戲劇完全是一味盲從,到了前四年進(jìn)入了極端懷疑的時(shí)候,如今方漸漸有具體的主張。歐陽(yáng)予倩自認(rèn)為研究還沒(méi)有十分徹底,因此不敢貿(mào)然發(fā)表自己的主張。歐陽(yáng)予倩還反思說(shuō),如今研究戲劇者,或隨便唱著玩玩,或借外國(guó)名家自重,這都不是根本辦法;他批評(píng)自己從前也曾如此,希望大家不上這樣的當(dāng)。歐陽(yáng)予倩批評(píng)說(shuō),戲劇研究者本有引導(dǎo)觀眾的責(zé)任,如果徒然指責(zé)觀眾盲從、程度不夠,也是不對(duì)的。
戲一唱就長(zhǎng)達(dá)六七個(gè)鐘頭,歐陽(yáng)予倩指出,“唱的與看的都極疲倦,這一層很容易改良”,他對(duì)戲“非長(zhǎng)不足以賣(mài)錢(qián)”的說(shuō)法予以質(zhì)疑。近年因?yàn)榉桥判聭虿荒苜u(mài)錢(qián)吃飯,因此唱戲的漸能服從排練,然而他們決不愿為長(zhǎng)時(shí)間的演習(xí),“唱白表情,尤不肯加以錘煉”,歐陽(yáng)予倩提出要求,深愿大家多多努力。
對(duì)話劇年的冷靜思考
除了對(duì)戲曲的關(guān)注,歐陽(yáng)予倩對(duì)話劇也有深入的看法。1937年2月21日出版的《申報(bào)周刊》2卷7期,刊有歐陽(yáng)予倩的《再談舊戲的改革》一文,該文在“本期要目”中出現(xiàn);然而正文中還有歐陽(yáng)予倩的另一篇文章《話劇年的喜與懼》,這篇文章并未出現(xiàn)在“本期要目”中,歐陽(yáng)予倩的名字也只是署在文章末尾,故而這篇文章鮮為讀者注意。
《話劇年的喜與懼》對(duì)1937年的話劇發(fā)展態(tài)勢(shì)進(jìn)行了冷靜的思考。1937年被認(rèn)為是話劇年,好幾個(gè)劇團(tuán)的公演都連賣(mài)滿座,劇場(chǎng)的經(jīng)理受到鼓舞,認(rèn)定話劇是可做的生意,預(yù)備組織新劇團(tuán)的也大有人在。歐陽(yáng)予倩指出,上海往往有“一窠蜂”的習(xí)慣,并以文明新戲?yàn)槔蠹襾?lái)注意:文明新戲受到歡迎時(shí),接二連三出了許多劇團(tuán),劇場(chǎng)老板從各方面敦促,趕排新戲,然而劇本缺乏,粗制濫造,專(zhuān)圖取巧,不認(rèn)真排練,全靠演員的小聰明多抓噱頭來(lái)迎合觀眾,最終弄得文明新戲驟然冷落。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目下話劇到了緊要的當(dāng)口,其命運(yùn)要看運(yùn)動(dòng)者的態(tài)度。話劇受到觀眾的歡迎,演技和舞臺(tái)處理的進(jìn)步、內(nèi)容接近現(xiàn)實(shí)都是重要原因;要求話劇基礎(chǔ)鞏固、向前發(fā)展,就要進(jìn)一步求內(nèi)容的充實(shí)、技術(shù)的更健全、更發(fā)達(dá)。
歐陽(yáng)予倩將文明新戲的墮落與1937年的話劇形勢(shì)聯(lián)系起來(lái)思考,指出文明新戲的衰敗原因,為話劇的發(fā)展指明了正確的途徑,尤其是關(guān)于劇本內(nèi)容充實(shí)、注重演技、舞臺(tái)處理等方面的強(qiáng)調(diào),至今不失積極的指導(dǎo)意義。
對(duì)日本歌舞伎的介紹
歐陽(yáng)予倩曾多次到過(guò)日本。1902年冬到1905年底曾在日本留學(xué),1906年和劉韻秋結(jié)婚3個(gè)月后,再次赴日留學(xué)。1910年,父親歐陽(yáng)自耘因患嚴(yán)重肺病赴東京就醫(yī),不幸去世,歐陽(yáng)予倩送父親靈柩回瀏陽(yáng)安葬。除了早期的留學(xué),歐陽(yáng)予倩后來(lái)還多次赴日本,如1919年夏,歐陽(yáng)予倩赴日本考察戲劇,為在南通開(kāi)辦伶工學(xué)社做準(zhǔn)備。這種經(jīng)歷,使得歐陽(yáng)予倩對(duì)于日本文化比較了解,《介紹日本的歌舞伎》發(fā)表于1926年9月6日《申報(bào)》。
文章的內(nèi)容正如題目所言,是對(duì)日本歌舞伎的介紹:包括歌舞伎的起源、發(fā)展歷史、音樂(lè)、布景、檢場(chǎng)、內(nèi)容與欣賞的原則等。
文章開(kāi)篇即把中國(guó)的舊戲與日本的歌舞伎進(jìn)行了比較,認(rèn)為二者“同是一種特殊的藝術(shù)”,并引用坪內(nèi)逍遙博士的話,指出歌舞伎有一種“無(wú)比類(lèi)的游戲的精神”,且變化無(wú)窮。
歌舞伎的發(fā)展歷史有些曲折和復(fù)雜:肇始于慶長(zhǎng)時(shí)代(明神宗時(shí)代),明治維新以后開(kāi)始盛行。最初是女子演,叫女子歌舞伎;以后加上男子與幼童,成了男女合演。寬永時(shí)代,政府以為有傷風(fēng)化而加以禁止,獨(dú)許可男子演唱,此后這種藝術(shù)就為男子獨(dú)占。帝國(guó)劇場(chǎng)成立之后,才養(yǎng)成了許多女優(yōu),并恢復(fù)了男女合演——從前不過(guò)是借兩性顛倒的扮裝來(lái)引發(fā)觀眾的好奇心,如今的男女合演完全照西洋的方法而更改,是男演男,女演女。歐陽(yáng)予倩再次將歌舞伎同我國(guó)的舊戲比較,指出男子演旦角成了數(shù)百年來(lái)的風(fēng)氣;帝國(guó)劇場(chǎng)雖出了幾個(gè)名女優(yōu),一般的人還是以為女子在舊戲中演旦角不如男子。
歌舞伎以歌舞為主,臺(tái)上的人只說(shuō)白、只舞不歌;歌的人坐在旁邊,只歌,不說(shuō)白不舞。歌舞伎的音樂(lè)以三弦為主,其余還有大鼓、小鼓、腰鼓、笛、銅鑼、拍板等。歌舞伎原本沒(méi)有布景,亨保年間(二百年前)大阪已經(jīng)有人在臺(tái)上掛幅山景,寶歷年間(百五十年前)已經(jīng)有人造轉(zhuǎn)臺(tái),所以舞臺(tái)裝飾頗為發(fā)達(dá)。歌舞伎在演的時(shí)候,檢場(chǎng)的當(dāng)場(chǎng)送椅子換衣裳,尤其是舞劇,舞子旁邊,有檢場(chǎng)的跟著,行動(dòng)飄忽;不像中國(guó)檢場(chǎng)的那樣怪形怪像,站在臺(tái)上。歌舞伎的內(nèi)容,切近情理的很多,然而荒唐無(wú)稽的也很不少。歐陽(yáng)予倩提醒,觀看日本的歌舞伎跟觀看中國(guó)的舊戲一樣,有的戲?qū)?瓷矶巫髋桑械膶?zhuān)聽(tīng)唱白,有的以架子見(jiàn)長(zhǎng),有的以武工為主,不能以寫(xiě)實(shí)的眼光去批評(píng)它,否則便大錯(cuò)特錯(cuò)了。
電影發(fā)展和演員表演的評(píng)論
歐陽(yáng)予倩不僅在戲劇方面成就卓越,在電影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現(xiàn)。1926年1月4日,歐陽(yáng)予倩結(jié)束了在丹桂第一臺(tái)的演出后,經(jīng)卜萬(wàn)蒼的介紹,加入新成立的民新影片公司。歐陽(yáng)予倩參加過(guò)電影演出,但是主要做編劇和導(dǎo)演。歐陽(yáng)予倩在其回憶錄《電影半路出家記》中,對(duì)自己在電影方面的經(jīng)歷有所介紹,但是并不具體,尤其是歐陽(yáng)予倩所寫(xiě)的不少影評(píng)和電影導(dǎo)演理論文章,如《影戲腳本采擇之標(biāo)準(zhǔn)》《談?wù)劜啡f(wàn)蒼》、《我對(duì)于中國(guó)影片的幾個(gè)感想》《忠告電影演員》《導(dǎo)演〈三年以后〉感言》《導(dǎo)演漫談》等,并沒(méi)有在回憶錄中提及,而學(xué)術(shù)界對(duì)這些文章也鮮有注意。歐陽(yáng)予倩在《申報(bào)》上也發(fā)表過(guò)電影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民國(guó)十六年的電影界》《〈清明時(shí)節(jié)〉的演員》。
《民國(guó)十六年的電影界》發(fā)表于1927年《申報(bào)》元旦增刊。歐陽(yáng)予倩肯定了電影的迅猛發(fā)展,“一日千里”,并且與小說(shuō)、詩(shī)文、雕刻、繪畫(huà)進(jìn)行了比較,認(rèn)為電影“力量強(qiáng)得多”。歐陽(yáng)予倩此前看到中國(guó)電影的快速進(jìn)步,以為不難追躡歐美之后;而近來(lái)卻覺(jué)得不然,歐美電影的進(jìn)步更加快速了。這自然也有中國(guó)電影界自身的缺點(diǎn)。比如,上海幾家大的影片公司有的只求出片快;有的面目看似莊嚴(yán),實(shí)際上行為兒戲;導(dǎo)演編劇、經(jīng)理、股東董事等之間的事權(quán)劃分不適;各家公司的經(jīng)濟(jì)力量都很薄弱,時(shí)局動(dòng)蕩,影片的銷(xiāo)路又少,于是過(guò)于追求營(yíng)利而不肯在影片上下工夫,導(dǎo)演、演員、攝影師,大致都怕費(fèi)事不太肯研究,公司也沒(méi)有力量讓他們?nèi)パ芯俊?duì)于民國(guó)十六年電影界的成績(jī)?nèi)绾危瑲W陽(yáng)予倩沒(méi)有下結(jié)論,但是他希望電影的成績(jī)不斷進(jìn)步,并且提出兩點(diǎn)建議:“一、獎(jiǎng)勵(lì)有意義的劇本及專(zhuān)門(mén)人才。二、各家比較有力的公司集合些資本,組織一所年限較長(zhǎng)、設(shè)備較完之藝術(shù),或退一步說(shuō),以技術(shù)為目的的電影學(xué)校。”這兩點(diǎn)意見(jiàn),著眼于編劇和電影專(zhuān)門(mén)人才的培養(yǎng),以及克服經(jīng)濟(jì)力量薄弱的困擾,設(shè)立以技術(shù)為目的的電影學(xué)校,在當(dāng)時(shí)是很有指導(dǎo)意義的。
1936年12月23日,明星影片公司攝制、歐陽(yáng)予倩導(dǎo)演的影片《清明時(shí)節(jié)》,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映。《〈清明時(shí)節(jié)〉的演員》發(fā)表于公映的前一天即12月22日。歐陽(yáng)予倩很注重演員的表演,寫(xiě)過(guò)《忠告電影演員》《電影演員的眉毛》等文章,《〈清明時(shí)節(jié)〉的演員》結(jié)合演員的在影片中的角色,談演員的表演。文章贊揚(yáng)了演員們的演技“都能各如其分,這是最難得的”。然后歐陽(yáng)予倩具體介紹了黎明暉、趙丹、舒繡文、章曼蘋(píng)、李麗蓮、李君滌、王庭樹(shù)、郝恩等人的表演。如黎明暉,歐陽(yáng)予倩指出她有多方面的才能,有豐富的人生經(jīng)驗(yàn),能勝任所演的角色,她在影片中罵歪脖子的那一段歐陽(yáng)予倩尤為贊賞。歐陽(yáng)予倩肯定了趙丹的話劇經(jīng)驗(yàn)和平日辛勤的修養(yǎng),能夠勝任不同的角色,演劇生命正在向前發(fā)展,認(rèn)為趙丹在悲劇里扮沉郁的青年、在喜劇里扮幽默的角色,似乎最合宜。對(duì)于舒繡文,歐陽(yáng)予倩既高度肯定她演二嫂子的角色“真是再恰當(dāng)沒(méi)有”,但是對(duì)于“演技已經(jīng)成熟”的說(shuō)法,又持不同看法,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舒秀文演得熟練是真的,倘若能多給機(jī)會(huì),她一定還能把握住多方面的變化。此外,歐陽(yáng)予倩還提到了其他演員如王飛娟、袁曼莉、徐莘園等,“他們的資格和表演也早有定評(píng)”。總之,歐陽(yáng)予倩積極贊揚(yáng)了演員的齊整,也做出了“片子應(yīng)當(dāng)不壞”的論斷。
鼓吹藝術(shù)與革命之間的關(guān)系
國(guó)民革命軍興時(shí),歐陽(yáng)予倩歡欣鼓舞:“大凡社會(huì)事業(yè),總不能脫離政治關(guān)系。青天白日旗飛揚(yáng)到長(zhǎng)江的下游,全國(guó)的空氣,都得著無(wú)窮的興奮,總以為沉悶的社會(huì)便能生氣勃然;只要加緊著我們的努力,眼見(jiàn)得理想之實(shí)現(xiàn)就不遠(yuǎn)了。”歐陽(yáng)予倩積極參與其中,參加慶祝北伐勝利大會(huì)的游藝演出(演《荊軻》),與高百歲、劉漢臣、夏月潤(rùn)、麒麟童、潘月樵等發(fā)起募捐慰勞北伐將士。《藝術(shù)與革命》是歐陽(yáng)予倩這一時(shí)期的重要作品,鼓吹藝術(shù)與革命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表于1927年7月7日《申報(bào)》。
歐陽(yáng)予倩開(kāi)篇就亮出自己的觀點(diǎn):“藝術(shù)本來(lái)不僅是用來(lái)宣傳主義的,但是真正的藝術(shù)決沒(méi)有不含有革命性的。”其原因是藝術(shù)家的觀察比普通人銳敏,思想往往超乎時(shí)代。因此,革命政府把提倡藝術(shù)作為不可緩之事。歐陽(yáng)予倩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人類(lèi)求幸福,幸福是從革命來(lái)的;批評(píng)了把革命和享福分開(kāi)的錯(cuò)誤觀點(diǎn)。歐陽(yáng)予倩強(qiáng)調(diào),為了享福就要不斷革命:“須知人類(lèi)的幸福,是從人類(lèi)不斷的革命來(lái)的。”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人類(lèi)在進(jìn)化之神鞭策之下,不得不努力向前;違背進(jìn)化公例的民族,就要落伍,社會(huì)因沉滯而趨于腐敗,“革命的工作,也不過(guò)是順著進(jìn)化的公例的一種努力罷了”。歐陽(yáng)予倩肯定藝術(shù)家在革命中的意義:“藝術(shù)家處在指導(dǎo)社會(huì)、喚醒人類(lèi)的地位。本著不斷的革命精神,參加社會(huì)的斗爭(zhēng)。”除此之外,歐陽(yáng)予倩還指出藝術(shù)是社會(huì)與人生不可或缺的:“若是沒(méi)有藝術(shù),社會(huì)便變成沙漠般的枯燥;若是沒(méi)有藝術(shù),人生也變成毫無(wú)意義。”
歐陽(yáng)予倩認(rèn)識(shí)到藝術(shù)的價(jià)值:“藝術(shù)所造于社會(huì)的,真是至遠(yuǎn)且大。”駁斥了“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觀點(diǎn),以許多事實(shí)證明,藝術(shù)與社會(huì)有密切的關(guān)系,“革命是幸福的源泉,而藝術(shù)又是革命的源泉”。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藝術(shù)不應(yīng)該再像從前那樣,是供少數(shù)人的享樂(lè),為少數(shù)人霸占,于民眾不發(fā)生關(guān)系;歐陽(yáng)予倩所希望的是民眾藝術(shù),建設(shè)中國(guó)新藝術(shù)使命的歸宿點(diǎn),完全在于民眾。歐陽(yáng)予倩極力倡導(dǎo)民眾藝術(shù),此后他還寫(xiě)過(guò)《民眾劇的研究》,指出“民眾劇”是應(yīng)當(dāng)作“平民劇”來(lái)理解,“平民劇是要建筑在平民身上,不外是‘民享’for the people,‘民有’from the people及‘民治’by the people”,并且發(fā)出這樣急切的呼吁:“無(wú)論如何,現(xiàn)在我們要戲劇,尤其平民要戲劇!趕快創(chuàng)造民享民有的新戲劇,尤希望以最短期間,有民治的戲劇!”歐陽(yáng)予倩在《民眾劇的研究》的基礎(chǔ)上,又撰寫(xiě)了《民眾藝術(shù)的演劇》(署名倩),分三次連載于《梨園公報(bào)》1931年1月27日、30日、2月2日。
結(jié) 語(yǔ)
歐陽(yáng)予倩的這些佚文,是20世紀(jì)20、30年代中國(guó)社會(huì)和文藝發(fā)展的重要見(jiàn)證。《年先生》《九江的乞兒》是歐陽(yáng)予倩有感于社會(huì)的黑暗、混亂與殺戮而作,是作者對(duì)民族命運(yùn)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思考,體現(xiàn)出作者的人道主義情懷。歐陽(yáng)予倩認(rèn)為連臺(tái)本戲與長(zhǎng)戲并不見(jiàn)得會(huì)賣(mài)座,并且從自我反思開(kāi)始,批評(píng)了戲劇研究者的盲從行為。歐陽(yáng)予倩演過(guò)文明新戲和舊劇,他能夠在話劇大有抬頭之勢(shì)時(shí)進(jìn)行冷靜地思考,將文明新戲與30年代的話劇進(jìn)行比較,強(qiáng)調(diào)劇本內(nèi)容充實(shí)、注重演技、加強(qiáng)舞臺(tái)處理等方面,為話劇的發(fā)展指出了正確的途徑。歐陽(yáng)予倩在1926年初步入電影界,在電影方面亦有自己的貢獻(xiàn),他對(duì)于演員演技的強(qiáng)調(diào)、著眼于編劇和電影專(zhuān)門(mén)人才培養(yǎng)、設(shè)立以技術(shù)為目的的電影學(xué)校的建議,在當(dāng)時(shí)是很有指導(dǎo)意義的。國(guó)民革命軍興使歐陽(yáng)予倩異常歡悅,歐陽(yáng)予倩從藝術(shù)與革命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為革命鼓吹,并大力倡導(dǎo)民眾的藝術(shù)。歐陽(yáng)予倩在這些作品中所指出的問(wèn)題,所提出的建議,所闡發(fā)的藝術(shù)理念,都是基于其藝術(shù)實(shí)踐而產(chǎn)生的,不僅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文藝有指導(dǎo)與促進(jìn)作用,就是我們現(xiàn)今文藝的發(fā)展,也可從中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