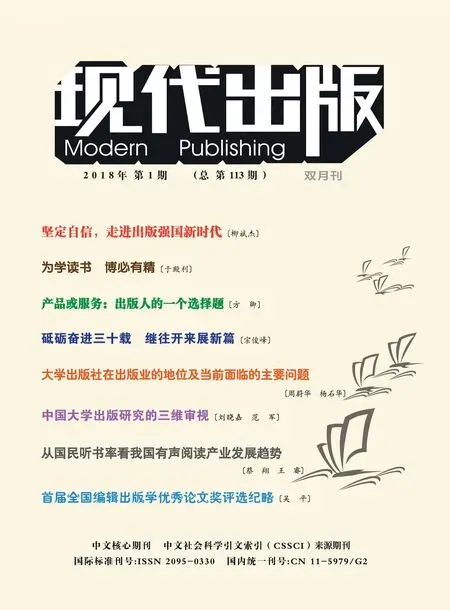我看大學出版
◎ 賀圣遂
我看大學出版
◎ 賀圣遂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大學出版社在西安舉辦圖書訂貨會,當我陪著《文匯報》一名女記者進入展廳時,滿懸的色彩繽紛的中小學教輔圖書廣告令她大感疑惑,隨即以頗含嘲諷的口氣發問:“我是否走錯了地方?”在翌日見報新聞稿中,她更是尖銳地質疑大學社出版物學術品質的狀況。而其時大學出版社正雄心勃發,漸成氣象,出版社數量已逾百,出書品種遽增,規模超常擴展,產值累累攀升,儼然已成為一支出版勁旅,受到業界普遍矚目看好。《文匯報》這篇責難報道雖然讓一些大學出版人感到尷尬不快,但畢竟揭示了快速崛起的大學出版在豐碩業績與炫目光彩之外存在的一些短板與軟肋,因此引發了積極的思考。
中國大學出版發育很遲緩,與其成立時間短、少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有關。嚴格意義上說,它們是伴隨改革開放出現的新生事物。國家允許有條件的各類大學創辦出版社,可是在頂著莊嚴的桂冠矗立起來的出版社招牌下,既沒有歷史和傳統,也缺乏人才與經驗。作為學校后勤保障部門的一部分,甫一創辦即要自食其力。生存所迫,本當是為高等教育服務,卻首選基礎教育著手,中小學教輔遂成辦社第一桶金,雖系無奈之舉,但此類出版物泛濫,被人詬病,引發批評,亦是自然中事。凡此種種,無疑暴露了大學出版發展中的問題。
大學出版何為?其時業內有識之士也早有探究思考,而國門洞開,也提供了考察、鑒取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機會。
我們知道,美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致也有一百余家大學出版社(與我國數量相當),其定位和宗旨十分明確,即致力于學術的傳播和教育的發展,以“倡導學術出版,推動學術交流,營造科學氣氛”為己任。學術出版的目標是跨越學術圈,與社會建立溝通橋梁,打破大學的圍墻,使其科學成果、精神文化產品更多地造福社會。絕大多數美國大學出版社規模有限,資金短缺,往往是虧損經營。哈佛大學出版社主管托馬斯·威爾遜不無自嘲地倡言:“大學出版社的存在就是在避免破產的情況下盡力出版學術作品。”有著這樣瀟灑的態度是因為美國的大學出版社是非營利組織,依靠私人基金和政府機構贊助運轉。正因為如此,出版社處境頗艱辛。美國大學出版社的產值不及美國出版業的百分之一,且早已被中國的大學出版社所趕超。我們顯然汲取認同美國大學出版的許多理念,也逐步發展確立了自己的理念:我們認為大學出版應該是一種反映人類文明軌跡與創造前瞻性見解的前沿出版;是所在大學的延伸,是大學生態鏈的重要一環;要與圖書館、實驗室并列成為學校的第三種學術力量,成為聚集、組織、輔助和催化學術的助推器。當然,中國特色的大學出版不僅強調學術出版的社會效益,同時重視產品的經濟效益功能,唯如此,中國的大學出版才能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競爭發展,走出自己的康莊大道。如今,大學出版已經是中國出版業中亮麗的風景,甚至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贊譽,大學出版人值得為此慶賀自豪。
但是,雖然經濟窘迫,卻仍然嚴格自律地從事高品質的學術出版的美國同行亦有令我們企慕不已的驕人業績:據考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文學獎的不少美國大家,多數首選在大學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新作。著名學者約翰·羅爾斯、何炳棣等蜚聲國際學術界的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也紛紛將大學出版社作為自己代表作的首選出版方,這與歐美大學出版社追求學術出版的理念密不可分。“9·11事件”發生之后,驚慌中的美國人聚焦伊斯蘭問題的探究解索時,發現包括艾哈邁德·拉希德所著的《塔利班》(2000年4月由耶魯大學出版)在內的所有最有價值的閱讀文本幾乎都出自大學出版社。2005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哈里·法蘭克福的《論扯淡》,一篇短短的學術論文卻因匡正時弊之功而榮登《紐約時報》的暢銷榜單,并售出36萬多冊精裝版。2016年推出的廣受好評的《絲綢之路:一部世界新史》的作者,牛津大學教授彼得·弗蘭科潘,也選擇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哈佛大學出版社。牛津和劍橋兩家出版社也許是存世最早,目前也還是聲名最為顯赫的大學出版社。他們都實力雄厚,盈利理財的能力也令我國同行折服。但是他們也都將自身看作大學的一個部門,致力于輔助大學開展教學與科研工作。將本校以及全球學術的前沿成果向學術界和全社會傳播,始終是其不變的使命。近年來,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通識教育”(匯集全球涵蓋人文社科、自然科學、醫學等各學科一流學者,二十余年出書近六百種)讀本因惠溉學林,廣受關注,在全球享譽不衰。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孫康宜、宇文所安等撰)以及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哈佛中國史》(卜正民等撰)等,令國內學界多有獲益。歐美同行的實力豈容小覷?是否也應警策我們仍當勉力思考和更好地實踐大學出版的責任和使命?
(賀圣遂,復旦大學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